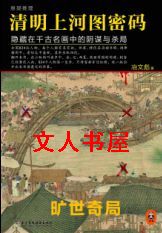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2: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还是听孙哥儿继续说,第二点呢?”管杆儿问。
“第二点是,他们既然得了钱,为何不早点逃走。何必等着被发觉?”
“嫌不够。还想再多得些?”皮二问。
“应该不会……”孙献摇头道。
“嗯,十万贯都不够分,那要多少才够?”黄胖点头道。
“第三点,就像皮二哥刚才所言,那十万贯是飞走的,而不是偷偷搬运走的。俸钱库的钱飞走时,我父亲就在库门前,亲眼瞧见。我去探监时,我父亲也亲口给我讲了,那天真有无数钱飞上了天,半空中还落下来了一些……这些钱是怎么飞走的?飞走后又去了哪里?”
几人都低下头,犯起难来。
“难道是驯养了些鸟儿,牵着绳索将那些钱带走了?”皮二忽然道。
“再大的鸟,也最多牵走百十文钱,十万贯,四五十万斤重,牛车都得拉几百趟。那得多少大鸟才能带完?”管杆儿道。
四人又都低下头,各自苦想。
邱迁照那个阿七吩咐的,挑了两只木桶,出了小院门,向巷道最里头走去。巷道里那几个家丁听到门响,都朝他望过来,每个人眼神都满是惕意。盯得邱迁浑身如被针刺,忙低着头往前走。
沿路经过的那些小院中,都传出些叮叮当当声,有敲击金属声、锻凿声、铜钱响声,恐怕是各种金银铜作。走到巷底,果然见到一口井。邱迁过去摇动辘轳,打满了两桶水,挑起来又埋头向回走。那几个家丁始终盯看着他,他丝毫不敢往左右张望。
挑了几趟,里外两缸水都挑满后,阿七又招手让他进屋,邱迁忙轻手轻脚走进去,见吴银匠又在埋头雕琢另一只银盏。阿七指着炉子边那架风箱比划,邱迁会意,忙轻步过去,坐到小凳上抓着木手柄,推拉起风箱。可才一拉,风箱里便发出刺耳吱嘎声。吴银匠听到,扭头朝邱迁恶瞪了过来,吓得邱迁忙放轻力量,但始终都有那吱嘎声。
“阿七!”吴银匠怒喝一声。
阿七忙蹲到邱迁身边,扒开邱迁的手,抓住风箱木柄,稍稍向上提了一点,示范着推拉起来,声响果然小了很多。邱迁接过手,照着试了试,果然轻了许多。阿七在一旁守着,等邱迁完全掌握后,才转身从柜子中取过来几块碎银,放到天平上称好,拿笔在一张纸上记下数字,而后将那些碎银放进炉子上架着的一只铁黑色小盆中,盖上了锅盖。邱迁以前见过人炼银子,知道那是石墨坩埚。阿七用手示意邱迁继续推拉风箱,邱迁一边小心推拉着,一边暗暗生悔:自己要查冯宝和谷家银铺的那桩生意,来了却在这里给人做杂役,连大气都不敢出,更不用说四处走动、查看和打听。这可怎么好?
“你蹲到那边墙角去。”邱菡对柳碧拂说。
“姐姐,做什么?”
“别问那么多,照着我说的去做。”邱菡怕她阻拦,不愿多说。
柳碧拂盯着她看了片刻,没再多问,站起身走到了墙角。
邱菡见她这么顺从,转头望向桌上的灯,不知为何,忽然想哭。随即想起去年春末那个晚上,他们夫妻两个在卧房里,已经脱了外衣,正要吹灯安歇,冯赛忽然望向她,嗫嚅半晌,才低声道:“有件事……”
做夫妻七年,冯赛从不拿丈夫威严来压邱菡,说话行事一向惯于服低,但从来没这么心虚气怯过,邱菡心里一沉,知道大半年来的担心终于来了。
那大半年来,冯赛的心已经变了。他虽然处处遮掩,但正是这遮掩让邱菡立即察觉,只是不知道是哪个女子。有回冯赛刚出院门,冯宝正巧走进来,问了句:“哥,你又要去清赏院?”邱菡当时在里屋,听到后心里一颤,忙侧耳倾听,但院外冯赛并没有答言,邱菡立即猜到,冯赛一定是打手势制止了冯宝。果然,冯宝“哦”了两声,之后进来问候邱菡,神色也不似往常,也在遮掩,还有同情。
汴京念奴十二娇,邱菡虽不详知,却也听说过,知道清赏院是茶奴柳碧拂的行院。起先,邱菡还盼着冯赛只是一时着迷,但长达半年,他的心思越来越躲闪。邱菡也越来越绝望,只能安慰自己:至少他不敢跟我明言,心里始终还念惜着我。
然而,那晚冯赛一出声,这最后一线不死心也被剪断。
邱菡心里冷得直颤,却仍笑着问:“什么事?”
冯赛抬头望过来,眼中满是愧怕,一触到邱菡目光,立即躲开,又踌躇了许久,才低声道:“我不知该如何开口。”
“你想娶柳碧拂?”
冯赛身子一颤,急望过来,又惊又怕:“你已经知道?”
邱菡用尽最后的气力,轻声说了句:“你想娶,就娶吧。不必问我。”
随即她便吹灭了灯,轻步走到床边,颤着身子上了床,缩到最里边,面朝着墙,再忍不住眼泪,泪水泉一般涌了出来……
都到这时候了,还想这些做什么?
邱菡擦掉再次涌出的泪水,冷冷吩咐柳碧拂:“蹲下。”
柳碧拂望着她,惊异不已。邱菡想,蹲不蹲应该区别不大,便不再多言,伸手端起桌上的油灯,走到床边,将灯焰靠近床幔,点燃了。
“姐姐,你做什么?!”
“别过来!站在那里!”
邱菡一边大声喝着,一边又去点床褥子。等柳碧拂奔过来时,已经点燃了几处。柳碧拂来抢灯,邱菡索性将油灯丢到床上,随即死拽住柳碧拂,将她拉到墙角,看着那张床迅速被火焰围裹……
卢馒头狠命回想着那辆厢车。
那是一辆新车,应该才造成不久。全身漆成青碧色,车檐一圈挂着绿绸幔子,前后车帘也是绿绸。后帘子上绣着一枝粉艳桃花,桃花背后是一轮圆月。虽然车子精贵,但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唯有这桃花明月的图有些不一样,会不会是一种标记,特地绣上去的?
但他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桃花明月是哪家的标记。找了这几天,也始终没见到。店里生意忙,缺了他,浑家和儿女们就有些支应不过来,晚上等他回去,几个人都不住声地抱怨。卢馒头想再雇两个帮手,但眼下生意刚开始,好也有限,又有房租压着。雇了人,生意未必能好多少。
他有些为难,夜里躺在床上想了许久,京城几百家大小车行都已经找遍,那辆厢车显然不是租来的,该是私车。私车便没办法一家家去找,只有碰机缘。于是他重新安排了一下:每天上午、下午生意最忙时,还是在店里照管,过了忙头,再出去寻那厢车。
他心里暗暗祈祷:诸位神爷,诸位菩萨,我犯了这大错,已经知悔,求你们可怜我并不是贪图钱财,是为了儿女才犯下这错,发发慈悲,让我能撞见那辆车,找见冯相公的妻女。
第八章
“五弟”
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
——王安石
“眼下你打算怎么做?”周长清问。
“自然是想尽快找见汪石。不过,他若是真的逃躲起来,短时间恐怕难以找见。”冯赛叹道。
“凡事先得看清,才能办好。咱们先来理一下。对这个汪石,你发觉什么疑点没有?”
“有四处。”
“哦?说说看。”
“首先,我第一眼见他,就觉得面善,似乎在哪里见过,却想不起来。”
“记不记得其他情景呢?”
“昨晚我一直在回想,似乎和银钱有关,至于什么银钱,则根本想不起来。”
“这个不能急,先放着,或许一时触动,便能记得起来。第二处呢?”
“他的来历——他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八岁,却有数万贯资财。一般而言,当是富家子弟,继承了祖业,但是……”
“他不像富家子弟。”
“嗯。他皮肤黝黑,那形貌一看便是自幼辛劳、风吹日晒。”
“应该是暴得了大财。”
“第三,京城闹粮荒,东南水路又受阻,他从哪里得来的十万石粮食?”
“嗯。当时我也在疑心。那么第四处呢。”
“第四处就是百万贯官贷如何能借到?”
“这百万贯官贷倒也说得通。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创制了朝廷生利之法,将官钱贷给民间已是一项政绩,像‘青苗法’,本意的确好,青黄不接之际,农民的确需要借钱买种、补助耕作,官贷只收二分利,比向富户借钱低得多。但这事一旦和官员政绩相挂,便生出许多强迫贷钱、催逼还债之弊。汪石能贷到这百万贯,也是同样道理。太府寺掌管国库,贷出得多,生的利便也多。但民间最怕和官府做生意,能不贷则不贷。汪石刚刚救了京城粮荒,财力又雄厚,太府寺巴不得多贷些给他。而汪石也是瞅准了这一点。”
“但他又是如何说动京城三大巨商联名作保?”
“最让人费解的正是这一处。那三人中,老秦看似面慈心善,但于生意上却十分精到老练,绝难让他上当;绢行的黄三娘,虽是女流,却心思细密机敏,远过男子,更不会轻易让自己落进陷阱;只有粮行行首之子鲍川,稍弱一些,不过也是自幼受其父鲍廷庵调教,又在生意场上历练多年,轻易也不会受骗,何况是百万贯巨资。”
“我只问过秦老伯,他并没有细讲,只说此人信得过。”
“现在看来,汪石的来历,一时难以查清。这三位,倒是该再去仔细打问一番,或许从中能找出些因由线索。”
“嗯。我这就先去拜问秦老伯。”
“好,饮了这杯你就去……”周长清又斟满了酒,举杯前先问道,“最后我再多言一句,刚才我们说了第一层信,第二层信你可还记得?”
“记得。第二层信是‘信己’。大哥曾说,信己,有真信,有假信;有深信,有浅信。更曾说,信几分,便安几分。”
“眼下,你信自己几分?”
“今天见到大哥之前,对自己恐怕信不到一二分了。说过这番话后,能信回五六分了。”
“好。这便是真信与假信的分界了。无事时,人大多都能自信,遇事后,这些信便大半散失。真信己者,并非盲信,而是明白哪些当为、哪些能为,至于不当为、不能为者,则付之天命。如此,心才能安,行事也才能不忧不疑。这杯酒,大哥祝你在此大难中,仍能真信己。”
“多谢大哥,小弟一定谨记在心,绝不许自己再颓丧自失。”
两人举杯,一饮而尽。
周长清送冯赛下了楼,账房提着一个袋子迎了过来,周长清道:“这里有几贯钱,你先拿去用。”
“大哥,我身上还有些钱,现在又寄住在烂柯寺,这些钱拿去没处放。等需要时,自然会向大哥要。”
“那好。不过我正要说住的事。等下我就让伙计去烂柯寺把你的行李搬过来,你就住在我这里。”
“大哥,我之所以住在烂柯寺,一是因那里清静,正好凝神静心;二来……”冯赛犹豫了片刻才道,“我妻儿现在不知身在何处受苦,我自己怎好贪图安逸?寄住在寺里,多少能心安一些,也算一家人两地同心,共渡难关。”
“那好,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你若有需要处,却不跟我说,那便是看低了我,也有负于你我多年之交了。”
“小弟知道,大哥放心。”
孙献默默思忖:那飞钱若真的并非神迹,而是人谋,就一定绕不开蓝猛和那十个巡卒,他们一定牵涉其中。十个巡卒中,六个查得着的,出事前都得了笔外财,想必其他四个也一样。死了的库监蓝猛,应该得的更多。
不过,十万贯库钱,一人哪怕只分到百分之一,也有千贯,在汴京十等坊郭户中,也算五等中富之财。然而那六个巡卒所留钱财数目虽然不知,但似乎没有这么多。他们所得之财,恐怕未必是从左藏库飞钱中得来的。而且,库钱飞走时,至少有十几个人亲眼目睹,很难骗得过所有眼目,何况自己父亲当时也在场。
孙献原本一片欢喜,这么一想,顿时有些丧气。不过他随即又想到库监蓝猛之死,他死于谋害应当确定无疑。若这库钱真是飞走,库监就算有过,也不至于死,什么人要急着杀他灭口?其中一定有重大隐情。
于是他取出袋里的三贯钱,分别放了一缗在黄胖三人面前,三人看到钱,立即一起笑呵呵,眼里冒光。
“三位老哥这几天辛苦了。接下来,有件事还得继续再查问一下——就是那六个巡卒意外之财的来路。这极要紧,若钱是各自从其他地方得来,这事就没有什么可查的了,但若都是来自一路,便值得继续挖下去。”
“我查的两个中,一个不清楚,另一个叫朱四的,我们自小就在一处厮混,根底全都清楚……”皮二一边摸弄着自己面前那缗钱,一边道,“那朱四从小就是个浑货,什么都做不来。他在风鸢段家做学徒,我去瞧过两三回,就已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