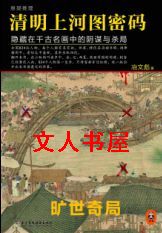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2: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出来时,已是深夜。两人疲累之极,邱迁记挂着姐姐和甥女,还想继续找,楚三官却连声不肯,说回去这么晚要被父亲打死。邱迁只得先去姐姐家再看看,敲门一问,仆人阿山夫妇和阿娴都已经回来,却都苦着脸摇头,冯赛、冯宝也不见回来。邱迁只能先回家。
今天天才亮,他就爬起来,随意吃了点东西,跟父亲谎称去看矾到货没有,匆忙出来,骑着驴子又赶到甕市子街,门敲开后,仆人阿山仍摇着头,说连冯赛也一夜未归,冯宝更不见人。
邱迁越发忧急,忙去寻楚三官。到了街口的楚家药铺,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正在店里骂伙计,认得是楚三官的父亲。昨晚楚三官特地交代,他父亲若在,千万不能唤他。邱迁只得在一边等着,瞅见楚三官父亲去后面了,才小声央告一个伙计去唤楚三官。好半晌,才见楚三官打着哈欠出来,说得先借邱迁的驴子送两担药去城南。邱迁只得帮他把药送到城南。完事后,楚三官才说:“咱们去芳酩院,冯泥鳅一定是钻到那里去了。”
“芳酩院?”邱迁一惊,他知道芳酩院是“汴京念奴十二娇”之一“酒奴”顾盼儿的行院。
“往年他不在瓦子,就在赌坊,可自从他哥哥娶了茶奴,那个茶奴和酒奴又是好姊妹,两个比别人更亲香,他只见了一回顾盼儿,就没了魂,趁着这个便利,没事也要找出些由头,滑皮滑脸拼命往芳酩院钻。”
邱迁听了,心咚咚跳了起来,脸也顿时涨红。
第十三章
芳酩院、馒头店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
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
——王安石
“将鱼行张赐和猪行魏铮一起传上来!”闻推官吩咐道。
一个衙吏忙出去传唤两人,片刻,张赐和魏铮一起走了进来,跪在冯赛身旁。冯赛有些讶异,自己从未接过鱼行、猪行的生意,怎么会关涉到他们的官司?再看杂买丞娄辉仍站在一旁,并未离去,就更加纳闷。
“娄大人,只有鱼行和宫里有关吧?那就先问鱼行……”闻推官望向鱼行行首,“张赐,为何一连两天短缺了宫里的鱼?”
“大人,鱼行岂敢违逆宫中?”张赐今年已近六十,须发皆白,不过面色红润,一双眼睛目光柔和,说起话来也和声细语,“一连两天,鱼行都只收到常日两三成鱼,货色又不好,斤半以上的都少。宫里的鱼又不能随意将就,只敢拣选最好的,因此不得不短缺了数量。”
“为何会这样?”
“上个月有个叫于富的富商包揽了上游黄河的货源,这一路占到京城鱼量四成以上,于富出的价高,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的鱼贩听到消息,都不再把货直接交给鱼行,争着先去找他,结果八成的鱼全都被那个于富攥在手里,成了汴京城的鱼头儿,他和牙人伙在一处,肆意涨价,左右刁难鱼行。货被他截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得尽力奉承他。这样也就罢了,谁知道这两天,他竟连一条鱼都不送了。”
“这于富现在哪里?”
“不知道。我们派了许多人去寻,都没寻见。就连那牙人也不见了人影儿。”
“那牙人叫冯宝?”
“是。”
冯赛一听,头里嗡的一声。冯宝什么时候去做了鱼经纪?!
闻推官看了他一眼,低头翻看了一阵案卷,又问猪行行首:“魏铮,猪行又是什么缘故?”
“禀大人,猪行和鱼行遭遇差不多,也是被一个外来的富商截断了货源,颠来倒去为难猪行,这两天也是忽然断了货,收到的猪还不到平常两成。替那富商跑腿撮合的牙人也是冯宝。”
冯赛听了更加吃惊,难道重名了?
闻推官又问:“你们说的这牙人冯宝,可是你们身边这冯赛的胞弟?”
“是。”两人同时回答。
闻推官望了过来:“冯赛,冯宝现在何处?”
“禀大人,小人不知冯宝现在何处,也正在四处找寻。”
“他做猪鱼两行的经纪,你可知道?”
“小人不知,今日是第一次听到。”
“真的?”
“小人不敢欺瞒大人。”
“冯宝既是你胞弟,他入牙行,又是你作保,冯宝既然躲藏不见,这两桩事便得由你来担。尤其鱼行,也关涉到宫中,你得火速办妥。”
“是。”
“今天何时能把宫里的鱼交足?”
“这个……”
“至少得申时之前。”杂买丞娄辉在一旁忽然道。
“那就申时。听到了吗?冯赛!”闻推官忽然提高音量。
“是。”
“至于猪行和鱼行的事情,关及汴京百万官民饮食,都是天大的事,耽搁不得,也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是。”
邱迁跟着楚三官,来到景灵宫东门的姜行后巷,才到巷口,邱迁的心又怦怦跳起来,他知道芳酩院就在巷子里左边第三个院子。他曾独个儿偷偷来过好几回,装作行路,走过芳酩院,向里觑过几眼。
那还是两年前中秋,汴京各大酒坊的新酒酿成,照例要办开沽会,各个酒坊向官中进呈一色上等酒。每家都雇请社队鼓乐,沿街争胜。队首都是三丈多高的长竹挑起白旗布牌,上写“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酝造一色上等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几个锦衣壮汉挑数担呈祥新酒,乐队跟在后面击鼓奏乐,各色社队竞相逗趣,糖糕、面食、车架、渔父、出猎、台阁……而最打眼的则是官私妓女——每家都要争请名妓压阵,银鞍闹妆马匹上,名妓们头戴花冠,身着花衫,或执花鼓,或捧琴瑟,引得满街人争看。
邱迁当时先也只是瞧热闹,然而,第三队过来时,他一眼看到了顾盼儿。
顾盼儿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戴镶金坠玉的花冠,只用一根红丝绳扎了个斜山式乌油发髻,上面插了六朵粉艳鲜绽的芙蓉花,身穿绯红软绫衫、浅粉色罗裙,肩臂上披绕着一条红叶纹样的轻纱。她也没有骑跨在那匹胭脂马上,而是侧着身子斜斜坐着,软软笑着。
邱迁不知道当时心里为何跳出“软软”两个字,但觉着那笑容身姿,真如诗中所言的“侍儿扶起娇无力”,娇慵中散着些醉意。当顾盼儿走近他这边时,他忙抬头细细盯看,白腻微丰的面颊衬着芙蓉和衫色,晕出些绯色。那双细而长的眼,微微乜斜,如雾中青草间的露水,目光莹莹颤动。嘴角的笑,艳冶中还有些憨态。经过时,她身上散出淡淡豆蔻香气,而那双轻挽红绦缰绳的手,白玉脂一样。邱迁恨不得立时奔过去将那两团白玉脂捧在自己手里,可随即又觉着自己的手太脏,不由自主在衣襟上擦了擦。顾盼儿却随即走了过去,他忙追魂一样昏昏然跟过去,接连踩到几个人的脚,险些被绊倒。
自那以后,他时常偷偷想起顾盼儿,也打问到她是汴京“念奴十二娇”的“酒奴”。不过,偷偷来这里几回,他都没再见过顾盼儿一眼。没想到今天竟要走进芳酩院。
院门开了一半,门扇漆成黑色,角上镂着流云梅花纹,露出里面一道粉壁,上绘着仕女拥瓶、把盏、斟酒的院体画。一眼看到图中那雍容艳冶的仕女,邱迁心又跳起来,呼吸也随之急促。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行院。
楚三官则晃着肩膀大咧咧走进了院门,邱迁忙跟了进去。绕过粉壁,小小巧巧的一座庭院,院中央一大块太湖石,石边高高低低杂植着各类香草藤蔓,碧油油满目青翠。一个妇人从前廊走了过来,五十来岁,胖胖的,衣着华盛。她望着楚三官,脸上有些嫌厌:“楚三,你又来做什么?”
“妈妈,我是来寻冯宝。”楚三官赖笑着。
“他又不是我养的狗儿,寻他到我家来做什么?”
“出了大事,急着寻他,妈妈不要藏起他。”
“我藏他做什么?又不是什么宝货。”
“可不是说着耍,他家真出了事,连你们家酒奴的姊妹茶奴都不见了。”
“你这泼赖,都说了几天都没见他,管自在这里啰唣!”
妇人连连摆手,作势要赶,屋里忽然传出一个娇糯的声音:“妈妈,碧拂姐姐怎么了?”
邱迁一听那声音,顿时着了闪电一样,忙向里望去,但门户空寂,看不到人影。那老妇正要开口,楚三官仰着脖子朝里喊道:“他家两位嫂子连两个小侄女儿都被人绑走啦!”
“被绑走了?”一个女子出现在堂门边,是顾盼儿。
顾盼儿今天一身春色,缠枝纹绿锦半臂褙子、柳叶纹浅绿罗衫、桃瓣纹嫩绿罗裙,乌油的发髻只插了一支碧玉钗,簪着两朵粉鲜海棠花。脸儿凝脂白,眼儿醉流波。邱迁心里暗想,满城人都去郊外寻春,却不知,这才是碧枝春光。
“究竟怎么了?”顾盼儿微微蹙眉,面露惊忧,显得越发娇憨可人。
“你问他——他是冯家的小舅子。”
顾盼儿忙望向邱迁。邱迁今天特地穿了一套浅青色新衣裳,却觉得自己满身尘垢,脸顿时红涨,舌头也发僵,眼睛不敢看顾盼儿,望着门框低声道:“昨天……昨天早上冯宝雇了两顶轿子,把我姐姐……还有柳姐姐接走,还有两个外甥女,半路上却被人劫走了,至今找不见人。”
“啊?!”顾盼儿几步走下廊前台阶,来到邱迁近前,“冯宝为什么这么做?”
邱迁偷看了一眼顾盼儿,慌忙躲开目光,又嗅到了豆蔻香气,越发手足无措:“我……我也不知道。所以才……急着找冯宝。”
“冯宝寒食前来过我这里,这几天都再没见过。你们赶紧去别处找。”
“好——”邱迁忙转身往外要逃。
“对了!邱公子,有消息请你也来跟我说一声。”
“好!”邱迁偷望了一眼,顾盼儿目光如酒,他顿时又醉了。
“你说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邱菡起身摸到桌上的火石、火镰,打着点亮了油灯。她见柳碧拂呆坐在桌边,便也在对面坐了下来。灯影下,柳碧拂面色十分苍白,神色也显得冷寂。邱菡想,这个时候,还是得一起想办法。然而柳碧拂却仍不愿多说话。自从娶她进来后,她一直是这样,始终不冷不热、不远不近,只把礼数尽到,多一句话都不说。
“你不怕吗?”邱菡又问。
“从十岁起,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柳碧拂竟淡淡笑了一下,目光却似乎有些孤寂悲哀。
“哦?”邱菡有些诧异,却不好深问。猜想她恐怕小小年纪就被卖给娼家,进了那样的地方,就算怕,也由不得自己了。这一年来,邱菡第一次不那么嫌憎柳碧拂了。
“姐姐很怕吗?”柳碧拂忽然转过眼,目光仍然很冷寂。
“开始很怕,现在好些了。我只怕他们对玲儿和珑儿……”
“做了母亲,为了儿女,是不是什么都愿意舍掉?”
“嗯。”
“连性命?”
“连性命。”
“若是舍了性命也救不了儿女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若对玲儿和珑儿怎么样,我就跟他们拼!”邱菡伸出手隔着衣服摸了摸,她怀里揣着一块瓷片,是在那炭场院摔碎那只碗后拣的一片,用来拼命的。
柳碧拂不再说话,望着她,眼里露出些凄然笑意。
邱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望着灯焰呆了片刻,终于还是忍不住问出一直想问的话:“你……你为何要嫁给冯赛?”
“这……那姐姐为何嫁给他?”
“我?我是父母之命。”
“成亲前没有见过他?”
“没有。”
其实邱菡见过,而且不止一次。当年冯赛才进京没几年,还是小牙人,常替邱菡的父亲说合生意。邱菡并没有特意看过他,有时冯赛在外面和父亲说生意,她从帘后偶尔看过几次。那时看了也没有怎样,只是觉着这个年轻男子样貌衣着干干净净,说话行事又温和简明,让人愿意亲近。后来父母说冯赛来提亲,她听了有些惊讶羞怕,但不厌,还略有些心动。因此什么都没说,听任父母安排。
“插钗定亲时也没见?”
“当时又羞又怕,哪里敢看他?”这句邱菡没有说谎。
“姐姐嫁给他,后悔过吗?”
“后悔?”邱菡呆了半晌,才叹道,“生为女子,哪有什么后悔不后悔?”
“为什么不能后悔?律法都说,夫妻若不相和谐,可以离婚。”
“又有几个女子愿意离婚的呢?”
“其实,姐姐并没有后悔过。”
邱菡苦笑了一下,并没有回答。心里却暗暗自问,后悔过吗?
没有。
哪怕冯赛娶进柳碧拂,让她满心怨忿,自己却从来没后悔嫁给冯赛。
为何呢?
冯赛常日里那种小心赔笑逗趣的体贴样儿,忽然浮现眼前。她心里一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