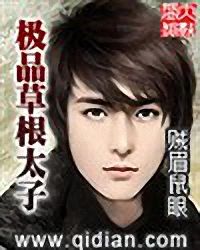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一直在考验着我,我成熟了,他也“瓜熟蒂落”了。对这件事,他很失意,觉得对不起我,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很感激他!来到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机关世界,政治势力派系纷争的官场,没有“古板”的原则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没有他的影响与榜样作用,我会留丢自己的“古板”,变得不伦不类,成为真正的“圆石头”,失去了可贵的人格个性。
世界上至今还存在“古板”这个词汇,足以证明有他生存的空间和环境。“文革”就是想把所有人的头脑清洗干净,然后输入统一的思想软件,结果人人中黑客的病毒,几乎致使整个社会机器瘫痪。我觉得,是“古板”拯救了濒临绝望的系统,从死机中把社会拉回光明。
那么,郭书记的“古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4 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4如毛的上司(自毁前程)(2)
郭书记的“古板”,有些固执己见的味道,“霸权主义”的色彩,山大王形象的脸谱。党委会,是他发表重要指示的平台,是他发号施令于党委班子的帅帐,有时候也是他发泄旺盛威严的角斗场。
“文革”前后,农民最讨厌的就是“兴修水利”,郭书记则乐此不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可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弊在当代,祸在千秋”了。
郭书记的水利工程,不分地块旱涝,不管地势高低,全都搞“条田”,跟小学生的小楷的方格一模一样,也像豆腐块。这是最早的“豆腐渣”工程,农民把它叫做“豆腐工程”,不结实,不顶用。条田的沟,秋天挖出来了,春天种地不方便,又填回去了。有了这些沟沟,高地块的水把低地块淹得更严重了。高地块本来就缺水,现在倒好,有点雨水半点都留不住,不然农民怎么会“秋挖春填”啊。他们不傻,有人傻,傻得不讲理。
大凡文过饰非的人,老天爷在他的面前就会变傻了。全公社12万亩土地,怎么也得有得益于“条田”的典型吧,百里挑一不难找到。一俊遮百丑,郭书记便大做文章,以此作为新一轮大兴水利的理论与实践,变本加厉地推行“条田工程”,群众称为他是“老一套”。“老一套”是什么呢?大概和“古板”一脉相承,同宗同族吧。
1978年,中断多年的高考在全国恢复了,天大的喜事!有见识的父母,无不把眼睛聚焦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老史、郭书记……都是明眼人,岂有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道理啊?他们听说我能辅导学生,哪能错过这个免费的老师(那时候也不讲有偿服务)和难得的机会呀?除非傻子吧。
都说郭书记不会笑,那是他傻。我看他不仅会笑,而且一笑竟然没了“古板”的面孔,笑得我很快进入“犬子家父”的角色。
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我绝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而落个“误人子弟”的恶名,那不是我的为人。
几个月过去了,其子学业毫无建树。郭书记自认他愚不可及,谢了我一片诚心,我对他也无话可说。他哪里知道,不是他儿子愚钝,是他自己的“古板”铸成了儿子终生的遗憾。
我第一次辅导他儿子时,就已经断定“大势去矣”,就因为他的一句话,叫我回天无力。
没等我开口讲课,郭书记先给儿子上了一课,他说:
“他妈的,好好学,呵呵,学不好你就当兵去……”
当兵?孩子们羡慕的就是当兵了!爸爸是党委书记,他要想当兵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自然乐不可支。小小年纪,“升学”与“当兵”孰轻孰重,他有那个筛选的能力吗?倒是他的老子,为他指出了一条可以通达理想的阳光大道,他还会专心致志的寒窗苦读吗?
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放弃,就启发激励他立志奋发。他笑了,说:
“爸爸说……说我狗屁不是,不是念书的……”
一个人对自己没了信心,还会有勇气吗?没过几年,我辅导的孩子都先后升学了,他果然走进了军营。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转业了,在新民客运站当内部“警察”,那时候不叫保安。
老史则不然,他对孩子的口头禅是,“我没有能力叫你去当兵,何况你还是个女孩子,要饭比当兵清闲,你要饭去吧。”
老史向我求教秘笈,我也实话实说。首先是家长要有信心,态度要坚决,不给孩子留有余地;切记“欲速则不达”,过分的约束和不必要的鞭策往往事与愿违……老史很快地消除了同孩子针锋相对式的谈话,“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1983年,老史的孩子考上了新民重点高中,和我的孩子是同班的学友。1986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
一师之徒两种结局,谁之责任,谁之功过?父母有,为师也有!那么,我有什么责任?
如是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开导老史,甚至可以教育他,命令他,“骂”他,直到他接受我的观点为止。对郭书记我会吗?他可是土皇上,一言九鼎的君主。而我人微言轻,纵然“忠心耿耿”,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人啊,不要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自绝于人情。官啊,位置再高,你也高不过人,人性是最崇高的,最值得珍惜的……
1979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给“古板”的农村带来一片生机,充满了活力。而对于很“古板”的郭书记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和随之而来的新名词,令他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他谈新形势作报告时经常说走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引起哄堂大笑。他很尴尬,骂自己,“他妈了个八子的,惯了,下次注意了,哈哈”。这正是——旧的车下轨了,新的轮子他还蹬不习惯。
1980年,郭书记走了,到县委纪检委员会任副书记,官升一级,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他走了,是个划时代的符号,农会干部退出了农村的历史舞台。他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党委书记,安步当车,起早贪黑走田间穿街巷地深入基层。他走了,也结束了一个“古板”的年代。他走了,上上下下都在猜测接任者……
4 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4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新来的党委书记姓冯,冯贵清。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脸庞、一副白边的近视镜……若是他出现在高等院校,你会认定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他到来罗家房乡政府不久就有了雅号,人称“冯眼镜”。
他就任之前,乡里的一些同志对他就很“熟悉”了,那是在县里开会认识他的。1981年,县里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乡村三级),冯书记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介绍那时他所在的大柳屯乡搞“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正是这个会议,才掀起了新民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序幕,吹响了农村经济大变化、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此时此刻,冯书记的仕途也达到了巅峰。一年后,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险些落个“上台巴掌响,下台绳子绑”的悲惨结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怎么改革?”没有定论,中央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可以执行,绝对没有的。1980年的1号文件说的很准确——联产承包,适用于“老少边穷”和“三靠”地区。所谓“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也就是说,后来的“分田到户”责任制,中央是反对的,起码不赞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央思想还没有解放,还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上上下下人人清楚,所以县里的会也没有明晰的说法,但肯定了一点——不许“单干”!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拉马抬槽”,拆社会主义的台,挖集体经济的墙角!
不需单干,那要怎么干?
在这个时候,安徽凤阳已经实现了“分田到户”,那里属于“三靠”地区。除此而外,报纸上介绍了许许多多实行“责任制”的典型,很适合我们乡村。于是,我们乡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强烈要求实行“以大化小”。
所谓“强烈”,是农民不堪忍受“大帮哄”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生长队百八十号男女劳动力,真正到地里干活的人不足一半,只有九等人和十等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栉风沐雨。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公社、大队谋个离土不离乡的差事。什么“农田水利”“公社养鱼池”“综合厂”“机修厂”“拖拉机站”“人保组”……他们都挣生产队的工分,却不给生产队挣钱。一个干活的农民,养活一个吃“闲饭”的游民,还有劳动的积极性吗?他们没有办法摆脱不公,只好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民怨四起。
这样的生产形式和形势还能维持下去吗?然而,没有红头文件,不维持也得维持。怎么维持?县里和公社派出大批的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实际上就是“监督”社员劳动,施以高压政治。“路线分析会”、“批判会”应运而生,你不老实就对你实行“专政”,扣你的工分。至此,社会矛盾、干群矛盾日趋激化。
农民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得知有的地方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以大化小”还不行吗?于是,就强烈要求大队公社为他们做主。刚开始,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为没有政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我们地区,那时候上级唯一的政策是,“包工包干”。比如说,种一亩地给你四个人一天的工分,你们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半天由你自己支配。农民不吃这一套,归根到底没有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还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他们的负担没有丝毫地减轻。
农民不甘心,就自己开会“以大化小”,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生产队,或是一分为三、为四……对此,后来公社认账了,全公社的生产队得到迅速的分蘖,生产队由原来的108个增加到140多个。
刚开始时,新生的小集体都是“人合心,马合套”自愿组成的,一时热情升高。没过多久,新生的和旧有的同化了,队长会计……应有尽有,不然不符合上级的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层人物”比原来还多了,社员的负担更加深重。“五脏俱全”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一干人,也“五毒俱全”,吃喝贪占懒无一不能。社员“出工不出力”又旧病复发,“以大化小”成了“换汤不换药”,农村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人怕逼,马怕骑”。到了忍无可忍,生死攸关的地步,农民的胆子比天都大,真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老少边穷”,什么“三靠”,全都不在话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地区和“老少边穷”“三靠”还有区别吗?不到一年的功夫,“三定型”的生产队彻底土崩瓦解。后来,我的小说《草根轶事》(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所谓三定型,就是生产队实行“定生产人员、定生产任务、定生产消费”。较大的生长队所以敢一分为二,就是以这个“三定”为理论根据的。到了农民手里,就成了“三分天下”,一个大汉朝驾崩,魏蜀吴三国鼎立。
既然“三定”名存实亡,干脆就拉马抬槽各自为政。新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驾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受命于“天”的,“天”就是农民,社员。
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其实就是介绍“三定”的经验。面对眼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分田单干”的局面他将如何地应对?全乡的干部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他对新兴的“分田单干”不冷也不热,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他每次下乡都要我陪同,大概因为我是乡里的舆论中心与党委的喉舌吧,我是广播站的记者与编辑。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晚上都要搞调查,与干部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心声。他十分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让农民体会到他是支持他们自发的改革的,但绝不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民很理解他,同情这位大员的处境:
“冯书记,你放心,有事我们担着,这是我们的主意。”
是的,的确是他们的主意,冯书记支持而已,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
罗家房乡的“分田单干”,在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完善着。
不到半年的时间,上级终于有了正式文件。文件中说:“如果农民愿意,可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我觉得,中央是在顺应农村现实的形势做出这个“意见”的。“如果”,就是商榷,商量,不是决策,而是意见、建议。“可……”模棱两可,并不坚决。可后来,官方对“分田到户”说成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点与事实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