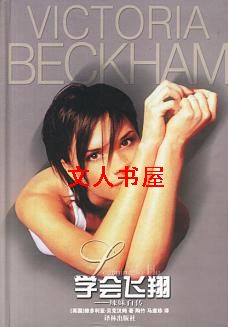山口百惠自传-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其自然,随心所欲。
珍视自己。
珍视自己的感性。
哭也好,笑也好,生气也好,悲伤也好,这一切都是感性的差异。今天,我从幼年的自卑感中稍许解放了一点,能够正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能够想得开了,这就是我自己的表现方法。
但是,我还是想把一直被人议论的那些话记在心里。因为那也是我的一部分没有改变的东西。
数字
每个人都会受什么拘泥,所谓吉利数字也是一种拘泥吧?
我从小学生时代起就和“十七”有缘。上了六年小学,我的学生证号几乎都是十七。如果牵强附会的话,这数字适用的地方很多,我的出生日也是十七日。
从小时候起,我就决定把“十七”作为我的吉利数字。虽然说这样决定了,可在以往发生的事情中,从不对数字寄托希望,不过只要学生证号是十七,我就莫名其妙地放心了。
记不得哪一次,只那一次,我的学生证号成了十八,就为这个,我心烦意乱,毫无根据地断定自己这一年也许会碰到什么倒霉事。
奇数和偶数相比,我喜欢奇数。
从前,在杂志来采访我时,我这样回答过。记者问“理由呢”,我说:“说不出道理,但总觉得是奇数就好。”现在想来,我的回答牵强、不明不白的。既然受某一事物拘泥,自然没有能够说得清楚的理由了。尽管如此,那位记者现出奇怪的感动之至的神情,说了声“嗯,说不出道理的感觉吗……嗯”,独自洋洋得意回去了,他能理解这些吗?
年龄也拘泥于十九岁。它比其他任何年龄都使人感到神秘和娇艳。过了二十岁就是大人,不足十八岁还不算成年人,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其间承上启下的十九岁这个年龄很感兴趣。
十九岁时恐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每逢问到我憧憬向往的年龄,我总要回答十九岁。到了这个年龄就停住,不要进入二十岁该多好——我希望。
十九岁!
不出所料,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了,也可以说成是精神上的分水岭吧。总之,这是我身边都被染上从未有过的颜色的一年。
在“歌星诞生”这个节目中,也是奇数和我相伴而行。预选号是101 号,电视预选是3 号,决胜大会是11号。我记得,预选时看到号码是奇数,就想到“是奇数,我没关系了”。
真是不可思议,是奇数就有信心。要是在那里拿到偶数号,也许当场就会丧失信心回家去了。我曾想过,仅仅是这么一点小事,它就可能使我的生活和现在截然不同。
初次登台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一日。引退日虽在十月,日子却是十五日。而举行婚礼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九日。如果说两个数字中有一个概率的话,那么,这说明还是和奇数有缘。
我现在的年龄是二十一岁。兴许过于拘泥了吧?不不,我今后还要拘泥下去。我自己私下里悄悄地拘泥于此,有时也是很愉快的。
少女
大概是几年前啦。
连季节都没有记清楚。
是在广岛的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那夭,和往常一样,帷幕拉开,一切正常进行。节目演过一半以后的时候,我开始谈起母亲。舞台暗转,聚光灯笔直地投射在我身上。我一个人讷讷地说了五分钟左右。
“将来,到了我穿上新娘礼服的时候,我要对母亲说‘谢谢’……”
我确实记得是用这话结束的。
钢琴轻轻弹出《波斯菊》这支曲子的前奏,这时,有位少女离开观众席,朝舞台跑了过来。
她那白色的连衣裙在昏暗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象是要来献花的,还没跑到舞台,就被工作人员挡住了。即便从高高的舞台上,我也能看到这个情景,我感到工作人员有些粗鲁。我一边唱歌,注意力却总向着那边。我看见那位少女把脸伏在旁边座席上一位妇女的肩上。
“她正在哭吧?”
我无法置若罔闻地继续演出。我希望,这场演出对那位少女来说理所当然地以一个美好的印象结束。
我很担心那位少女的好意被他人挫伤。哀怜的是,象她穿着的连衣裙一样雪白雪白的心灵沾上了泪痕。我觉得可能会丧失掉少女和我之间非常宝贵的东西。
唱完《波斯菊》,又该我讲话了。我用眼睛追逐着少女的身影,说:“工作人员不过是尽力做了自己的工作。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能把你拿着的花给我吗?”
少女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她也许会拒绝的,也许不肯原谅我——。紧接着的一刹那,她轻轻点了点头。
少女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来到和她身材那么高的舞台前,把花束送给了我。
我很高兴。至少这一瞬间,我越过了歌手和观众之间的藩篱,和这个少女的生活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她和我的心灵有了很大的联系。
“谢谢,”这是我由衷的话。我把目光转向接过来的花束,那正是一束淡雅的波斯菊。
歌
出国归来时,必须在海关申报单上填写在旅行地所买的东西,还得填上乘坐哪次班机抵达、本人住址、姓名、年龄、职业等等。职业这一栏上说,申报人要尽可能详细填写。每当我面对这张表,便要斟酌如何填写才好。
是填歌手、女演员,还是电影演员呢?从歌手、电影演员这几个词里得到的感觉,也就是所谓语感,是轻浮的,我都不那么喜欢,但我对女演员的名称也有抵触。犹豫再三,有时我甚至还填写过自由职业。我不知道演艺界的工作究竟属于自由职业还是服务行业,但是不管算哪一行,的确都是说起来难以解释的工作。
直到不久以前,我终于开始毫不踌躇地填写“歌手”二字了。我觉得自己大概是真正地喜欢了这个工作,胜过了担心语感中的轻浮。
一、我选择歌手,而不是演员,也不是电影演员,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把歌唱作为职业以来度过了八年时间,并不是我最初就喜欢这种工作。当然,我喜欢唱歌,是自己投入这个自己向往的世界中去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把唱歌职业化,却与自己的志向无关。同一支曲子一天不知得唱多少遍,一唱就是两三个月。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我开始讨厌唱歌了。
不知不觉我赞成了周围的人们把歌手说成玩偶的比拟,我不喜欢自己是那个样子。不知是谁说过,戏剧是集体的演出,唱歌是个人的表演。这话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厌烦唱歌。
因此,心神恍惚中常常唱错了歌词,导演也提醒过我,可还是不起作用。
我也厌烦到各地去公演。
不论到哪里演出我都是这样:除了车站、剧场、住宿的饭店外,不想上街,也没兴致品尝地方风味。
站在舞台上,照节目单上的曲目演唱,照台词说话,又照着乐谱发音,唱完了事。
当时人们说我是个人的表演,我也无可奈何,心中有一股无法摆脱的凄凉。
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谋求自己的班子,我想演唱不再是个人表演的歌子。组成一个班子要有很多人:灯光、音响、舞台监督、乐队,还有歌手。这些人当中只要缺少一个,我的舞台就不能问世。
我希望有一个不必我操心,大家就能为组织一场演出而进行讨论的演出班子。
为了建立这个班子,我花费了意想不到的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所在的公司碰巧没有安排演员个人计划的机构,所以首先要开始让他们接受这一破例的申请。以后的进展就比较顺利,我与那些理解我的心情,申请参加的人定出了“山口百惠计划”。
多么高兴啊!
“以后,我们要制定出一个能让观众们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影响的计划。”
大家也拧成了一股劲。
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边喝边想:照射我的聚光灯毫无疑义是温暖的。随着不同的曲子变换各种音调的平衡,以烘托歌曲效果的音响,也是温暖的。边听自己的歌唱、自己的声音,边从伴奏得密切和谐的每一件乐器声中,也感到了温暖。
“唱歌是个人的表演”,说这话的人我不认识,所以说这话的心绪因缘自然也不清楚。但我引以为自负的是,至少我的歌唱、我的舞台,并非是个人的表演,它是一股和谐的暖流。
我喜欢温暖的音色。
今天,我认为自己所以对自己的歌唱抱有自信,就是得益于在演出计划中与这些人的幸会。也许世上任何人都肯定会有他自己独有的为之自信的东西,在我来说,首先是嗓音,其次是唱法。我的嗓音绝非甜美清润,而是低沉粗旷的,与我平时说话的声音相比,我对歌唱的声音更有信心。说到唱歌的监力时,我知道自己有发挥自己身体某一部分能够表现出某种特长的动人之处。
其次是我的唱法。
在初次登台以前,我只有一个八度音域,七年半后的今天,用真声可唱出两个八度,算上假声便扩展到三个八度。同自己的音域变得开阔起来相比,我更高兴的是能够用自己的嗓音把任何人的歌变成自己的歌。
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歌,不论谁都难以模仿。单模仿形式和表面,那算不了模仿者自己的长处。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自己的嗓音和唱法抱有很大的自信吗?因为有了自己的声音,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这一点绝没有言过其实。而且,同我班子中的人们相遇以后,我在一段时期那么讨厌唱歌的状况也彻底改变了。
人们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着,那些细微的变化情况,通过音乐旋律和歌词表现出来。我发现即使是歌词和旋律不变,随着歌唱者年复一年的演唱,歌子本身也会有变化。
也许迟了。发现这一点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单是能够发现这一点就是幸福。现在,同一支歌子一天不论唱多少遍,即使唱上一年,我每次也都会以令人惊异的新鲜感来演唱。
因为是歌手也许就以为当然如此了,当一名歌手居然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回顾当初,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当我观察自己的变化过程时,我不能不感到人的心灵在感知和探索之中,就象循环不已的季节那样变化着。
面临引退,我思索着和自己相关的歌唱。现在,我深刻而亲切地感觉到,爱上歌唱是多么美好。使我大为庆幸的是,我不是在未同大家幸会并且对职业性歌手感到厌倦时辞去工作的。
假使我始终象当初那样,说不定现在连哼过的摇篮曲也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可以断言我已经真正爱上了歌唱的今天,在我已经达到歌唱顶峰的今天,辞去歌手的职业,我并不恋恋不舍。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当歌手这一希望的呢?我想说是从很小时候,但是我也觉得好象是进入演艺界之前的四、五年开始的。然而,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这么一件事情。
那时妹妹还小,我们到姨母家去玩。记得是在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歌手呀,可真够呛、这工作可是不好干哟!”
姨母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望着她的面孔。她脸上表现出要我搭话表示赞成的神情,我不知道怎么口答才好。因为我什么也不懂,那时,不负责任地说声“是啊”也行,但我什么也没说,也没能够笑出来。
也许那时,我就在无意中已经预感到了自己今后的道路。
送报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临到快放暑假的某日,一位邻居家的阿姨对我说:“今年夏天,我想回乡下看看,不如百惠的朋友中有没有人愿意干点零活,替我投送四十天报纸。只送早报就可以了。”
听完,我想了一下,从这个地区看,朋友中没有能做这项工作的人。
“行啦,阿姨,我来干吧。反正暑假里我也没有别的计划,没有关系。”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母亲也没有特别表示反对。
我当时读书的学校,规定禁止学生在暑假里千零活。虽然我决定去干,却不知道学校会不会同意。
母亲先同我的班主任谈了此事。
有一天老师叫我放学后先别走,留在教室里。老师爽快地对我说。
“干得了吗?要是中途打退堂鼓,还不如开始就别干。啊!”
“没关系。”
听我这样回答,老师又以温和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好吧,那就干干看吧。”
什么问题也没有,老师就批准了。这件事后来不知怎的竟被说成是我“为了帮助家里的生计”,是性情好的美谈故事,我只能对此目瞪口呆。
放暑假的前两天,为了记住将去送报的人家,我就跟着那位长辈跑开了。她先交给我一本清清楚楚的登记着哪一家订什么报纸的笔记本,我就是按照本上记的把这些记住。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