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怎么说的?”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和她跳舞的时候说的。”他转过身来对着我,认真地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爱的时候,不说也看得出来。”
“喔……”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是故作镇定。到家门口,我熄了车灯。在黑暗中,我们都坐着,不动。然后我说,“安,你也爱上了什么人吗?”
他摇头。
“如果发生了,你——会告诉我吗?”
他说:“会吧……”声音很轻,“大概会吧。”
今晚,我想,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秋夜,13岁的男孩心里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许不太明白。一种飘忽的情愫?一点秘密的、忽然袭来的捉摸不定的甜美的感觉?
平常竭尽所能拖延上床的他,早早和我说了晚安,关了房门。
你记得那个晚上吗,安德烈?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平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19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在一个极端苦恼,或说“痛苦”的情绪里。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在这种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23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粉红色的蝴蝶结
歌德这样描写少年维特: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Von Himmel fordert er die schoensten Sterne/Und von der Erde jede hoechste Lust);19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叠的时候。你的手足无措,亲爱的,我们都经验过。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绯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十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40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23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象: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10次,受伤20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沉思,沉思的倾诉?
你是否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MM
第十二章 让豪宅里起战争
MM:
这个月实在没什么值得谈的,每天都在准备毕业会考,虽然足球还是照踢。也因为每天都在拼命读书,所以礼拜五发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个十到十三年级的班都被叫到会议厅去集合。我到了会议厅,看见校长已经拿着麦克风站在前面。我们都很惊讶,一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才会有这样的阵仗。你也知道,德国学校一般是没有集会的,什么朝会、周会、升旗降旗、开学或结业什么的,都没有。
大家坐定了以后,校长就开始解释:我们高中部的一个学生会干部──就叫他约翰吧──被几个陌生人围殴受伤,我们学校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呼吁所有的同学团结一致,谴责暴力,并且给被打伤的同学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动啊。但是紧接着“流言”就开始了,而且“流言”还得到证实:打约翰的是本校学生,但所谓“围殴”,其实是一小撮人围着他理论,打了他一个耳光,只是这样。
学校召集我们,想培养一个团结互爱的气氛,但是真相一出来,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超级反感。搞什么呀,我们是毕业班的学生,正在上一堂重点课,中断讲课,就为一个学生被人打了一个巴掌?
MM可能会觉得,嘿,安德烈,你怎么这么不讲道义,缺同情心,你应该支持那个被打的学生啊。
我只能告诉你,MM,我在这所中学九年了,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个笑话。克伦堡中学是一个典型的富裕的郊区中学,平常安安静静的,但是我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拿着小刀追赶,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抓着棒球棒打混架,学校当局也知道,但是从来没管过。怎么这一回,突然这么“积极”啊?
看我能不能跟你说清楚。德国中学分成三类,你知道的,“主干中学”(五年级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只能开卡车、收垃圾、做码头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实业中学”(五年级到十年级),主要是职业教育,培养各种工匠技师,从面包师、木匠锁匠到办公室小职员,都是这里出来的;然后是Gymnasium“完全中学”(五年级到十三年级),等于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学术菁英。我们的学校是一种综合中学,三类都在一个校园里。
我所看见的打架,基本上都发生在“主干中学”的班里,这些学生很多来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适应的困难,所以很多学生也来自问题家庭。好,你现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为什么那些学生拿刀子追杀的时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学”的学生被打了一个耳光,你就突然这么紧张,这么郑重?
年轻人起冲突是常有的事,但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经八百告到学校去。我不敢说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么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并不都是流氓。事实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药的。他们只是跟中产阶级德国人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什么叫“尊敬”或者“荣誉”。他们可能表现出比较强的攻击性,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认同。
我认识这个被打的约翰,家里很有钱,是那种很幼稚、胆小怕事的人,观念完全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种绝不会晚上溜出去会朋友,而且动不动就“我妈妈说”的年轻人,活在一个“白面包”世界里,根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的发展才真叫我火大。学校网页上有个学生论坛,很多同学上网讨论这个“约翰事件”。有一个“安妮”女生这样写:
我们学校越来越沉沦,越低级了,变成一个暴徒、无产阶级、白疑横行的地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认为我们学校将来收学生时,应该要先看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再决定他够不够资格进来。我真的无法以学校为荣了,“那种”学生越来越多…
太荒谬了,MM,我并不赞成暴力行为,我承认绝大部分的打架都发生在“主干中学”,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主干中学”学生来自所谓“下层社会”而“下层社会”问题真的很多,但是我无法接受学校把这些学生拿来做问题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没法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菁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么回应那个“安妮”吗?只写了一句话: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安德烈
第十三章 向左走,向右走
地平线有多远
安德烈:
台湾式新闻
很久没回台北了。昨天回来,就专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新闻。那一个多小时之中,四、五个新闻频道转来转去播报的都是一样的新闻内容,我综合给你听:
天气很冷,从来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于是山村里的小诊所就挤满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个人因为天冷而病发死亡。
半夜里地震,强度五点九。(是,确实摇得厉害,我被摇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里,等候,然后再睡)。电视报导得很长,镜头有:一,超市里的东西掉下来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预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异功能,预测了地震会来,但是预测日期错了。四,医院里护士被地震吓得哭了。五,有人抱着棉被逃出房子,带着肥猪扑满。
有个小偷在偷东西,刚好碰上地震,摔了下来,被逮个正着。小偷偷不到东西是“歹运”象徵,所以他手里还抓着一条女人的内裤。
天气冷,人们洗热水澡,七个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镜头:尸体被抬出来。
宾馆里发现两具尸体。
一辆汽车冲进菜市场,撞伤了十来个人。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猪圈里养了两年。
一个立法委员结婚,几个政治人物去吃饭,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有没有和彼此讲话。
街上有游行示威,反对中共制订“反分裂法”。镜头:老人晕倒,小孩啼哭,绑了蝴蝶结的可爱小狗儿们扑来扑去。
媒体采访北京的两会,记者们跑步进入会场,摔倒了。
灯节的灯熄了。
好了,这就是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怎么样?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何发展?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也没听见。只好上网,然后才知道:
叙利亚提议要逐步从黎巴嫩撤兵,伊朗声言要继续发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抢救释放却又被美军枪击的义大利女记者认为美军是蓄意射杀,联合国发表新的报告,估计二零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万艾滋病患者,北刚果的部落屠杀进行中,莫尔多瓦今天国会大选,但是反对派指控现任总统垄断媒体,做“置入性行销”,而且用警察对付反对党,是最独裁的民主……
有一个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乌拉圭新总统华兹奎兹宣誓就职。
这有什么稀奇,你说?
左眼看世界
是蛮稀奇的,安德烈。这个新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左派当政。而主持宣誓的国会议长,穆吉卡,在六十年代竟是Tupamaro游击队反抗运动的创始人。为了消灭他的游击队,一九七二年乌拉圭开始让军人掌政,固然消灭了游击队,也为乌拉圭带来十三年的军事独裁,被杀害被凌虐或失踪的人不计其数。穆吉卡也是曾在监狱里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读到这类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见两个现象: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二十年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莫尔多瓦,一党专政走向了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是进步了,不是吗?
可是你发现,莫尔多瓦的掌权者事实上仍是共产党,只不过,这个共产党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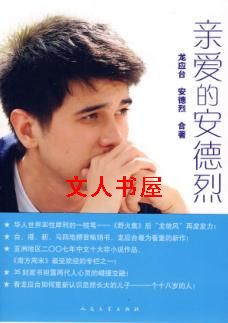


![[韩娱GD]我亲爱的小冤家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3/1392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