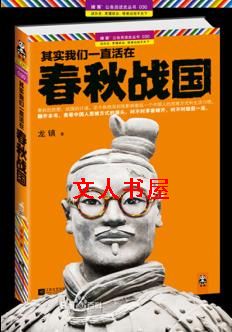阳谋春秋-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先生,鼓乐之声!还有仪仗!”驾车执事遥遥向前方一指。
吕不韦推开车窗一阵端详:“绕道,从城南插过去。”
执事一圈马缰正要回车,便听鼓乐队前遥遥一声高呼:“先生且慢——”随着呼喊,一个红色身影便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到得车前三五丈处便气喘吁吁地站住,展开一卷竹简尖声念了起来,“君上有,有诏:先生荣归故里,赐入国晋见,以全先生大名也!”
“噢!卫君要我晋见?”吕不韦惊讶地笑了,思忖片刻也不下车,只对着内侍使者一拱手,“既是如此,便请贵使上车同行。”内侍使者却连连拱手道:“卑微小臣,不敢僭越,只当为先生鼓乐开道。”吕不韦笑道:“我本一介商旅,谈何僭越?还是上车同行快捷了。”内侍使者还是连连拱手:“先生奉诏,便是国宾,小臣万不敢当!”吕不韦笑道:“贵使执意,我便去了。”脚下一跺,三马缁车便辚辚驰向古老的城池。
吕不韦的惊讶不是受宠若惊,而是莫名其妙。
卫国本是西周始封的王族诸侯,立国便是公爵之国。直到春秋之世孔夫子游说列国,卫国依然是春秋十二大国之一。孔夫子那令人尴尬的“子见南子”的故事,便发生在卫国。然则,自从进入战国,卫国便是江河日下。第十五代国君时,卫国自贬爵位,做了“侯”国。齐国灭宋后卫国大吃惊吓,在第十七代时再次自贬,做了“君”国。从此便颤颤兢兢如履薄冰,守在濮阳龟缩不出。
庶民却不然。殷商遗民们虽然成了周室诸侯的子民,却无心做周人社稷宗庙与僵硬井田的奴隶,对殷商老民驾牛车走天下的传统一心向往之,除了老弱妇幼固守桑麻,精壮男子不是离国经商,便是游学为士,总之是不安于枯守家园。百十年下来,卫国便出了许多大商名士。留在濮阳的老国人,便只有嫡系正宗的西周王族血统的子民了。这些守望社稷的君臣“国人”们自恃血统高贵,便分外矜持,既不能阻止殷商老民外流,便也不再理会这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与士子。殷商血统的大商名士们偶然回归故里,也从来不入朝拜会卫国君臣,与老周室老国人也是两不搭界。久而久之,便是个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大名士如商鞅者,竟是至死没有回过卫国。此等老传统之下,这个卫君却要“赐”吕不韦“入国晋见”,如何不令人莫名其妙?
说起目下这个卫君,却是战国中后期一个奇异人物。
要知奇异处,便先得说说末世君道。战国之世,一大批西周老诸侯国与洛阳王室的天子一道,都进入了风烛残年之期。同是末世衰微,各个老国的因应之道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便有五种法式:其一,燕国式。得地利之便,整军固守,拓边扩地而进入“战国”行列。其二,齐国晋国式。地广人众,新地主与士人崛起,庙堂高层恪守王道旧制而不思变革,终于被新贵们推翻替代,晋国成了魏赵韩三国,姜氏的齐国成了田氏的齐国。其三,宋国式。对先祖(殷商)功业念念不忘,不思变革而只图名号惊人,执意称王图霸而遭列强瓜分灭亡。其四,陈、杞式。既非王族诸侯,却又赖大圣贤祖先之名(陈国以舜帝后裔得封,杞国以大禹后裔得封)不思进取,逐渐被列国蚕食灭亡。最后一式,便是洛阳天子、鲁国、卫国式。此三国都是正宗的西周王族血统,天子王族不消说得,鲁国君是周公之后,卫国君是周武王弟康叔之后。进入战国之世,这三国都是执意恪守祖先旧制,丝毫不思变革,国中始终一片死寂波澜不惊。期间,鲁国虽有新士人新地主崛起之征兆,但也只是死水微澜而已,迅速便沉寂了下去。三国之君主,也是一色的无为守成,小心翼翼地不开罪任何强国,甚事不做,守到那日算那日。虽然如此,鲁国终究还是被齐国灭了。
从此之后,洛阳濮阳两君主便更加小心翼翼了。
同是无为守成,洛阳濮阳却也是小有不同。洛阳周天子是真正地任事不问,一应“大事”只交给太师处置。王族要依照祖制分封裂土,分便分,一片王畿便分封出了“东周”“西周”两个公爵“诸侯”,王畿之地便真正成了孤城一座。纵然如此,周天子依旧是整日沉湎于残破的乐舞,昏昏大睡绝不问事,此道以周显王为最甚。
卫君的“君道”不同处,便在于孜孜不倦地鼓捣这个小城堡中残留的臣民。目下这卫君名怀,时人便呼为卫怀君。此君癖好权术之道,纵然其天地小若濮阳一城,也是整日折腾乐此不疲。为了使臣下敬畏自己,卫怀君便派出十几个心腹小吏,扮成官仆进入几个县令与几个大臣的府中刺探其隐私。
一名县令很是简朴,一晚就寝,觉得身下有异,起身点灯,揭起褥垫一看,木榻草席已经破了一个大洞。次日清晨,县令尚未进入公堂,卫怀君的特使便到了。说是特使,其实只传一句话:“闻卿席破,特送新席一张。”放下草席便走了,直将个县令惊得一身冷汗!
白马津是卫国关市设卡收税之重地。一日,卫怀君派人扮做客商,过关时有意向关吏行贿三件玉佩,免了十金关税。当晚,关吏便被急召濮阳。卫怀君当头便是冷冷一句:“神目如电,小吏岂可暗室亏心?三玉何在!”关吏大惊失色,当即奉上尚未带回家的三件玉佩,并自请重罚。卫怀君却又是哈哈大笑:“吏有改过之心,处罚便免了。”小吏敬畏国君神明,便也加进了“发私”行列,卫怀君的神明之举便越来越多了。
除了“神明”,卫怀君还有一长,便是在后宫与大臣之间设置“螳螂黄雀”之局。卫怀君很是宠爱美妾泄姬,但又怕泄姬之父兄借势坐大,便对正妻魏妃表现出异常的尊崇,同时又分别密嘱魏妃与泄姬“发其不法”。对于已经零落稀疏的政务,卫怀君很是倚重信任掌管宫廷事务的长史如耳。怕如耳蒙蔽欺君,卫怀君便擢升下大夫薄疑为上大夫,名为襄助如耳,实则使之两相对抗。后来,这如耳与薄疑竟鬼使神差地成了同心好友。卫怀君觉察,立即同时罢黜两人,又擢升了另一对冤家互为“襄助”。人或不解,卫怀君便是神秘一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亦妙哉!”
卫国有了此等一个神秘兮兮活宝一般的君主,天下名士便是一片嘲讽。大名赫赫的荀子一针见血地指斥:“卫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治民也。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吕不韦一路忖度,卫怀君狡黠而善密事,必是探听得自己商旅有成,要派给自己一个“义举”。所谓义举,对于商旅十有八九便是“献金报国”。若仅仅是要钱,吕不韦无论如何是要出的,不管此君做何用场,都得出。否则,此君之口便会使你在天下沸沸扬扬五颜六色,你却找谁个辩驳?然则,此君若是别有所图,却该如何应对?从今日之势看,此君依然是牵绊衡平之术——鼓乐仪仗相迎以示其诚,君不出面以示其威,分明有求于人,却矜持得要“赐见”于人。此君自以为高明,恩威并出面面俱到,吕不韦却分明看到了一副苍白的可怜相便在眼前。
“濮阳义商吕不韦晋见——”内侍尖亮的通报在飕飕冷风中分外刺耳。
吕不韦不禁笑了,未曾谋面便将他定在“义商”之位,除了献金能有甚事?心下一松,便跟着导引内侍悠然进了陈旧残破的大殿,过得一座黑沉沉的大屏便紧走几步,在中央座案前深深一躬:“在下吕不韦,参见君上。”
“先生请起。”须发灰白的卫怀君虚手一扶,又矜持地一笑,“赐座。”
吕不韦正要到最近的案前就座,却见一名中年侍女悠然走来,伸手示意,将他领到了卫怀君左下侧的案前,算是完成了“赐座”礼仪。吕不韦释然一笑,便席地跪坐案前,却只看着卫怀君不说话。卫怀君笑道:“先生达礼,本君却是待士不周也。”吕不韦知道卫怀君这前半句是说他待君先话,算是通达礼仪,然后半句却是不明,如此国君果然能自责么?便一拱手道:“君召国人,原是常道,在下大幸也。”卫怀君目光闪烁间又矜持地一笑:“先生,无觉膝下有异乎?”吕不韦却不看座案之下,只摇头道:“在下愚钝,敢请君上明示。”卫怀君一怔,终于又是一笑:“先生座案之下,草席破洞矣!”
其实,吕不韦入座时便瞥见了破旧草席上的一个大洞,偏是浑然不觉,要与卫怀君兜兜圈子看他如何做作,此刻便肃然一拱:“物力惟艰。君上节俭为本,在下感佩不已!”卫怀君似乎愣怔了一下,却呵呵笑了:“原是捉襟见肘也,谈何节俭。”见这位君主终于显出困窘之相,吕不韦慨然笑道:“君上既有此言,在下愿献千金,以补宫室之用。”卫怀君却又矜持地端了起来:“果然,义商无虚也。然则,先生区区千金,却与社稷何补?本君之意,欲请先生撑持邦国,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吕不韦心下一惊,果然来了,这回显然不是金钱之事,却要小心应对,便谦恭笑道:“在下一介商旅,何能撑持邦国?若是事端之难,敢请君上明示。”
“区区细务,不难不难。”卫怀君笑得分外可人,“本君思忖:先生理财大家,可做我大卫关市大夫,专司十三处关卡税金。每年若能收得万金,三成便归先生。先生既有官身,又是公私两利,岂非立身上策乎!”津津乐道,竟很有几分得意。
骤然之间,吕不韦几乎便要放声大笑,然却生生憋住,满脸通红地皱着眉头拱手道:“君上妙算,在下却是愧不敢当。在下小本生意,年利不过百金,如何有运筹万金之大才?若是一年收不齐税金,在下倾家荡产事小,误国只怕事大。如此重任,在下断不敢当也。”
“足下大名赫赫,不想却是如此器局也!”看着吕不韦额头涔涔汗水,卫怀君不禁哈哈大笑,且立时将称呼变了,“才不堪任,足下倒也实在。不做便不做,至于大雪天出汗么!”笑得一阵,卫怀君突然压低声音,“然则,足下车马煌煌,却不象小本商人也。”
“君上神明。”吕不韦沮丧地苦笑着,“人云衣锦荣归,在下却是虚荣也。这煌煌车马,原是赵国大商卓氏之物,因了寄放在在下的车马客栈里,在下便趁着窝冬之期用了这车马。若不是借这车马,在下如何能在大雪窝冬时回乡?谁个不知阳春三月好上路也。”一番话唠叨仔细,当真一个活生生地小商人。
“噢——”卫怀君恍然点头长长地一叹,“既是如此,足下千金也就免了。”
“这却不能。”吕不韦连连摇头,“商旅游子,根在故国,献金原是该当!”
“足下忠心可嘉!然则,何年何月,你才能兑得千金之诺?”
“君上,”吕不韦怪模怪样地一笑,“在下正有千金在车,原是积攒多年要孝敬父母了,明日我便派人送来宫室如何?”
“既是在车,何须明日费时费力?”
“正是正是。”吕不韦恍然拍案,“君上跟我去拿,岂不利落?”
“也好。”卫怀君矜持地一笑,起身离座,“本君便成全足下一片忠心。”
吕不韦打量了一眼这个肥肥白白地君主,一挥手:“走。”便大步走了出去。卫怀君也再没了诸般礼仪,跟着吕不韦便出了大殿。到得车马场,吕不韦向驾车执事低声吩咐几句,执事竟惊愕得说不上话来,愣怔一阵才从车中提出一个沉甸甸地棕色大皮袋,有意一摇,一阵呛啷金声便夺人耳目!卫怀君一挥手,便有一个老内侍推着一辆手车走来,卫怀君上前两步,亲自接过大皮袋,便要解开袋绳验看。偏这吕氏钱袋是祖传手艺,袋口绳是密结暗筘,等闲人休想随意开得。卫怀君一阵摸索,却不得要领,便大是尴尬。吕不韦面无表情地向执事一点头,笑意憋得满脸张红的执事过来摆弄了几下,大皮袋便松了口。卫怀君甩手打大袋口,一片粲然金光赫然烁目!卫怀君又一挥手,内侍走过来便推走了皮袋。
卫怀君这才轻松地笑了:“足下献国千金,却要何赏?”
“但凭君上。”
“传诏。”卫怀君转身高声吩咐身后的长史,“赐吕门一世子爵,领封地三里。”话音落点,便大袖一甩径自去了。
缁车出了濮阳北门,吕不韦便大笑起来,想一阵笑一阵,笑一阵又哭一阵,最后终是软软地瘫在了坐榻上。驾车执事心下不安,便时不时回头透过车窗瞄得一眼,此时见吕不韦疲累得睡了过去,才从容驱车在雪原上走马北去。
行得片时暮色来临,遥遥便见前方凛凛刺天的胡杨林披着软软地晚霞隐隐红成了一片。驾车执事回头便道:“先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