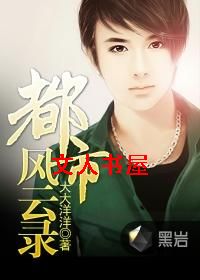机关风云-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天,白金水把文佳栩送上了北去的列车,文佳栩走得不声不响,白金水对外绝对保密。中南分局机关都知道少了个文佳栩,但谁也不知道具体去向。干部部门的人知道点内情,但中间拐了两道弯,也说不准了。文佳栩就这样永不回头地离开了这个养育过她的中南土地,踏上了新的生活征途。
文佳栩踏上远去的列车,心潮翻滚,回想起与白金水多年建立的私下感情在此刻就这样断掉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真正断绝情缘的时刻却又不那么容易断,真是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此一去就只有在梦中想了,不,不能断,我不能没有他呀。文佳栩对白金水多年的感情此刻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她突然猛回头,扒开上车的人群,跳下列车,冲上去紧抱白金水,放声痛哭高声嚎叫着:“我不走!我不能离开你呀!”
白金水此时也激情奔涌,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老脸上流下了酸楚的泪。他回想自己玩了一大圈的女人,只有文佳栩真正对他有情有义,要不是残酷的现实逼他们分手,他白金水决不走分离这步无奈棋。白金水想到这里心情又冷静下来,现实告诉他不分是不可能的了,两手抓住文佳栩的肩膀,轻轻地推开一点,热情地说:“小文啊,你对我的情下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但是现实无情啊,你必须走,感情是改变不了现实的,车快开了,你还是上车吧。”
“不,我死也不走!”
“不能啊,你就听我的吧,快上车。”
白金水一边说一边将文佳栩推开,文佳栩又冲上去将白金水抱住,嘴里反复叫喊着:“我不走,我死也不走……”
此时开车的铃声急切地响了,白金水心里急了,一把将文佳栩抱起就往车上走,上车后,白金水把文佳栩放下来,冷静地轻声说:“小文啊,别小孩子气了,走吧。”
说完,白金水返身下车,文佳栩跟了出来,白金水堵在门口不准文佳栩下车,但列车要开了,白金水只好请列车员帮忙,将文佳栩推上车,强行将文佳栩与白金水分开,关上了车门。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开出了中南站,文佳栩站在车门边号啕大哭,透过车门玻璃泪望站台上的白金水,列车无情地将他们的距离拉远,直到白金水在她的视野里渐渐消失,文佳栩才无可奈何地低下头来面对现实,列车员把文佳栩拉到卧车坐下,但是文佳栩的心情仍然没有平静下来,此时她深深地体会到,人只有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才觉得那个地方可爱,人只有真正分手的时候,才觉得不应该离开他。但是她也清楚的明白,无论她怎样激情奔涌,离开白金水,离开中南已成现实了,不可能再返回,现实告诉她,必须向前走,去营造新的生活……
白金水送走了文佳栩的当天晚上,他又来到星月岛陶花溪看守的别墅。白金水对这栋别墅情有独钟,对别墅里的人情爱甚笃。自从有了陶花溪,白金水来得最勤。就是因为陶花溪最年轻,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也丰满结实,青春是宝嘛,谁不喜欢年轻呢。正因为陶花溪年轻,白金水去的次数多了,客观上冷落了文佳栩。虽然白金水时不时也到绿洲湾文佳栩那里去,但明显的失去了往日的缠绵痴情。文佳栩动心怀疑过白金水可能有新欢,而情随事迁,由此而动过与白金水分手的念头。而陶花溪却没有想那么多,安守本份,遵守白金水给她订立的纪律。白金水来多来少,对于她来说没什么明显的反应,任他白金水来去自由。因此,这次白金水的到来,陶花溪与往日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反映,更想不到白金水这次找她寻欢,是来与她绝情分手的最后一欢。
白金水与陶花溪这最后一欢,也和绿洲湾与文佳栩寻欢一样,先欢后分。陶花溪与往日一样,满足过白金水的肉体发泄后,平静地睡下。白金水却不让她睡,把她抱在胸前,坐起来,靠在床背上。陶花溪反倒觉得奇怪,不解地问白金水:“怎么不睡下?”
白金水没有回答陶花溪的问话,却潸潸地流下了老泪,直到白金水的热泪滴在陶花溪的脸上,她才惊愕地转过身来,边给白金水擦泪水边问:“先生,你这是怎么啦?”
“小陶啊,这栋别墅我们只能住最后一晚啦,先生我舍不得呀。”白金水哽咽着掐头去尾的说上这么一句。
“先生,你能不能说清楚点,乡女我听着糊涂。”陶花溪不解地问道。
“从明天起,这栋别墅就不是我们的了,我已经把它卖了。”
“先生,那以后,我们住哪儿呀。”
“啊,对了,你跟我这么久,我还没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听口音很熟悉,好像跟我老家一带的口音差不多。”
“先生你老家是……”
“中边开远。”
“哎呀,我和先生是同乡啊。”
“你家住在开远什么村?”
“开远县云峰乡杨家村。”
“杨家村?那你咋姓陶?”
“我是跟我娘姓。听我娘说,她在怀我的时候,我爸与我娘约定,生个男孩就跟爸姓杨,生个女孩就跟娘姓陶,后来我娘生了两男两女,女的就都跟娘姓陶,男的就都跟爸姓杨。对了,我还有个哥姓白,也是在铁路上工作。”
“在铁路什么单位?”
“哟,这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是铁路上的,穿着铁路制服,戴上大盖帽,可威风啦。不过,他长大后,我只见过他两次,因为他从小就去了我远在中原的外公家,一直就没有回来过。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回老家来给我娘报喜。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他参加铁路工作的那一年,他穿着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回家向我娘辞行,其他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嗬,是这样。那他叫白什么名字?”
“不不,他不叫白什么名字,他叫陶……”
“你刚才不是说他姓白吗,怎么又姓陶了呢?”
“听我娘说,我哥小时候姓白,长大后是他自己改姓陶的。对了,我外公姓陶,他是我外公带大的,自然就改姓陶啦。”
“那他小时候叫过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好像是白……白循环,不不不,小名叫循环,大名叫白……哎呀,我也记不清了,我回去问问我娘就知道了。”
“不用问了,我全知道了,你哥叫白循。循环是他的小名。上大学后改成陶再生,他就在中南站当站长。我不但知道你哥叫白循,我还知道你娘叫陶春风。我和你娘陶春风是指腹为婚,你娘生下白循一岁后,我就参加了铁路工作。一年后我就与你娘解除了指腹为婚的封建包办婚约。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听说她改了嫁,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不知道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我的小情人正是她的小女儿,真是天报应,造孽啊。孩子,我对不起你呀,是我不好,我老糊涂,我不是人,我该死!好孩子,你就骂我,打我吧。”
白金水说得真切动情,流下了忏悔的眼泪。白金水虽然是指腹为婚,但毕竟是从小长大青梅竹马的同伴,她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本来就对不起她,再伤害了她的女儿,天理不容啊。白金水回忆他几十年的生涯,从得到第一个女人开始,几十年风风火火玩了一圈的女人,最后却又转回到第一个女人的女儿身下。
陶花溪听完白金水的述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个劲地伤心痛哭。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大情人却是娘的前夫,自己的干爹。她倒没有过多的想到对不起自己,而是对不起老娘,娘要是知道了该有多伤心,这不等于拿着利刀往娘心窝子里捅吗?她还有脸见人吗?她还能活下去吗?怎么世界上最伤风败俗的蠢事敢情叫她母女俩一块赶上了呢?真是老天无眼,老天不公,伤天害理呀。
白金水把哭成泪人儿的陶花溪紧紧地抱在怀里,但是这种贴心的依偎已失去了往日的情窦,完全被长辈对晚辈的爱抚所替代。陶花溪也没了往日温柔细腻的情爱柔情,换之而来的是撕心裂肝的痛恨。
“孩子,你不要责备自己,不要伤心难过,一切都是我的错,你是无辜的。”白金水此时说的却也是真心话。
白金水看到陶花溪如此伤心痛苦,担心她想不开,诚心诚意的开导她:“孩子呀,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情爱,做为一段错误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千万别再犯不应该犯的错误呀。你还年轻,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这样吧,我给你指条道路,这栋别墅我已经把它卖了,卖了五百万,我留一百万,你拿四百万回去,承包一片果树林。丰收的果子叫你哥白循,不不,陶再生,他是中南站的站长,他用火车把你的果子运出去,推销给果品批发市场,靠自己的劳动致富。我这点钱只不过帮你起步而已,千万别拿着它坐吃山空,不拿它承包果林,也要办个适应农民特点的实业,路就靠你自己去走了。”
陶花溪听白金水说要给她四百万,先是一阵惊喜,因为她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但是,陶花溪惊喜中又带着深深的忧虑,忧虑带着四百万回去怎么向娘交差,在外打工带几千块回去,才合符常理。带四百万回去娘肯定会追问来路,娘是不会收来路不明的不义之财的。回去说不清楚,母女之间还要产生矛盾。要是实话实话,又会剌痛娘的心,等于在娘愈合了的伤口上又划上更惨痛的一刀。她深知娘是不会要白金水这种肮脏臭钱的,遗憾的是母女两代人用肉体灵魂换来的钱,又不能自己亲自花,陶花溪为此而左右为难。
白金水了解陶春风,也理解陶花溪,如果她不收下他的四百万,白金水更加心神不安,更加内疚难平,因为这是他向她们母女俩唯一表达忏悔的方式。白金水见陶花溪为四百万犯难,进一步开导说:“孩子,我知道你犯难,因为你无法向娘交待,但是你娘已是日薄西山的人了。你年轻路还长,必须有个好的归宿,你就听干爹一句话,无论如何要把钱收下,回去后先不要跟娘讲出实情,先找个银行存起来,等办实业时再动用。你娘那里找机会再慢慢讲,一次不要说得太彻底,先用试探性的办法逐步提起你哥和我的情况,视她的反应程度再决定一次透露多少。不过,最好是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再说,先告诉她我危难消息,她尽管恨我,但在我危难之际,她就不会过份的记恨我的过去,而同情我现在的危难痛苦。记住,千万别告诉她我们那段错误的历史,否则,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原谅你。”
“您会有危难吗?”
“不不不,会,会的,比如我进……进医院,或者车祸什么的,都有可能的啊。”
白金水停了一会儿,又继续接着说:“好孩子,你理解干爹就好。这样吧,明天你就回去,此地不可久留,回去后,按干爹说的去做,找到自己的归宿,挺起腰杆做人,找个婆家,安分过日子。”
陶花溪任凭白金水怎么说,她也不想听也不想说了。
第二天,太阳从星月岛升起来的时候,砍一刀开着小车为陶花溪送行,砍一刀本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对一切都表现得莫衷一是,但对陶花溪失身的遭遇却表现得不同平常,惊人的表现出他那仅存的一点点人性味。他认为是他砍一刀害了她,是他砍一刀的罪过,他后悔不该把陶花溪送给白金水。送谁不行,却偏偏送了陶花溪。要是当初把陶花溪与柔桂花换过来也许就没这事了么。正因为砍一刀认为对不起白金水,也对不起陶花溪,才主动替白金水开车送陶花溪回家乡。因为白金水不好护送陶花溪,他认为他去送最合适,既能够洗刷自己一点罪孽,又能够保护陶花溪携带四百万安全返乡,因此,砍一刀亲自开车替白金水护送陶花溪回家。这一举动对于砍一刀来说却是反常的。在砍一刀玩世不恭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绝无仅有的一次。不但别人不理解,就连砍一刀本人也不理解。
砍一刀把陶花溪送到家门口,也不进门去坐坐,调转车头就往回开,陶花溪也不挽留,她恨砍一刀,恨白金水,恨世界上一切男人。她认为世界上的祸根是男人,无边黑暗是男人黑心制造的。但她无力与男人抗争,更无力改变她痛恨的现实,她想唯一能回避这个痛恨现实的就是以死抗争,离开这个世界。她现在要考虑的就是那四百万的问题,陶花溪并不是为个人考虑,因为她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呢,她要把钱给母亲留下,可又无法向母亲说明这钱的来历,说不清反倒不说的好。陶花溪把钱放在母亲的枕头下,一个人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跳河自杀了。
陶春风发现枕头下有四百万块钱,吓了一大跳,她八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穷了一辈子,平时捏几个小钱在手上都捏出水来,头一次见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