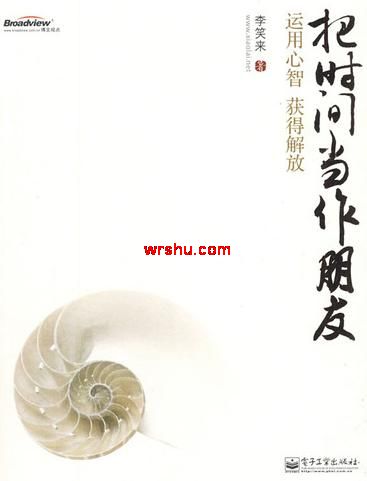时间旋涡(时间三部曲之三-出书版)-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一颗失落的灵魂,一个脆弱的人儿,也远比大多数人温顺。桑德拉希望待在这里的一周时间,能给奥林更多的是帮助,而非伤害。不过,她可不敢打包票。
当她从精神检测的房间出来,押送奥林来的警官仍在那里等着,这让桑德拉倍感意外。通常情况,警察送人来后,都会甩手就走。在回旋纪及其之后最糟糕的年头,州救助中心作为一个机构,俨然是为缓解不堪重负的监狱系统而存在的。这一应急需求尽管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不复存在,但时至今日,对于有明显吸毒嫌疑的轻微犯罪人员,州救助中心仍是一个垃圾倾倒场所。这之于警方,倒是方便得很,可对于工作时间长,经费短缺的救助中心员工,就远不那么方便了。一旦人送来,很少再有跟进的司法介入。就警方而言,移交就等于结案——说得更难听一点,就等于冲马桶。
尽管天气非常热,博斯一身休斯顿警服仍显得干爽整洁。他开始问起桑德拉对奥林。马瑟的印象。但因为早已是午饭时间,桑德拉下午的日程又排得满满的,她便邀请博斯一起去餐厅——员工餐厅,而不是奥林。马瑟肯定会感到失望的患者餐厅。
她取来星期一惯常的汤和沙拉,然后等着博斯。博斯也要了同样的饭菜。因为时间比较晚了,他们就随便找到一张空桌子。“我想对奥林做一些追踪调查。”博斯说道。
“这倒挺新鲜。”
“你的意思是?”
“休斯顿警局还做跟踪调查,我们一般不常遇到啊”我想也是。但奥林这案子里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的是”奥林“,她注意到,而非”犯人“或是”患者“。很显然,博斯警官对他很关心。”他案卷里我倒没见有什么特别的呀。”
“他的名字跟另外一起案件有牵连。这事我没法细说,不过我想问的是……他有没有提到他写的东西?”
桑德拉突然来了兴致。“有简短地提到过。”
“拘留奥林的时候,他身上背有一个皮包,包里有十来个格子笔记本,里面全写得满满的。他被人殴打时,拼命保护的就是这些东西。总的来讲,奥林都很配合,但我们不得不费了好些力气,才从他手里把那些笔记本拿过来。他要我们保证,必须要确保笔记本完好无损,而且案子一完结,必须马上还给他。”
“然后呢?我的意思是你们还他了吗?”
“暂时还没有。”
“因为既然奥林那么在乎那些笔记本,它们可能对我的测评工作会有帮助。”
“我明白,科尔医生。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问题是,那些内容与休斯顿警方办的另一案件有关。我这一直在誊抄,不过进展有点慢——奥林的笔迹不大好辨认。”
“我可以看看你誊抄的内容吗?”
“我来这里,想说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也想请你帮一个忙。你看完之后,能否不让它的内容进入官方渠道?”
这倒是个挺奇怪的要求。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回答。“我不明白你说的官方渠道是指什么。任何相关的观察分析,都得写进奥林的精神测评记录中。这是没得商量的。”
“你怎么观察分析都可以,只要不直接复制或引用笔记本中的内容。等我们完结一些问题后,就无所谓了。”
“奥林在我手中只七天时间,博斯警官。七天后,我要提交一份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可能彻底改变奥林。马瑟的命运,这一句她没说出来。
“我明白,我也没想插手。我感兴趣的,是你对他的心理测评结果。简单说,我想从你那里得到的,是你对奥林所写东西的意见。特别是那些东西的可靠性。”
桑德拉终于有点明白了。奥林所写的某些东西,对一宗悬案具有潜在的证据价值,博斯想知道那东西(或其作者)的可信度有多大。“如果你想让我在什么法律诉讼中作证——”
“不,绝非如此。只是私下意见。你给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以不违反患者保密规定或任何其他职业规范为原则。”
“我也说不好——”
“你读完之后,可能会清楚一些。”
博斯的一片诚恳,最终说服了她,尽管她仍有所保留。那些笔记本,以及奥林对它们如此的迷恋,让她着实感兴趣。如果发现有什么相关的临床证据,她可就顾不得对博斯所做的承诺了。她首先得忠实于自己的患者,她想博斯一定能明白这一点。
对于她的条件,博斯毫无异议。然后,博斯站起身,剩下部分沙拉,以及在精挑细选吃掉櫻桃番茄后铺垫在下面的莴苣叶。“谢谢,科尔医生。谢谢你的帮助。我今晚就把第一批内容发到你邮箱里。”
他递给她一张自己的休斯顿警察局名片,上面有他的联系电话、邮箱地址和他的全名:杰斐逊。阿姆里特。博斯。桑德拉嘴里重复着他的名字,一面目送他走向餐厅门口,消失在一群白大褂医生之中。
忙完一天的例行诊断工作,在落日长长的余晖中,桑德拉驱车回家去。
日落常常让她想起年份特别短促的回旋纪。那时节,太阳膨胀变大,已是苍老不堪。在西天长空中,它看上去之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只是科技手段下的一种幻觉。真正的太阳已经苍老膨胀,犹如一个巨型的怪物,在太阳系的中心正迅速走向寂灭。她所看到的地平线上的景象,是假想智慧生物运用超乎想象的强大技术,对太阳致命的辐射进行过滤处理后的结果。多年至今——自从桑德拉长大成人以来——人类就一直生活于这种默然无声的外星生物的掌控之下。
天空蓝得刺眼,只在东南边陲有玻璃质的珊瑚一样的淡淡云彩,给投下一丝的暗影。据天气预报播报,休斯顿市区的气温跟昨天一样,高达105华氏度。新闻访谈全是关于即将发射的白沙火箭的内容。这些火箭的目的是要往上层大气注入硫磺气雾剂,以阻止全球变暧。对此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非它们之所为——假想智慧生物没提供任何保护措施。它们只保护地球免遭膨胀的太阳的破坏,至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显然不在它们职责范围内。不言自明,这应是人类自己的事儿。而与此同时,一艘艘油轮正接连不断地徐徐驶入休斯顿港航道,船上满载的是通过星际隧道,从新世界天赤星输送而来的充足而廉价的原油。拿两个星球的石油来烹煮我们,桑德拉心想。车内空调超负荷运转,呜呜地发出抗议,但她仍感觉凉意不够。
自打从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实习期满,然后到德克萨斯州救助中心工作以来,桑德拉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心智遭受困扰的患者做测试——很简单,绝大多数正常成年人都能轻松通过——然后签发过或不过的诊断书。受试者是否有正确的时空意识?受试者是否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不过,桑德拉想,要是让全人类都参加这测试,结果未必乐观。受试者思维混乱,常常伴有自虐行为。受试者往往不惜以自己的长期利益为代价,以寻求短暂的满足。
她回到位于镜湖小区的公寓时,夜幕已经降临。此时的气温也略略降了一两度。她用微波炉做好晚餐,打开一瓶红酒,一面查看博斯的邮件是否发过来。
邮件已经发了过来。有好些页,说是奥林。马瑟写的,可第一眼她便觉得怎么看怎么不可能。
她将文稿打印出来,在一张椅子里舒适地坐下,开始看起来。
开篇第一句:我叫特克·芬雷。
第二章 特克·芬雷的故事
我叫特克·芬雷,故事中所记述的,是我现在的生活,而我曾认识、曾爱过的一切的一切,都早已死去,都早已不再。故事始于一颗行星的沙漠中,我们过去管这个星球叫“天球赤道利亚”,简称“天赤星”。这颗星球已经终结——不过,也难说。这些便是我的记忆,亦是事实。
一万年,差不多也是我离开那世界的时间长度。想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一度,我几乎唯一就只记得这个。
我醒来时,置身旷野,身上一丝不挂,感到头晕晕的。空旷的蓝天里,太阳毫无遮拦地将它的光芒狠狠投射下来。我感到渴极了,渴得要命,浑身酸痛,舌头沉重,像是死在了口腔里。我挣扎坐起来,却差点儿翻倒。我视线模糊,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这地方来的。我甚至也记不起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我唯一知觉并确信的是,一万年(可谁曾计数过?)已过去了。想到此,心里就一阵慌乱。
我竭尽全力纹丝不动地坐稳,闭上眼,直至一阵可怕的眩晕过去。然后,我抬起头,努力想要弄明白眼前的景象。
我身在露天,看样子是一片沙漠。数英里之内,就我目力所及,不见一个人影。不过,我也并非唯一的存在:一大群飞行器从头顶上方驶过,速度很慢。飞行器造型奇特,看不出是什么让它们悬空不落下来的,因为它们既没翅膀也没旋翼。
我暂时不再去理会那些飞行器。当务之急,我需要找个阴凉的地方,我的皮肤已被日光灼伤得红通通的。不知道我已在阳光下暴晒多久了。
沙漠里,一直到天际,都是实实匝匝的沙地,上面东一块西一片地散落着像是巨型玩具的碎片:一个圆弧形的半只蛋壳样的东西,少说有十英尺高,灰绿色,在几米外的位置。远处还有一些类似形状的残片,色彩明丽,虽都已开始褪色。那景象,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荼会,最后乐极生悲。更远处,是连绵的山峰,看上去像被熏黑的下颌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金属粉尘和滚烫岩石的味道。
我往前爬行了几米,躲进破裂的蛋壳阴影里。真是凉快,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第二所需要的是水。然后也许还需要找点东西把自己的身体遮掩起来。但稍稍一动,我又感到头昏目眩。那些造型奇特的飞行器中,有一艘似乎一直悬在头顶上方。我试图挥动手臂,吸引它的注意,却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我眼一闭,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我躺在一个担架样的东西里,被人抬着。
抬担架的人身穿黄色制服,口鼻上戴着防尘面罩。一位穿着同样黄色服装的女子走在我一旁。我们目光相遇,她说请尽量保持镇定。我知道你被吓着了。我们必须得赶快,但请相信我,我们会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几艘飞行器降落下来,我被抬上其中一艘。黄衣女子跟她同伴说了几句,不知道讲的什么语言。捕获我或者救助我的人让我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站住,而没有倒下。一扇门降落下来,将沙漠与天空关在了外面。飞行器内浸染着比外面柔和得多的光亮。
身穿黄色无袖套衫的男男女女在我周围忙上忙下,但我一直盯着刚才说英语的那个女子。“镇定。”她握着我的胳膊说。她身高不过五英尺多一点。摘下面罩后,她模样跟人没什么两样,这让人心里踏实多了。她棕色皮肤、黑色短发,看面相有些像亚洲人。“你感觉怎样?”
那可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勉力耸了耸肩。
我们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她护送我到一个屋角。墙面上平滑地伸出一个床一样的平面体,随之伸展出来的还有一个支架,可能是医疗设备。黄衣女子让我躺下。其他士兵或者是飞行人员——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身份——没理会我们,自顾地忙碌着,操作沿墙设置的控制平台,或急匆匆地奔向飞行器的其他房间。我有一种电梯上升的感觉,估计我们已经起飞了,尽管除了说话声——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没有听见其他任何声响。没有颠簸,没有震动,没有涡旋。
黄衣女子将一根钝头的金属管压在我前臂上,然后又在我胸廓上压了一下。我感觉心中的紧张不安放松下来,渐渐陷入麻痹。我猜是被注射了麻药,但心里并不太在意。不再感到口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子问道。
我声音粗哑,告诉她我叫特克·芬雷。我告诉她说,我出生在美国,最近一直住在天赤星上。我问她是谁,来自什么地方。她笑笑说我叫特蕾娅,来自于一个叫涡克斯的地方。”
“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那地方吗?”
“是的。我们很快就要到了。尽量睡一会儿吧,如果睡得着。”
于是我闭上眼,尽可能地回顾自己的一点一滴。
我叫特克·芬雷。
特克·芬雷,回旋纪末期出生,什么工作都干过,包括临时短工,水手,小型飞机驾驶员。后来设法搭乘一艘近海货轮,穿越圆拱形的星际隧道(因为是拱形的,过去也有人叫它“大拱门”),到了天赤星,在那里的麦哲伦港待了一些年。遇见一个叫丽丝。亚当斯的女孩。她在寻找她父亲。我们四处找寻,闯人一帮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