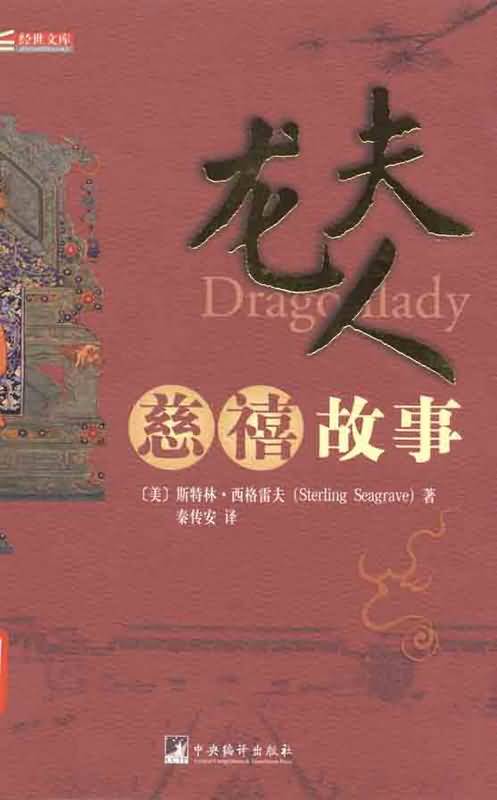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呐,躺在担架上,身旁有医生与护士……嗐,一想起医生喽、尸体喽,思路就会变得病态、感伤;同时,这种幻觉又会令人感到一些兴奋的乐趣,一种过分的激动,从而提醒人们,不要再想这类事情了——对艺术极有害,对友谊极有害。不错。当下,救护车拐了弯,驶过托顿汉考特路,凄厉的铃声不断回响,隔条街都能听见,甚至再远些也听得见;此时,彼得·沃尔什又回过头想:这正是孤独的好处,一个人独处时可以随心所欲。要哭便哭,只要没人瞧见。然而,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落落寡合;他不会拣恰当的时机哭,或笑嘛。眼下,他伫立邮筒边,兀自寻思:我生来就有这脾性,此刻就要淌眼泪呢。为什么?天晓得。敢情是由于什么美感,或因为整天劳累过度;从访问克拉丽莎开始,天气那么热,又那么紧张,五花八门的印象接二连三,真叫他精疲力竭;那些缭乱的印象犹如水珠,一滴一滴,流入心田底层,凝固了,深邃,黑幽幽的,谁都永远摸不透。大概由于这一点,就是生活的奥秘,彻底的不可侵犯的奥秘,他觉得生活恰如一座陌生的花园,迷魂阵似的,令人惊奇;真的,有些时刻简直叫人诧异得喘不过气来;此刻,他站在不列颠博物馆对面的邮筒旁,便是这样的时刻,刹那间万物浑然一体;救护车,生与死。好像他的灵魂被汹涌的情感冲击着,升华到高楼之顶,而他的躯体空空如也,宛如白茫茫一片荒滩,惟有零零星星的贝壳。他之所以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落落寡合,正由于这脾性——多愁善感。
有一回,克拉丽莎跟他在某处乘公共汽车,坐在上层;那时,她很容易激动,至少表面上如此,一忽儿沮丧,一忽儿兴致勃勃,活跃得很,是个挺有意思的伴侣;她会从公共汽车上层望下去,认出一些古怪的小巧的景物、名称或熟人;当时,他俩常在伦敦四处逛荡,猎奇探胜,有时,从卡利多尼安商场带回几大袋珍贵的东西;那时,克拉丽莎有一种理论——他们有成堆的理论,正如一般青年那样,老是理论不离口。他俩的理论是要阐述那失望之感——不了解人,也不被人了解。人们怎能相互了解呢?你同某人每天见面,然后分离半年,甚至几年。他俩都认为,这是令人失望的,人与人之间多隔膜呵!然而,当她乘公共汽车,驶上谢夫茨伯里大街时,却说,她感到自己与万物为一,不是在“这里、这里、这里”(她拍拍座位的靠背),而是到处存在。车子驶上谢夫茨伯里大街时,她手舞足蹈。她这人就是这般模样。所以,要了解她,或任何人,必须找出和她性情相投的人,以至合她心意的地方。她有一种奇异的本能,会和她从未交谈过的人息息相通——街头一个女人,站柜台的一个男子,甚至树木,或谷仓。她终于形成一个先验论(84)式的观念;正因为她怕死,这一观念安慰了她,让她相信,或自称相信,她所谓的幽灵(即一般人所说的肉体),同无形之魂相比,是昙花一现的,而后者充塞于天地之间,因此可能永存,经过某种轮回,依附于此人或那人身上,甚至死后常在某处出没。也许……也许……
当他回顾两人之间漫长的友情时(将近三十年了),感到她的理论还真有些道理。他俩真正的相会是短暂的,断断续续,常常是痛苦的,因为他有时到外地去了,有时遭到干扰(比如今天早晨,他刚要开口同克拉丽莎叙谈,伊丽莎白闯进来了,像一匹小马,俊美而缄默),尽管如此,这些约会对他的生活起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仿佛有人给你一粒谷物的种子,棱角尖锐,叫你拿着挺不舒服——那些幽会正是如此,时常使他痛苦不堪;可是,跟她分手期间,蛰伏了好多年后,在完全不相干的地方,种子萌芽了,苞放了,清香四溢,你不由地触摸、品味、环顾,尽量感受和理解。就这样,有时她忽然会到船上来跟他相会,或在喜马拉雅山间,都是受了最古怪的启示而冲动的(比如有一次,由于萨利·赛顿,那慷慨而热情的傻姑娘,看见蓝色的绣球花便想到他,克拉丽莎立即来找他了)。她对他的影响,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大。而且总是出其不意,没约好就来了,却又一副淑女模样,爱挑剔,冷若冰霜;也有罗曼蒂克的时刻,令人醉心,使人想起明丽的田野,或英国特有的收获季节。他多半在乡间而不是在伦敦与她幽会;在布尔顿,一幕又一幕的情景呵……
他回到旅馆,穿过大厅;里面摆满了浅红色椅子和沙发,点缀着花木,叶瓣尖细,看上去枯萎了。他掏出房门钥匙。年轻的侍女递给他几封信。他上楼去……以前,他多半在布尔顿同她相会,常在残夏时节;当时,他和熟人们一样,在布尔顿待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起先,她跟他站在山顶,双手掐着头发,斗篷迎风飘舞,指点着,对他嚷道:她看见赛汶河在山下流呐。有时,他俩到林中去,她用水锅烧水——手可不灵巧呢;炊烟袅袅,在他们脸上缭绕,她那嫣红的面孔在烟雾中隐现;向一所茅屋中的老农妇要水喝,老人家还到门口看他俩走咧。他们总是步行,别人大都驾车出游。她对乘车厌倦了,并且讨厌一切动物,除了那只狗。两人沿路漫游,走了不知多少英里。忽然她岔开去,辨明方向,然后引领他回头走,穿过田野;一路上他俩争论不休,讨论诗,议论人,还谈论政治(那时她是个激进分子);谈得对四周景物视而不见,除非她止步的时候,这才对一片景色或一株树赞叹不已,还叫他一起观赏呢;尔后再向前走,穿过布满茬儿的田野,她带头,忽而摘一朵花,说是给姑母的;她虽然娇弱,却爱步行,从不感到吃力;终于在暮色苍茫中,返回布尔顿了。晚餐后,那老头儿布赖科普夫掀开钢琴,弹起来,还唱呢,可毫无腔调;他俩舒舒服服地靠在安乐椅里,忍住笑,终于憋不住,笑出来,笑个不停——无缘无故地傻笑。他俩以为布赖科普夫什么都没瞧见哩。翌日早晨,她就在屋子前面跳来蹦去,活像一条摇着尾巴的小狗……
哦,是她的来信!蓝信封,是她的笔迹。他不得不看。又约他见面,肯定是痛苦的!念她的信真得费好大的劲儿。“我必须告诉你:见到你太高兴啦!”就这么一句话。
然而,这封信却叫他心烦,使他懊恼。要是她不写多好呵。他已经思绪纷乱,再来这样一封信,就好比肋骨被人戳了一下。她为什么不让他清静呢?说到底,她已经同达洛卫结婚,而且好多年来过得十分幸福嘛。
这种旅馆也够呛的。根本不能叫人舒泰。来往的旅客太多,帽架上不知挂过多少帽子了。再想一下,连苍蝇也在不知多少人的鼻子上叮过了。至于表面上使他眼睛一亮的整洁,其实并非整洁,而是光秃秃、冷冰冰,不这样才怪呢。每天清晨,一个瘦瘠的女总管要巡视一番,四处窥探,吩咐清教徒式的使女们把东西擦得锃亮,好像下一个顾客是一块腿肉,要用擦得一干二净的大盘儿来盛咧。睡觉嘛,一张床;要坐嘛,一只靠背椅;刷牙刮胡碴子嘛,用一只平底杯,还有一面镜子。他把书呀、信呀、睡衣呀,随意乱扔,同这冷漠而古板的气氛颇不协调。正是克拉丽莎的信使他悟到这一切的。“见到你太高兴啦,我必须告诉你!”他折起信纸,丢在一边;再也不想看了!
要让他在下午六点钟收到这封信,她必定在他离开后立即坐下来写,贴上邮票,叫人去寄掉。正如人们所说,她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的访问使她心烦意乱。她必定感触很多,在吻他手的刹那间,觉得懊悔,甚至羡慕他,也许还想起他以前说过(从她的表情看得出来):万一她嫁给他的话,他俩将改造这可恶的世界。如今她却是这般模样,到了中年,平庸得很;于是她凭着不可遏制的活力,迫使自己撇开这一切,不再顾影自怜,因为她有一股生命力,坚毅,有韧劲,足以克服任何障碍,使自己顺利地进展。这种力量简直无与伦比。诚然,他走出房间后,她会顿时反应。她将为他觉得十分难过,并且考虑自己究竟能干些什么,给他些乐趣(他总是缺少这个);他能想象她泪流满面,赶紧到写字桌边,飞快地写下一句话,就是他看到的那一句:“见到你太高兴啦!”这是她从心坎里感到的。
彼得·沃尔什解开靴带。
可是,纵然他们结了婚,也不会如意的。说到底,她倒是嫁给那个人,自然得多哩。
真怪,不过事实如此,许多人感到这一点。彼得·沃尔什干得相当体面,恰如其分地担任一般职务,讨人喜欢,但是人们觉得他有点儿怪,有时好摆架子——真怪,恰恰是他,尤其在他两鬓花白之时,却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神色,一种矜持的样子。正是这神态使女人觉得他富于魅力,看来他并非地道的男子汉,而她们喜欢这感觉。他有一种不寻常的素质,或者说,骨子里与众不同。兴许他有点书呆子气——每次来看望你,都会拿起桌上的书来读(此刻他就在读什么书,靴带拖在地板上);或者说,他是一位绅士,这表现在他磕掉烟斗里烟灰时那副派头,当然还有他对女士们彬彬有礼的风度。然而,任何没有头脑的姑娘都能易如反掌地摆布他,这情景妙极了,却也可笑得紧。不过,那姑娘别以为得计,可能要上当呢。因为,尽管他非常随和,而且由于他有教养,性情愉快,跟他交往真有趣儿,实际上,这是有限度的。那天,克拉丽莎说什么来着……别想了,别想了,他看穿了。他受不了——说什么也受不了。有时,他会同其他男子一起开玩笑,大叫大嚷,摇来摆去,捧腹大笑。他真是个男子汉,可不是叫人敬畏的大丈夫——这样反而好;比如,戴西心想,他就不像西蒙斯少校那么威严,一点儿也不像;尽管她已经有了两个小孩,还常在内心比较两个男人呢。
他脱掉靴子,把口袋掏空,漏出随身带的小刀和戴西在阳台上拍的快照——戴西,一身缟衣,膝盖上蹲着一只狐(85),妩媚极了,黑里俏,从未见过她这样美的。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比克拉丽莎自然多了。没有神经质的激动。毫无麻烦。既不疙瘩,也不烦躁。一帆风顺。阳台上那可爱的标致的黑皮肤姑娘,她提高嗓门声称(他能听见她的声音):当然,当然,她会把一切献给他的!就这么大声叫嚷(她毫无顾忌):你要怎样就怎样!她嚷着,向他奔来,跟他相会,不管旁边有什么人在瞧。她只有二十四岁嘛。但已有了两个孩子。唔,哦!
嘿,嘿,到了这把年纪,还惹来这么些纠葛,真是一团糟。当他在子夜时分惊醒时,忽发奇想:跟她结婚如何?对他来说,再好也没有了,可是她呢?关于这问题,他曾对伯吉斯太太推心置腹地讲过,因为她是个规矩人,不是长舌妇。她认为,他离开英国期间(表面上是去找律师商量),戴西可能重新考虑,想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伯吉斯太太说,问题在于她的处境,社会习俗的阻碍,要放弃孩子,等等。无论如何,将来总有一天她会守寡的,于是在郊区徘徊,甚至可能不顾体面,什么都干得出来。(她说,这种涂满脂粉的女人会落到那步田地的,你懂嘛。)但是彼得·沃尔什对她这番话嗤之以鼻。他还不想死哩。他思忖,她必须自己判断,自己拿主意;他穿着短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着这些心思,一面把衬衫抚平,因为他也许要去参加克拉丽莎的宴会,也许上哪个娱乐厅去,或者待在家里,念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作者是他以前在牛津的一个熟人。嗯,倘若他终于退休的话,这就是他要做的——写书。他要重返牛津,到波特雷图书馆(86)去查资料。那可爱的标致的黑皮肤姑娘会跑到平台尽头,挥舞着手喊道,她压根儿不管人们怎么议论哩。可是一切都枉然。他仍然待在旅馆里,就是她认为了不起的男子汉,无瑕可击的绅士,那么魅人,仪表堂堂(至于他的年纪,她根本不在乎);眼下他却在勃卢姆斯伯里区的旅馆里,刮胡子,梳洗一番,放下剃刀,拿起水壶,一面继续想:以后要到波特雷图书馆去查资料,弄清楚他感兴趣的一些琐事。随便碰到什么人,都要好好聊一下,谈得忘了时辰,愈来愈不准时进餐,连约会都忘了;当戴西要他吻一下,亲热一番(她会这样要求)的时候,他却三心两意(尽管他真心爱她)——总而言之,就像伯吉斯所说,她最好忘掉他才能幸福些,或者,仅仅在记忆中想起他在一九二二年八月里的模样,于暮色中伫立在十字路口;当时她乘着马车离去,紧靠着后面的座位,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