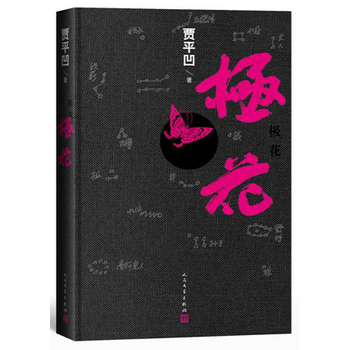极花-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土豆糍粑,烙土豆粉煎饼,再就是炖一锅又酸又辣的土豆粉条。
吃过了饭,地里没活,黑亮爹就又开始凿石头了。天热光着了上身,脊背上有两排拔火罐留下的黑坨。一块半人高的石头在半晌午时开始生出一个女人头,接着露出脖子,露出肩,只差着要从石头里完全走出来。瞎子收拾起了石磨要磨粮食,他过四五天就磨粮食,好像家里有磨不完的粮食,其实也就是苞谷、荞麦和各种颜色的豆子,他是把地里家里该干的体力活都干过了,没啥干了,就推磨子,这样就显得他的存在和价值似的。黑亮帮着从窑里取出了笸篮,经过他爹的身后了,说:村里有了那么多了,你还刻呀?他爹说:给你刻的。黑亮说:人不是在窑里了吗?他爹说:我心里不踏实,刻个石头的压住。一簸箕苞谷倒上了磨盘顶上,石磨眼里插着三根筷子,瞎子抱了磨棍推起圈儿来。那圈儿已转得我头也晕了,而石磨眼里的筷子不停地跳跃,又使我心慌意乱。在老家我是最烦推石磨,娘把磨出来的麦面在笸篮里罗着,手指上的顶针叩着罗帮儿发出当当的节奏声,那时候我和弟弟就抱了磨棍打盹了,停下脚步,娘就会说:停啥呀,停啥呀?我和弟弟还闭着眼便继续推着磨棍转圈儿走,甚至这么走着并不影响着梦。瞎子没有顶针,他磨一遍了也筛罗,筛,罗没有声响。
窗台上爬着一只旱蜗牛,它可能是从夜里就开始从窗台的右角要爬到左角去,身后留着一道银粉,但它仅爬了窗台的一半。
硷畔下又有谁和谁在吵骂了,好像是为鸡偷吃了晒席上的粮食而吵的,吵得凶了就对骂,全骂的是男女生殖器的话。接着又有人在西头向南头长声吆喝,说村长新箍了一孔窑让去他家喝酒哩你去不去?应声的就问带啥礼呀?吆喝的说你带啥礼我不管,我买了条被面子,再带个媳妇去。应声的说你哪有媳妇?吆喝的说我没媳妇就不会带别人的媳妇?!应声的说那我也带个别人的媳妇!黑亮,哎——黑亮!那人又隔空吆喝黑亮也去喝酒。黑亮爹在嘟囔:那是叫人喝酒哩还是索礼哩?黑亮往硷畔下瞅了一眼,没有应声,给他爹说他得到店里去,要和立春腊八谈代销的事呀,立春腊八兄弟俩太奸,当初他要代销,他们要直销,现在却又让他代销,他就偏提出抽百分之十二的成。他爹似乎没吭声,他就进窑提了半桶水,又进我的窑里来拿草帽子,诡异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提水干啥?我懒得理他,他说:给醋瓮里添呀,这你不要对人说。
黑亮走了,整个中午和下午都没回来,两顿饭是黑亮爹把饭碗端来放在了窗台上。他放下了碗,敲敲窗子,自个就退到窗子旁边,喊:吃饭喽!这是给瞎子说的,更是在给我说。碗沿上不时有苍蝇趴上去,他就伸了手赶。为什么不吃呢,我肚子早饿得咕咕响,就从窗格里把碗取进来,用手擦拭碗沿。黑亮爹说:没事,那是饭苍蝇。苍蝇还分屎苍蝇饭苍蝇吗?!但我没给黑亮爹发脾气。
天差不多黑下来,白皮松上的乌鸦开始往下拉屎,黑亮才提了个空桶踉踉跄跄回来。他是喝高了,不知是不是在村长家喝的,进了窑就把窑门关了,竟然把一沓子钱往我面前一甩,说:你娘的,给!往常晚上回来,他都是坐在那里清点当天的收入,嘴里骂着村长又赊账了,把那一沓子纸票子和一堆硬币数来数去,然后背过身把钱放在了柜子里,上了锁。但他喝高了把钱甩在我面前,我想起了爹还活着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行为,娘见爹把钱甩在面前,娘是一下子扑过去把钱抓了,就去酸菜盆里舀浆水让爹喝,再是扶爹上床,脱了鞋,埋怨喝成啥了,酒有多香的?!我一直看着娘,觉得娘太下贱,娘却对我说:你爹喝了酒才像你爹。我才不学我娘的样,甩过来的钱沓子在我面前零乱地活着,我不理,钱就扑沓在那里,气死了。
* *
白天里我等着天黑,天黑了就看夜里的星,我无法在没有星的地方寻到属于我的星,白皮松上空永远是黑的。
这一天,太阳下了西边梁,云还是红的,老老爷就坐在了磨盘上,我以为他又要在夜里看东井呀,但前脚来了猴子,后脚就再来了那个叫梁水来的,猴子是来说他前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割草哩一条蛇钻到他屁眼了,问老老爷这是啥征兆?老老爷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梁水来就来取压制好的极花,他拿了极花就亲了一口,说:极花极花,我也把你敬到中堂去,给我也来个胡蝶!还扭头往我的窑窗看,我把头一偏,呸了一口。猴子说:这灵验吗,那我也要一棵。老老爷说:中堂是挂天地君亲师的。黑亮爹说:今日是咋了,来这么多人,来见老老爷就都空着手?!我瞧见硷畔上果然又是四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拉着一个孩子,孩子是兔唇,不愿意去,那人说:狗蛋,给老老爷磕头,让老老爷给你起个名字。旁边人说:已经叫狗蛋了还起名?老老爷却问孩子多大了,是啥时辰生的?然后翻一本书,琢磨了一会儿,说:叫忠智吧,让我起名,就要叫哩。那人说:要叫哩,要叫哩,狗蛋,再给老老爷磕头。老老爷说:叫忠智。那人才说:哦,忠智!按着孩子头又磕了三下,父子俩就走了。旁边人就说老老爷给村里所有人都起过名,但又都叫小名,比如马德有叫猴子,王仁昭叫拴牢,杨庆智叫立春,杨庆德叫腊八,梁尚义叫水来,李信用叫耙子,刘孝隆叫金锁,刘德智叫金斗,梁显理叫园笼,王承仁叫满仓,王贵仁叫础子。水来说:起贱名好养么。猴子说:以后都叫我马德有呀!老老爷,以后谁要不叫你起的名,你就再不起名了。老老爷说:不起名那咱这村子百年后就没了。猴子,猴子,黑亮爹在叫。猴子跑过去,说:我叫马德有。黑亮爹说:你能配上德有?猴子就是猴子么,你帮我去把厕所墙旁的那块石头搬过来。猴子说:白出力呀?黑亮说:锅台上还有一张饼哩。猴子进了窑,拿饼吃着去厕所那儿了。
村里人原来都还有另外的名字,不知老老爷给黑亮起了什么名,我便也觉得我的名字不好。当初那个晚上,老老爷得知我叫胡蝶,他说了一句胡蝶是前世的花变的,他的意思是我的名字不好?如果胡蝶今生就是来寻前世的花魂的,而苦焦干旱的高原上能有什么花?我也曾经是憧憬过我将来了会嫁到哪儿会嫁给个什么人,到头来竟是稀里糊涂地被拐卖到这儿面对的是黑亮?!我想让老老爷能给我也起个名,但磨盘那儿人实在太多,我无法开口。
硷畔上还有人来找老老爷,或许村里闲人太多,瞧见老老爷这儿人多,也就来凑热闹吧。一阵吵闹声,就见三朵扯着一个人往硷畔来,那人犟得像毛驴,一到硷畔上就抱住了黑亮爹凿的一块大石头,三朵就扯不动了,三朵说:毛虫,咱去见老老爷,你也是给老老爷发过誓的,你能让你爹两天了不吃不喝?毛虫说:我不是去镇上了吗,我只说当日就回的,谁知道有事耽搁了么。三朵说:有啥事,你去耍钱了!你只图赌哩还知道不知道你爹瘫在炕上?!毛虫说:那是我爹,又不是你爹。三朵说:是你爹,你对你爹好了,不是对我爹好,可我就高兴,你对你爹不好了,也不是对我爹不好,我还是不愿意。你去给老老爷认罪去!毛虫说:他又不是庙里的神。三朵说:他不是庙里的神,但他是老老爷!毛虫说:他能给我一碗饭还是给我一分钱?我认他了他是老老爷,不认他了就是狗屁!三朵抽了一个耳光,骂道:你狗日的不怕造孽!毛虫要回手打,三朵又一脚,把毛虫踢坐在硷畔入口地上,三朵还要扑过去踢,毛虫翻起身就跑了。
这边三朵打毛虫,磨盘边的人都静下来面面相觑,待毛虫一跑走,齐声骂毛虫,老老爷叹了一口气,说:这忘八谈!猴子说:把老老爷气成啥了,也骂王八蛋!老老爷说:不是王八蛋,是忘八谈。三朵说:忘八谈,啥是忘八谈?老老爷说:八谈就是德孝仁爱,信义和平。说毕,起身回他的窑里去了。老老爷一走,把众人晾在那里。他们说:回,回。就也散了,各自回去。
我压根没有想到多热闹的硷畔就这么快地空落了。天整个黑下来,还刮开了悠悠风,靠在水井轱辘上的那扫帚在吱吱响,扫帚在哭吗还是在自言自语着什么?我在窗前待了一会儿,在窑壁上刻下新的一条道儿,就把煤油灯点着了。
脑子里还在琢磨我的名字:胡蝶能寻到什么花呢?这土窑里,唯一的花就是那极花,花是干花,虫子也是死虫子。黑亮在镜框里装了极花就来了我,村里那么多光棍效仿着也在镜框里装极花,那么,我来寻的就是极花?我一下子从墙上取下了镜框,拆开来,拿出了极花,说:你就是我的前世吗,咹,我就是来寻你的?说了一遍,再说几遍,不顾及硷畔上有没有黑亮爹,也不管狗在咬还是毛驴在叫,鼻子里一股子发酸,眼泪流下来,就觉得极花能听见我的话,也能听懂我的话。我便把极花对着窗口,指挥着风:你进来,你把这极花吹活么。风果然进来,极花是被吹开了,花瓣在摇曳。我再指挥了花瓣:你能把我的消息传给我娘吗,娘丢失了女儿不知道急死急活了。花瓣突然真的脱落一片,浮在风里飞出了窗格,它忽高忽低地飞,飞过了石磨,又从石磨那儿往白皮松飞去,样子很急,如狗见了骨头跑得那么快,倏乎就出了硷畔沿不见了。
* *
我在想我娘。
营盘村前的山是三个峰头,村里人都说那是笔架山,可营盘村没有出文人,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出过。娘就对我和弟弟说:好好念书,营盘村的风水会不会就显在你们身上呢!但娘的日子过得很苦,爹死后,她得忙了家里活,还得忙地里活,原本就长的脸一瘦了显得更长。每到开学前,她就为筹我们的学费熬煎,已经把一间房卖给了邻居,还卖掉了她的结婚陪妆箱子、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到后来,连家里上几辈人传下来的铜脸盆锡酒壶玻璃插屏也卖了。我见过娘在灶膛烧火时哭,我给她擦眼泪,她说烟把她熏呛的,我说火是明火没有烟呀,她就唠叨我事多。娘是越来越爱唠叨,总是我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我都有些烦她。五月初三是爹的忌日,娘要给爹的遗像前献米饭,在米饭上夹了一筷子豆腐,又夹了一筷子炒鸡蛋,还说:你就爱吃个酸白菜!把酸白菜夹上了,却突然哭起来:你轻省了,你啥都不管了,你把我闪在半路上?!把一碗饭菜和遗像全打翻在地。到了冬季,石头都冻得像糟糕,但手只要一摸上去,又把手能粘住。那天我和弟弟从学校回来,弟弟说:今日娘给咱做啥饭呀?我说:米粥吧。弟弟说:一天三顿老是米粥!我说:你再弹嫌饭碗子,让娘唠叨你!一抬头,却见娘在远处的那棵砍头柳下脱棉袄上套着的碎花衫子。从村子到镇街六里路,要路过那棵砍头柳,砍头柳就是每年都要把树枝砍掉了只剩下树桩,来年春上树桩上再长树枝,这种柳越砍越长得旺,以至于树桩粗得三个人才能搂抱住。娘最好的衣服就是那一件碎花衫子,她是去镇街了才把碎花衫子套在棉袄上,从镇街回来了又把碎花衫子脱下来。娘是去镇街了,提了一个大包,里边装着作业本,圆珠笔,一袋盐,一袋碱面,竟然还有塑料纸包着的一斤羊肉。我说:今日不过节呀。娘说:不过节咱就不能吃肉啦?吃,给你俩吃好的!那个晚上,我们是炖了肉,还烙了个大饼子,吃过饭了,娘才告诉说:这个家再这么下去就完蛋了,即便饿不死,你们的书也念不成了,村里有三个人要去城市打工,我也跟着一块去呀。娘的决定使我高兴,娘不在家了我就不受她的唠叨了,但我立即意识到照顾弟弟要成了我的责任。弟弟还小,在村里初中读一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在他们班是前三名,而我比弟弟大五岁,初中快要毕业,高中则要去十五里外的县城。娘在问:胡蝶,你觉得你能考上高中吗?我说:我数学不好,但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给同学们念过。娘说:你不敢保证是不是?那你就休学来照看弟弟吧,弟弟是咱家的希望,我外出挣钱就是要发狠心供一个能上大学的。我呜呜地哭了,娘就唠叨:女孩子学得再好将来还不是给别人家学的?说完了,又说一句:你学不进去么。我睡下了,娘在屋里翻寻着酒,爹生前爱喝酒,死时还留有半坛子,娘觉得倒了可惜,自己就有时喝那么一口,倒也喝上了瘾。那一夜酒坛子里已没了酒,翻出了上个月给弟弟治咽喉剩下的咳嗽糖浆,她把那些咳嗽糖浆全喝了。
第二天,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