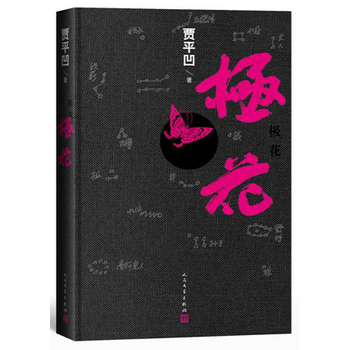极花-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房,同了房孩子就不干净。我躺下没有言语,脸上烧烫了一下。那就是我的孩子吗,我怎么生了个那么难看的孩子?这孩子是罪恶的产物,他是魔鬼,害我难过了那么长日子,又横生着要来索命!好吧,我把你生下来了,你带走了我的屈辱、仇恨、痛苦,从此你就是你了,我就是我,我不会认你是儿子,你也别认我是娘。
但是,就在夜里,窑里黑隆隆的,黑一却哭起来,他哭得响亮,好像是突然点了灯,生出了一团火焰,使整个窑洞里的桌子椅子,瓦罐陶瓮,炕上的被褥枕头,门窗上窑壁上所有的纸花花都醒了灵魂,在黑暗里活着,好过着。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满心身的是一种莫名的愉悦,就对黑亮说:你把他抱过来。黑一睡在了我的怀里,哭声戛然而止,我触摸着亲吻着他的脸蛋,他的屁股,他的小手小脚,是一堆温暖的雪和柔软的玉。我在心里说:这是我儿子,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黑亮也睡过来,我推开了他,让他睡到地铺上去,他的脚太臭,不能熏着我的孩子,他睡觉爱动,不让他在睡梦中胳膊腿压着了我的孩子。我只和我的儿子睡。
这是天意。黑亮睡在地铺上了,仍是激动着,说:第一次就有了孩子,天赐给我了你和儿子。
是天意。我在默默地说,天是让我的儿子来陪我的。
我突然觉得孩子的名字应该叫兔子,嫦娥在月亮里寂寞的时候,陪伴她的就是兔子。我就抱着儿子亲,叫着:兔子,兔子。
黑亮说:你把黑一叫兔子?
我说:他不是黑一,是兔子!
兔子就兔子吧。黑亮妥协了:这名字也好。他又说:兔子几时会叫爹呢?
只会叫娘。我看着窑顶,其实没有窑顶,只是黑暗。我再一次把兔子的脚丫子含在嘴里,那是一块糖,几乎要消融,我又把脚丫子取出来,在心里对兔子说,相信娘,总有一天娘会带着你到城市去,这个荒凉的地方不是咱们待的。
那时候,我觉得满世界都在缩小了,就缩小成我一个人,而在这个村子,在这个土窑里我就是神。
十天里,我一直就坐在炕上,我的身下铺着黄土。这是村里的习惯:从坡梁上挖下纯净的黄土,晒干再炒过,铺在炕上了上边苫一张麻纸,产妇月子里就坐在上边。这黄土还真能吸干身上的脏水,快速地恢复了伤口。十天后,我开始下炕走动。那一个晚上,从吃晚饭起兔子又哭闹了,兔子差不多有五天了,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哭闹,老老爷写了张纸条:天皇皇地娘娘,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老老爷让我们把纸条贴到村子里的树上去,我和黑亮贴了往回走,天上繁星一片,我一眼就看到了先前发现的那两颗星,星星的光一个大一个小,发的不是白光而是红光。我指着说:那是我和兔子的。
但黑亮说看不到呀,那儿哪有星?这让我惊奇,他怎么看不到呢?他说真的没有什么星呀,是你看花了眼吧。我没有再和他说话。
* *
兔子要过满月了,黑家备了酒席要招呼村里人。太阳还在崖头上,硷畔上就来了一批,有给孩子拿衣裳的,有给孩子送鞋的,更多的是抱一颗南瓜,提一筐土豆,端一升苞谷糁或扁豆。半语子也来了,他拿了一个小炕虎。小炕虎几乎家家都有,石刻的,拳头那么大,黑亮就说过,家里有孩子了,孩子在两岁前,这炕虎拴一条绳,绳一头系在孩子身上,孩子在炕上玩耍就不会掉下炕去。孩子两岁后媳妇抱着出门或回娘家,也同时抱着炕虎,就能辟邪。黑亮在小时候就系过炕虎,但他长大了却不知道把炕虎丢在了哪里没有寻到。而半语子带来了小炕虎,小炕虎被汗手抚摸得油光起亮,他说他小时候用过。我很喜欢这个小炕虎,高高兴兴接受了,就放在兔子身边。黑亮却进窑拿走了小炕虎,给我说:不能用他家的。原因是麻子婶现在还昏迷不醒,她是生过孩子,但没活成,用他家的不吉祥。他说:我给黑一做个新的。我说:叫兔子。他说:噢兔子,兔子要用新的小炕虎!
太阳正端的时候,訾米来了,她又是穿得花枝招展,人还在硷畔入口处,声就传过来:这是给咱村过事哩么!她拧着腰身往我窑里来,有人就问:你给孩子带了啥礼?訾米说:我给我干儿子带了一棵极花!她拿的一个纸卷儿,打开了真的是一棵极花。但她却说兔子是她的干儿子,这就胡说了。问话的人说:干儿子?你和黑亮认了亲家?!亲家母的沟蛋子,孩他爹的一半子!她却嗬嗬地笑着进窑了。
訾米把极花放在兔子的旁边,趴过去在兔子脸上亲了一下,留下一个红印,她说为什么她没早来,她有重孝在身,来了对孩子不好,昨日去东沟岔给立春腊八烧了纸,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来烧纸了,她再也不会去了,她要重新活人呀,回来就把孝衫脱了,门上的白对联也撕了。你瞧,我这红上衣怎么样,好看吧?她展示着给我看,还悄声说:胸罩内裤都是红的。我说:你去挖极花了?她说:这极花不是我挖的,昨日从东沟岔回来,东沟口遇上有人挖了极花,我看是有虫子有花的完整就买了。你家里有了一个极花才有了你,你让黑亮把它晾干了也装到镜框去,有了孩子就又有极花,这多好的!她又去抱兔子,亲兔子的屁股,兔子就被弄醒了,哇哇地哭。她说:胡蝶,你是扎下根了,我还是浮萍哩,让孩子认我个干娘吧。我说:你不是已经给人说是干娘吗?她说:我怕你不肯么,先下手为强呀!兔子却在她怀里尿了。
开始喝酒吃饭啦,黑亮爹做了三桌菜,当然是凉调土豆丝,热炒土豆片,豆腐炖土豆块,土豆糍粑,土豆粉条,虽然也有红条子肉呀焖鸡汤呀,烧肠子呀,里边也还是有土豆。但大家都喜欢地说:行,行,有三个柱子菜!如果再舍得,有四个柱子菜就好了!黑亮爹说:原来有羊肉的,黑亮去了王村张屠户那儿,不巧屠户老张在镇上住院,人家关了门了么。今儿酒好,二十元钱一瓶的,黑亮,上酒上酒!
这一顿饭风扫残云般地吃过了,而酒还是继续喝。凡是喝完一瓶,瞎子就在旁边捡空瓶子,先对着空瓶子咂一下里边的剩酒,然后放在硷畔沿边,那里已经垒上了十几个空瓶子。半语子首先醉了,须要黑亮爹也来喝,黑亮爹过来连喝了三盅,半语子还要和他划拳,黑亮爹六拳都赢了,半语子说:你们打个通,通关,吧!黑亮爹说:你们喝,我得招呼大家呀。半语子不行,胳膊扳着黑亮爹的脖子。老老爷是坐在上席,他不喝酒,只喝水,就给黑亮说:你去挡挡酒,别让你爹喝醉了,他有高血压哩。黑亮也不好去阻拦,就进窑抱了兔子出去,说:你们还没看我儿子吧,让孩子认认爷爷奶奶伯伯娘娘的。喝酒的人就停下来。兔子是用小被子包裹着,人们都在说孩子长得胖长得好看。半语子上半身趴在桌子上,说:我看看,像他,他爹,爹还是像,像,他爷?!忽然有个妇女在硷畔入口上来,她的公公瘫痪几年了,黑亮爹盛了一碗饭还夹了一块肉让她送回家去,那妇女把空碗放回桌上,却对半语子说:麻子婶醒过来了?半语子说:她要是醒,醒过来,来了,还能,能不来?那妇女说:我咋看麻子婶在你家门外摘南瓜花哩?半语子说:大白,白天,的,你见鬼,鬼了?!那妇女说:明明是麻子婶,穿了一身长袍子么。半语子说:啊,啊!起身就跑回去了,他脚下拌蒜,后边就有人跟着,怕他栽了跤。
后来,厮跟他的人返回来,说真的是麻子婶,麻子婶又活过来了。
人们都骂这是撂天话,那人说他跟着半语子回去,老远看见半语子家的烟囱里冒烟,进屋一看,麻子婶在厨房里烧火做饭哩,她穿着绣花鞋长袍子,半语子一下子扑过去抱住,说:你咋,咋活活,活了?麻子婶说:饿死我了。
麻子婶在炕上昏迷不醒,半语子觉得她是不得活了,就找了木匠做了棺材,棺材做好就放在窑里,又给麻子婶洗了身子,穿上了寿衣,放在棺材里,也不盖盖,说:你睡吧,几时不出气了,我就埋了你。麻子婶在棺材里躺着躺着,突然睁开了眼,一翻身,棺材里翻不过身,就说:人呢,我咋睡在这里,你不来拉我?窑里没有声音,她艰难地爬出来,见窑门掩着也没有锁,说:死家伙你出门了不锁呀,让贼偷呀?!却觉得肚子饥,饥得特别难受,就到锅里案上寻吃食,锅是做过了饭没有洗,案上乱七八糟一堆,也没个能吃的,揭了瓦罐发现还有些苞谷面,用水和了,要在锅里做面糊糊,还觉得面糊糊里应该煮些菜,但窑里什么菜都没有,便摇摇晃晃到门外地塄上看到种的南瓜蔓上叶子肥绿绿的,摘了几片,又觉得南瓜叶煮锅太苦太涩,就扔了南瓜叶,把那三朵南瓜花摘了。
厮跟着的人跑回来说了麻子婶的情况,黑亮爹让那人赶紧再去半语子家,叮咛着不要给麻子婶做饭了,她这么久汤水未进,突然吃了别的饭胃会出事的:把她背来,我给她熬些稀面汤。
麻子婶是被背了来,吃了一碗稀面汤,她说:人这多的干啥哩?我抱了兔子给她看,她说:生下来了?这么大的事都不给我说!就动手掰开兔子的腿,叫道:长个牛牛!将来又祸害谁家的女子啊!大家就哄哄地笑。她却急火火地说:剪子呢,剪子呢?半语子说:你又寻,寻,剪子呀?!她说:我给孩子剪个钟馗,小鬼就不近身了。
那天,半语子回去了三次,取了剪子,又去取了红纸和绿纸,麻子婶偏要黄纸,再去取了黄纸。众人取笑半语子:咋这积极的?半语子说:我这也,也,娶了个新,新媳妇么。
* *
麻子婶以后来我这里成了常客,黑家再没嫌弃过她。她一来就在我的炕上剪纸花花,到了吃饭时,也就在这里吃。半语子有些过意不去,掮了一袋苞谷和一背篓土豆。有时晚上了麻子婶也不回去,就和我睡在炕上,黑亮当然搭地铺,四个人在一个窑里,黑亮觉得怪,要睡到杂货店去,麻子婶说:你睡你的,我是你婶哩!她比先前更爱说爱笑,甚至有些诡异,经常是三更半夜就醒了,说神教她一种花花了,点了灯就剪起来。她能把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和人混在一起重新组合成一个形象,人身子或者是树,狗或者有着人脸,又把毛驴叫人毛驴,把老鼠叫人老鼠。甚至常指着窑壁说:你看见那里有个啥?我看着窑壁,上边什么都没有。她说:爬着一只青蛙。便一口气剪出十几个青蛙来。
有一天下午,天上的云全变红了,像燃了火,麻子婶就剪出了一棵树。整个画面是一棵枯树,以树干为中轴线,两边枝干对称伸开,而根部又如人的头部或鼻头,显得朴拙又怪诞。树枝间有产生旋转感的菊花纹,也有飞翔跳跃的小鸟。更奇异的是无数的小黄蜂布满于枝枝干干,并随着树的枯洞如血流一样飞舞,我看着都能听到一种嗡嗡的蜂鸣声。
麻子婶,我说,这是啥树呀?
空空树。她说,眼睛盯着我,那眼光我有些害怕。
空空树?
她竟然唱起来:正月里二月中,我到地里壅血葱,地里有个空空树,空空树,树空空,空空树里一窝蜂,蜂蜇我,我蜇蜂,我和蜂被蜇得虚腾腾。
以前的麻子婶从没在剪纸花花时唱歌的,几乎从那以后,她每次剪出什么就顺嘴唱一段歌子。比如她剪了个男人用毛驴驮着媳妇,唱的是鸨鸨,树皮,金锁拉驴梅香骑,金锁拿着花鞭子,打了梅香脚尖子,哎呀哎呀我疼哩,看把我梅香矫情哩。我说:你剪的金锁?她说:是金锁。我说:金锁以前对他媳妇好?她说:好。比如她剪了棵极花,唱的是:挖药的人巾巾串串,吃药的人呻呻唤唤,贩药的人绸绸缎缎,卖药的人盘盘算算。我说:啥是巾巾串串?她说:你见过谁挖极花回来衣衫回全过?比如她剪了吃搅团的,唱的是:天黑地黑雾朵儿黑,吆上毛驴种荞麦,揭一回地拐三弯,揭了三回拐九弯,按住犁头稳住鞭,还不见媳妇来送饭?左手提着竹笼笼,右手提的双耳罐,站在地头望老汉。吃的啥饭,吃的搅团。怎么又是搅团?柴又湿来烟又大,锅板两片锅四拃,笊篱没头勺没把,怀里揣的是你娃,不吃搅团再吃啥?我就笑起来,她说:我再剪一个你看是啥?她一边剪一边唱:能把鸡毛撂远,能把犁辕拉展,能把牛皮吹圆,能把驴笼嘴尿满。她剪出了一个人,我说:是村长。她说:这是你说的,我没说。比如她剪了一个窑洞,窑门口坐了个妇女,旁边有树,树上有鸟,面前是狗,狗在撵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