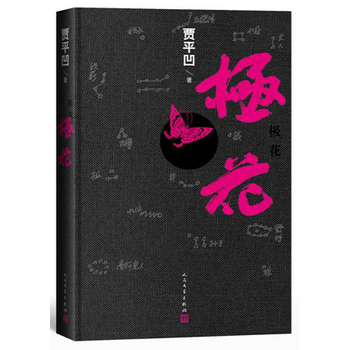极花-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楞想害我,我就要骂他!老老爷说:三楞又咋啦?那人说:三楞给他爹的坟上放了块大石头,石头正对着我爹的坟,这是不是压住了我家的风水,我该不该也在我爹的坟上放块石头?老老爷说:你觉得他家压你家的风水,这就真的是压了,那你也放块石头吧。那人骂了句:三楞我你娘!却又说:你知道立春家的事吗?老老爷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还理会人家的事?那人说:村里的人都说哩,外地那个石老板为啥买了立春家那么多血葱,还要定期来进货,是前些日子立春把石老板领去他家,石老板一见訾米,竟然认识訾米,立春的媳妇原来在城市里做妓女,有意思吧?老老爷就一阵咳嗽。我见不得那人的样子,多高的身子一个碗口大的脑袋,眼睛一眨一眨的像鸡屁眼,更听不得那人说话,凭啥就说立春的媳妇是妓女,老板认识就是妓女啦?!我本来懒得动,偏用扫帚打鸡,鸡往左跑,我要让它右跑,嘎嘎嘎地就撵到了葫芦架前。老老爷还在咳嗽,那人说:你撵的啥鸡呀,鸡毛卡到老老爷喉咙啦!我说:我撵你哩!就推那人走。那人还不想走,老老爷摆了摆手,那人才走了,嘴里嘟嘟囔囔地骂我。
老老爷吐了一口痰,不咳嗽了,说:胡蝶你泼辣。
我说:他是笑话立春哩还是眼红立春呢?!你说他有毒,真是有毒哩!老老爷说:小动物身上都有毒哩,没毒它也难存活么。胡蝶,你是第一回到老老爷这边来的呀,你公公不在?我说:我又没出硷畔,你又不会带我逃跑的。他笑了一下,只发了个声,脸上并没有表情。
你还没看到你的星吗?
老老爷骗我,没星的地方咋能看出星呢?
你继续看吧,你总会有星的。
那要看到啥年啥月?!
老老爷立起了身,却说:胡蝶,老老爷得去西沟抓蝎子呀,太阳要落山了,蝎子该出来了。泡了酒你也来喝。我说:老老爷,你别怕,我不会连累你。心里又一阵犯潮,我的眉眼就皱起来。老老爷说:我怕谁呀,而谁都怕我哩。我说:村里人好像都敬着你。老老爷说:是敬哩,敬神也敬鬼么。我不明白他话的意思,他却说:你有病了?我说:是有病了,这里没卫生站,也没个药。老老爷说:你才是药哩,你是黑亮家的药。他的话我又听不懂了。他说:你不思茶饭?我说:口里没味。他说:觉得恶心想吐?我说:又吐不出来。他说:你把手捂在嘴上哈一下,再闻闻是啥气味?我哈了一下闻手,我说:怎么有些酸味?他说:你怀孕了?!我一下子脸红起来,嘴里不知说些什么,而同时眼睛就模糊,葫芦架在动,硷畔在动,老老爷也成了两个老老爷:这不可能吧,我怎么就怀孕了?!一股子凉气从脚心就往上蹿,汗却从额上流出来。
我急了,说:老老爷老老爷,这你得救我!我不能怀孕,我怎么都不能怀孕,老老爷!
老老爷说:这孩子或许也是你的药。
老老爷,老老爷!
你走吧。
我走了,走得像一根木头,走回我的窑里就倒在了炕上。
* *
怀孕的事我不敢说给黑亮,但我越发恐惧,焦躁不安,额头上起了痘,又严重地便秘,只要黑亮不在窑里,就使劲挤压肚子,蹬腿,甚至从炕上、方桌上往下跳,企图它能坠下来,像大小便一样拉掉。我是多纯净的一块土地呀,已经被藏污纳垢了,还能再要生长罪恶和仇恨的草木吗?但我没办法解决肚子里的孽种啊,只能少到硷畔去,像以前被关闭在窑里一样,又终日无声无息地趴在窗口。瞎子在上个月要盘新炕而拆掉了他的炕,说旧炕土是最好的肥料,就堆在白皮松下。这一日,他问黑亮爹给毛驴磨些黑豆呀还是豌豆,黑亮爹说黑豆还要涨些豆芽的,磨豌豆吧,少磨些。瞎子说:把这些炕土要送到地里,给它吃好些。就套了毛驴推石磨。毛驴不好好推,推着推着就把套绳弄掉了,瞎子在呵斥:转磨道你都寻不见方向呀,是嫌给你磨的豌豆少啦还是嫌那炕土堆大啦?我看着那堆旧炕土,心突然地一阵疼,像针扎一样:经过了前几日的一场小雨淋过,旧炕土堆上长出了三棵芽来,是草芽子还是菜芽子,或许还是树芽子,很小很嫩很绿。这些芽子怎么就长在旧炕土堆上呢,它们只知道种子在适当的土壤和水分里就发芽,一发芽就梦想着长成蔬菜长成花草长成树木,可这是一堆旧炕土呀,堆在白皮松下并不是长久的,很快就要铲了运走啊。我可怜着这些芽子,别的生命或许多么伟大,它们却是如此卑微下贱!
我开始不吃不喝,不和人说话,真的病倒了。
我一病倒,这吓坏了黑家人,黑亮已不到杂货店去了,问我哪儿不舒服,要不要背了我去王村的卫生站看看。我不能让医生看,说我感冒了,睡一睡就好了。黑亮爹改善了伙食,或是小米干饭,熬土豆、粉条和酸白菜的杂烩,或把荞面压成饸饹,搓成麻食,又把土豆丝拌面上笼做成麦饭,把南瓜绿豆焖锅做成揽饭。还买了二斤羊肉和红白萝卜一块清炖。给我一天吃五顿,顿顿都让多吃。正吃着,麻子婶又来了,人还在硷畔入口,就说:咋这香的!黑亮爹除了剪小红人时热情过,上次冷淡了这次仍冷淡,说:你还是不喝茶?麻子婶说:你那茶浓得我喝不了。黑亮爹又说:还是吃过饭来的?麻子婶说:我吃的是汤饸饹。黑亮爹说:噢,那就不坐了?麻子婶说:赶我走呀?!我剪了新花花给胡蝶呀!她就进了窑,把一个包袱解开,纸花花就摆了一炕,说:你这啬皮公公,锅里炖着羊肉也不把我让一让。你帮我选选哪个好看!我无心帮她选,窑门一关,扑通跪下,说:婶你救我!麻子婶说:你公公是啥人么,过河就拆桥!黑亮打你啦?我说:我怀孕了,你有啥办法能把胎打下来。麻子婶却没惊讶,也没慌张,让我站起来扭扭身子给她看,又翻我的眼皮子,撩了衣服看奶头子,她说:你咋和你婶当初一样呀?!
麻子婶告诉我,她当初怀上了也并不知道,恶心呕吐,被盐商的大老婆看出来,假装给她治病,让她喝苦楝子籽水,胎就打掉了,胎一落,她才知道那大老婆怕她有了孩子争家产,她偏又给盐商怀上了,盐商就娶了她做小的。
我说我和她的情况不一样,我不能要孩子,求她给我弄些苦楝子籽吧。麻子婶说:这你让我作孽呀,孩子毕竟是条命啊!我说:那你就不管我的命啦?你要不弄苦楝子籽,那我就得死,我死了孩子还不是死?!麻子婶想了想,答应了,说:你喝苦楝子籽水的时候,不能让人看见,鸡呀狗呀也不能让看见!
麻子婶真的在再来时口兜里装了些苦楝子籽,说村口有棵苦楝树,她就在那儿摘的。我偷偷地用水泡了这些苦楝子籽喝,喝过一杯了,把苦楝子籽塞进炕洞去,再泡新的,为了药效更大,我在第三次泡时还砸碎了苦楝子籽,泡出的水苦得难咽,喝下去肚子就疼。我以为这下就可以落胎了,却在厕所里泻肚子,一晌午泻五次,泻得虚脱了。
黑亮爹见我感冒了,又泻肚子,病越来越重,就当老老爷在葫芦架下泡蝎子酒时,把我的病情说给了老老爷,老老爷这才告诉了我是怀了孕,叮咛泻肚子也不能随便吃药。我在窗口里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吓得我差点昏过去,偏这时麻子婶又拿了苦楝子籽来了,刚到硷畔,黑亮爹就跑近去高兴地说儿媳妇怀孕了,我心提到嗓子眼上,担心麻子婶一时说漏了嘴,但麻子婶嘿嘿地笑,黑亮爹也嘿嘿地笑,麻子婶笑过了,她说:这是胡蝶说的?黑亮爹说:她没说。麻子婶说:那是黑亮说的?黑亮爹说:黑亮还不知道哩,是老老爷以儿媳妇的神色说的。麻子婶就拍着手,说:我只知道是干柴遇烈火的,可没想到这么快的!该谢我吧,是我的小红人招了魂呀!黑亮爹就给了麻子婶十元钱。麻子婶说:这你咋舍得呀?!黑亮爹说:你是村里第一个知道这事的,图个吉祥!麻子婶说:哦,要我在村里声张啊,那就像打发要饭的?黑亮爹又拿了十元钱给麻子婶的口兜里装,却发现了口兜里装着苦楝子籽,说句你咋还装这个,并没在意,麻子婶笑嘻嘻进了我的窑。
怀孕的事已经暴露了,那个下午,我把所有的苦楝子籽全砸碎泡了,我想尽快地把胎打下来。
晚上黑亮回来,一进窑把我抱住了就亲,我不让他亲,他说嘴不臭的,这么大的喜事你不告诉我!我明白他也是刚知道怀孕的事,没再说话,黑亮爹在门外喊着快来端饭,两人在门外说话:啥饭?我炖了鸡。咱就那一只公鸡要打鸣的你炖了?我炖的是那个黑鸡。那黑鸡还下蛋的呀!黑鸡炖出的汤有营养。
吃毕了饭,黑亮坐在炕上,说:说造人我真还把人造下了!兴奋地双手在炕沿上拍节奏,问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最好是起两个名字,是男孩了叫刚强,是女孩了叫极花。我突然就说:不能叫极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叫极花,是因为极花是草是虫还是因为极花是我特殊的通讯物,但我就那么说了一句,声音尖锐得像刀子。黑亮说:不叫极花了,叫如意。他从箱子里便取出一个褥子往炕上铺,念叨着你现在地位提高了,就得睡得舒舒服服,一个黄豆都不能垫着你。在铺褥子时,就发现了我藏在炕头席下的苦楝子籽,他并不知道苦楝子籽能做什么,顺手抓起来从窗子扔了出去。事情坏也就坏在这里,黑亮把苦楝子籽从窗子扔出去,刚好老老爷从窗外经过,看了看,把地上的苦楝子籽捡起来。黑亮爹出来倒涮锅水,说:黑啦你还出去呀?让黑亮陪着你。老老爷说:家里咋有这东西?黑亮爹说:苦楝子籽,这咋啦?
老老爷叽叽咕咕给黑亮爹说着什么,黑亮爹就叫黑亮,黑亮出去,一会儿返回窑,脸全部变形了。他说:你喝了苦楝子籽水?是不是喝了苦楝子籽水?!我知道一切都失败了,仰头对着他,我觉得我的鼻翼鼓得圆圆的,出着粗气。黑亮又说:你要害我的孩子?咹?!我呼啦把被子一裹,脸朝炕里睡下了。黑亮嗷嗷地叫,举了拳头来打,拳头快要打到我身上了,拳头却停住,转身踢麻袋,踢凳子,凳子在地上发出呻吟声,他抓起凳子就摔向窑门,窑门被撞开了,一条凳子腿飞了出去。
黑亮爹在外边喊:你疯啦,黑亮?!要打就打那死麻子,十个麻子九个怪,是她拿来的,麻子拿来的!
黑亮就从窑里跑出去,他好像是在他爹的窑里拿菜刀,他爹在喊:刀放下!你要去就去质问她,别再惹乱子!硷畔上一价声的狗叫,瞎子也起来了,在拉黑亮,拉不住,黑亮爹在叮咛着瞎子:你去,你也去,防着他出事!一阵脚步声,瞎子白天里老趿着一双没后跟的鞋,走路吧啦吧啦响,他跑去的脚步没有那声了,可能是光着脚。
黑亮和瞎子是去了麻子婶家,黑亮到底打没打麻子婶,我不知道。第二天晌午,半语子来给黑亮爹赔情道歉,说他把他那妖精打了一顿,骨头打断了,在炕上躺着,不信了你去看。黑亮爹没有说话,也没有去,我却在窑里哭了。我不再和黑亮冷战,给他说这事不能怨恨麻子婶,是我让麻子婶给我的苦楝子籽,现在倒害得人家断了骨头,那不残废啦,央求他去看看麻子婶。黑亮这才说半语子打断的是麻子婶的两颗门牙。但麻子婶从此再没到黑家来过。
* *
已经是秋末了,硷畔上开始堆放起苞谷和豆秆,黑家人在地里就扳了棒子,而豆秆是连豆荚一块背回来的,隆起了一个垛子,等晒干了用连枷打豆子。黑亮很少去镇上、县上进货了,和瞎子叔又每天去地里挖土豆,摘南瓜。这些活他们不让我干,我也懒得去干,就坐在那豆秆垛子前,看豆秆垛子里爬出来的瓢虫。这里的瓢虫很多,都是铁红的,就像我那件衬衣的颜色。但瓢虫身上有着白色的圆点,如同是星,我用草棍儿一戳,它就飞起来,我感觉我不如它。豆秆垛子里竟然还爬出了一只蚂蚱,我的草棍儿没有戳上它,它往硷畔沿上蹦跶,蹦跶了三下,又蹦跶了四下,竟然翻过身,四条腿那么动了动,就死了。
三朵那天是来了,老老爷嘀嘀咕咕给他说什么,三朵就又去了黑亮爹的窑里,黑亮爹在窑里正烟熏雾罩地做饭,也是嘀嘀咕咕了一阵,两人出了窑,黑亮爹说:三朵,叔过后要谢你哩。三朵说:你抱上孙子了再说谢。三朵急急忙忙离开硷畔,回头还朝我笑了一下。他们鬼鬼祟祟的行为使我惊觉起来,但三朵给我的笑是柔和而善意的,我就又弄不明白他们是要干什么。
我在无聊地盯着一只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