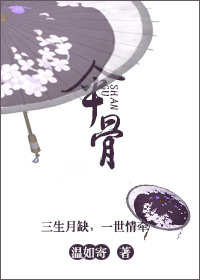伞骨-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申屠衍将食盒放在窗边的案几上,将一叠油豆腐,一叠小白菜,还有一盅冬瓜羹摆出来,早已经过了用饭的时辰,饭菜虽然精致,却都已经失了温度。
钟檐这一日被父亲罚着背书,抄写,后来又关了禁闭,早就腹里空空,看见饭菜,便像一头饿疯了的小猫一般扑了过来,也顾不上用筷子,伸了爪子抓了白花花的米饭,就往嘴里塞。
他这样狼吞虎咽,恨不得一口就把整碗米饭都塞进去,钟檐觉得照着他这样的吃法,太容易被噎住,便递了一碗冬瓜汤过去。
钟檐却瞬间停住了扒饭的动作,慢慢抬起头来,黑漆漆的眼仁周围已经微微发红,肿得跟红眼兔子一样,他这样看着似乎要比他大许多的少年,许久才忽然开口,没来由来了一句。
“喂,大块头,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也是他们口中的纨绔子?”
不分五谷,四肢不勤,甚至连书也念不好,只会斗鸡走狗的纨绔子?
申屠衍怔住了,舔了舔干涩的唇。
“其实不是的。”
他的声音几不可闻,却忽然生出了伤心,这份不被人知的伤心,今天非要找一个人说一说不可。
“其实我只是不爱念他们口中的那些大道理的书罢了……什么孔孟之道,礼义春秋,我统统不爱听……有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每一个人都想要当官,那么,渔樵耕商,这些行当又有谁来做呢,那么,我们的国家岂不是乱套了……人又不是只有出仕的一条路。”
小孩儿望着天际,绯色的桃花簌簌从枝头划落,又在眼界里消失不见。他这样自说自话,却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申屠衍神色一暗,木然问道,“那你……少爷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他问出口,马上觉得太过唐突,况且,这样的问题,连自己也没有想过,他以前一直想,只要活下来就好,哪里还有多余的心思。现在,这个问题,却这样摆在了他的面前。
钟檐咬着筷子,很努力的想了一会儿,最终却摇摇头,“我还不确定。不过我总会找到那样一条路的……哎,像你这样的冰山大块头,只吃饭不长脑的是不会懂的。”
申屠衍站在一旁,看着小孩儿眼睛亮汪汪的,索性放了筷子,用爪子抓着鸡腿儿啃着欢畅,仿佛刚才那个小孩儿是幻觉,他还是那个张牙舞爪,肆意横行的钟檐。
五陵年少不言志,一朝云开关山去。
后来他们分别,各自经历人生中的坎坷和际遇,申屠衍才想起那个夜晚,他的心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塞满了一种的莫名的情绪。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陪你一起找,好不好?
但是那个晚上,他是没有说出口的。他只是静静看着那个小孩儿,在岁月催促下,长成了京城中的翩翩佳公子。
而他却,始终沉默。
京都的春季都是在绿荫黄花中溜过的,它就像只雀儿,蓬门窄巷,勾栏红楼,驻足了又飞走了,徒留下一声光阴的欸乃。
寅时二刻,穿着绯色罗袍的官员从石阶上鱼贯而入,高呼一声万岁。
新的一日开始。
下朝的时候,钟尚书忽然喊住了杜荀正,“杜太傅,留步。”
杜荀正回过神,滞了步,看出他是有话要说,便耐心听他的下文,钟尚书走近了一些,“听说妹夫昨日将一位上门请教的贡生给轰出门了?”
钟尚书还没有开口,还没有开口,他心中已经多少猜中他说的必是这样一件事,倒不如坦荡承认是有这么回事啊,“那书生妄谈朝政,窥探圣意,竟然说太子不出三年必废……包藏祸心,空有其表,不是治世之才。”
“糊涂啊!妹夫呀,你好生糊涂。那萧无庸已经连中两元,这殿试魁首非他莫属,你这么做,不是又给自己树敌吗!”钟尚书知道自己这个妹夫天生一副读书人的清高迂腐之气,颇有些恨铁不成钢之意。
“高中哪有那么容易,刘夔,唐思齐的学识便比他好得多,秉性也比他沉稳可靠得多。”
钟尚书叹了一口气,“杜荀正呐杜荀正,为官之道比的并不是学识,做了这么年臣子,你还不懂吗?当今陛下圣明,看得自然也通彻,你且看看,满朝中又有哪一个同僚不赞一声的,圆滑如此,陛下又怎么会去点两个空掉书袋的迂腐木头呢,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过了几日,皇榜便公布了,高祖御笔一挥,那个名唤作萧无庸的举子果然高中一甲。
放榜那天,钟尚书被宣进了宫,钟檐便趁着这个空当偷偷溜出来玩。
那时,申屠衍已经被他调到了身边当伴读,说是伴读,实际上他却比钟檐还要不济,闲来无事时,他便问站在一旁杵着的大块头,“你认得字吗?”。
“不认得。”申屠衍很有些不好意思。
“这样才好。”钟小少爷答应了一声,眼儿弯了弯,心里却显得很欢喜,心里却想着要的就是不识字。
“……”申屠衍无语。
于是申屠衍便陪着钟檐念书,整整七个年头。起初钟檐觉得申屠衍实在太呆了,问他一个问题,能用三个字回答绝对不用第四个字,比起他的那群酒肉朋友,实在无趣得要死。后来,他却渐渐习惯这样一个沉默的存在,以至于后来少了申屠衍,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不能够习惯。
这七年里,申屠衍一直看着他写字,却从来不认得一个字,只因为他不想他认得。
所以,像偷偷出去玩这样的坏事,钟檐当然也要拉上垫背,更何况是申屠衍这样又大个又耐摔垫起来顺手又舒服的垫背。
那一日,他的身后还挂了一条粉裙垂髫的小尾巴。
于是风格迥异的三个小孩儿就在京都的街上招摇过市了。
放榜的日子,东阙的街上是万人空巷的热闹,年近花甲才高中的耄耋老贡生,名落孙山蹲在榜前面痛哭流涕的青年贡生,街上前来迎接三鼎甲的仪仗队伍,锣鼓喧嚣。
正是金榜高高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街上实在太挤,三个小孩儿怕被挤到,索性蹲在街道一旁,托着下巴看热闹,小姑娘的手紧紧拽着哥哥,深怕被人挤没了,指着远处的喧嚣,声音软糯,“表哥,你看那声音是要迎接状元吗?”
钟檐原本也不喜欢带着小姑娘,觉得她太碍事,可是看着小妍,心底却柔软了下来,生了调笑的心,“你们小姑娘不是都说嫁人当嫁状元郎吗?快仔细瞅着,状元的模样。”
小妍脸臊得通红,越是想要辩解,越是结巴,“表哥……你……胡说……”
钟檐看着炸毛的小姑娘,决定不逗她了,语气温和,抚着她柔软的发,认真说,“什么状元郎,我们小妍长大要嫁给世界上最好的男子。”
小妍不明白她的表哥怎么会忽然说这样一句,只是觉得这一刻表哥的神情实在是认真,也不言语,忽然,耳边喧闹而来的是一阵锣鼓声,越来越接近。
钟檐转头过去,看见看锣鼓喧嚣之中,笔挺坐在青骢马上的紫衣男人,跟发现了什么似的,兴奋大喊,“呀,这个状元,我认得的!”
不仅认得,还请他喝过酒呢。
一直沉默着的申屠衍也看到了那个男人,脸色却越发凝重了起来。
是的,他也认得。
☆、第二支伞骨·转(下)
“喂,大块头,我认识状元,你信不信?”钟檐扭过脸去,对着申屠衍说。
“粉面桃腮,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沉默的少年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钟檐有些不高兴,横眉,“你知道?你认识字么?你知道一年有多少秀才吗,多少秀才中又有多少举子,多少举子中才能产生一位贡生,而状元,是他们之中最有学问的人……”
申屠衍望着那经过的仪仗队伍,心里也在琢磨着其他的事,听得他这么也一说,拧着眉,也很认真的思考,半响,得出结论,点头,“嗯,他是个变态。”
变态?钟檐为这样一个结论苦笑不得,“那你觉得,大晁朝选才,选得都是变态了,比的不是文采还是谁……更变态?”
旁边的小姑娘见哥哥争起来了,也上来添乱,“表哥,表哥,什么是变态……”钟檐觉得头痛得越发厉害了。
申屠衍木头脸却纹丝不动,很严肃的样子,“嗯,大概是的吧。”
钟檐无语,嘴角几番细微抽动,他觉得他不经侮辱了状元,也侮辱被状元请喝酒的他,许久,才从牙关中挤出几个字,“你、才、变、态。”说着,拽着小妍,气鼓鼓的往前去了。
钟檐觉得这几个字,实在没有冤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申屠衍一样怪异的存在么……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用这个两个字给他定义的。
现在也是么?
钟檐不禁想着,他把他当什么都好,总算是他的什么,而不是陌路。
醉了酒的人很快就睡熟,申屠衍轻轻掩了门,关上一夜萧瑟。
渐渐入了冬,雨水不像前一段日子那样丰沛,伞铺的生意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紧俏,闲暇时候,钟檐便坐在自家伞铺的门槛前发呆,什么也不做。他看似在想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什么也不想的。
很多年前,他也试图去想一些问题,社稷,民生,还有理想……可是真正经历人生以后,他才了解所有的铺垫和为前路所做的准备都是无济于事,在命运突来之时,它们都是徒劳无功,比如年少时的轨迹失衡,比如永熙十三年的那场政局交替,又比如申屠衍……会在这个时候找到他。
既然想什么通通没有用,小钟师父便翘起二郎腿数落东门市的猪肉掺了水,王赖子家的烧刀子缺斤少两,借此来打发闲碎的时光。那时候,申屠衍已经学会了糊伞面儿,他糊的第一支伞骨就是之前掛在梁上的十一支伞骨中的一支。
等他糊完了,钟师傅便皱起眉头看了好大一会儿,那糊完的两支歪七斜八,总算没有破洞,钟檐举起其中的一支,实在只能算是丑疙瘩了,但是……那伞面是黑压压的两团墨是什么,难不成他还在上面画了画,可是实在看不出是什么,“迎面相对的……两头狗熊?”
“……”申屠衍憋了好久,猛咳,摇头,试图引导他,“不是。你不觉得这画面很熟悉?……我想要记住它。”
“你想要记住狗熊?做甚?”
“……”
钟檐又去翻了另外一支伞,他翻开那一直朝下的伞面,却有些痴楞了。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虽然那画师的画功实在是拙劣,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临风提灯的少年。钟檐低垂着头,拿着枯枝有一下没一下的拨动着地上的小石子,看不出在想什么。
许久申屠衍忽然开了口,嗓音低哑,他说,“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你第一次杀人……为了我。”
那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看着新科状元游街回来的几天后。
那时候,钟檐受了状元郎的刺激,第一次生出好好学习课业的心,倒是规规矩矩的坐在课堂上,连整日被他耍着玩的老夫子,也吓了不轻。
没有人知道钟檐是为什么而改变,只有申屠衍知道,可是他知道也不准确。其实钟檐那时并没有什么想法,他只是想要在找到自己要走的那条路之前,试试父亲所说的那条仕途。
那是北靖拓跋三皇子悔诺的第二年,雪满祁镧,风贯京都。战事进入僵持阶段。还只盼着战事快些结束的老百姓,边塞的,京都的,江南的,都热切的对着凯旋之音,翘首以盼。
可是盼来的不过是永不休止的征兵和征粮,国家再丰腴,也抵不过这样日月侵蚀的掏空汲干,有人可是睁眼,他们认识道,战事永不会停止,*才是君主们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而其他的一切,不过都是遮羞布。
人无尽,欲不止。
可是寻常老百姓只是越发憎恨起胡狄人,他们拒绝贩卖漠北而来的货物,拒绝食用北靖人的食物,每一日他们都会在街头发现被蹂躏致死的胡狄的奴隶……
另一方面,朝堂上的老臣们开始用昏聩而老花的老眼重新审视这个天下……一时间,主战派与求和派泾渭分明,纷争不断。
杜太傅便是站在那主战派的。
而钟尚书却主和。他认为国力消耗殆尽,是时间休养生息,勾践卧薪,犹为晚矣,霸王过江,尚待归时。为此,他们已经不知道争吵过多少次了,甚至发展到不许自家的儿女吃另一家的吃食。杜夫人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哥哥赌起气来,竟然跟稚童没有什么两样,不觉好笑。
主和的还有当年的新科状元,翰林萧无庸,为此,钟尚书与他走得也近了许多,萧无庸甚至还好几次登门拜访。
那时钟檐和他的大木头正在暗中较劲,这也是钟檐转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赌气归赌气,但是他也不敢把申屠衍往街上领,他平日里只叫他大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