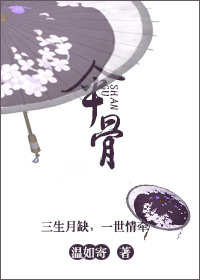伞骨-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到别人嫌弃了?抬眸,蹦出三个字,“我、乐、意。”
朱寡妇自觉没趣,看着钟檐手里的白菜,“要不钟师傅,送我几棵菜吧,真好晚上包饺子。”
钟檐望着手上的菜,迟疑了一阵,终于伸出手去,把菜递给了她。
朱寡妇得了便宜,又磨了一会儿嘴皮子,兴高采烈的走了。
钟檐低着头,又除了一阵子草,忽然把工具,赌气的扔到了土里,再过几天,菜老得都上了芯,他那么用心的除草做什么呢?
他望着满地绿油油的菜叶,忽然发了狠。他对自己说,申屠衍呀申屠衍,大木头呀大木头,你再不回来,我就把你种的菜统统都吃完,不吃完也统统送掉,送不掉就扔掉,一点都不留给你。
那时大军被困北地,云宣已经五天没有关于大军的最新消息了。
就在大军被困第三天,这股子寒流渐渐退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好过些,朝廷拨不下来款来,即使拨下款来,也到不了将士们的手里,饿得狠了,就开始掘树根扒树皮。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无论在哪里同样适用。
申屠衍看着眼前的场景,忽然想起金渡川一战,仿佛所有的历史都要重新上演。
他已经三天没有展眉笑过了,即使睡着的时候,想的也是这样一件事。说来又是一件蹊跷的事情,自从他离开云宣的那个雨夜,他的大脑仿佛被抽空一般,就再也没有做过一个梦,无论是好梦,还是坏梦。
不梦闲人不梦君,真是一件令人惆怅的事。
可是现实再怎么残酷的事情,总是要睡觉的,就在他强迫自己睡去的第三个晚上,事情还是有了转机。
他在朦胧之间,忽然听到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声音,那悉悉索索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越来越近,渐渐包围他的一切。那咯噔咯噔的声音,与其说是想是敌军的铁蹄,倒不如说像是木头车的两个轮子。
他不会做梦的,他是知道的。
他意识到这一点,从床上跳起来,撩开营帐,外面早已点起了火把,时刻警惕着准备迎敌。
只见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是大大小小的马驹,马驹后面拉着一个木头车,木头车上鼓鼓囊囊的,不知陈列了什么货物。而统统这一切,只有在中间车上的一人驱赶。
申屠衍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那坐在木头车上的人吹了一个口哨,所有的马匹都停了下来,那人笑嘻嘻的跳下车来,走到申屠衍的跟前。
那人很丑,在惨淡的月关下简直丑得鬼哭狼嚎,可是申屠衍却对着他笑了。
——应是故人来。
申屠衍拍拍穆大有的肩膀,笑道,“你怎么会来?”
穆大有也笑,“将军,我怎么来不要紧,关键是我来干什么,”他转头望了望身后的马车,“我是来给你送钱来的。”
马车上盖着的布被缓缓揭开了,满满当当都是棉衣和物资,申屠衍吃惊,敢想问,只听见穆大有说,“经过当年的事情,我已经是一个废人,跟随将军怕是再也不能了,可是我总是想做些什么。”
见申屠衍仍然蹙眉,他笑着说,“反正也不是我的钱,是赵世桓那老儿的钱,那老儿这么多年不知道贪了多少钱,简直富得流油,他逃走的时候没办法带走,猜藏在哪里了?嘿,全在古井底下。”
申屠衍楞了半刻,抚掌大笑,“拿得好!”
作者有话要说:感谢各位亲们的地雷啦,本来眼皮打架,立即清醒了,嗷一声,嘿嘿
☆、第七支伞骨·转(下)
“拿得好!”申屠衍痛快抚掌。他在兖州时就觉得奇怪;那一口口的古井;在那片荒地中事根本打不出水来的;与其说是取水的井。倒是更像是仓库。原来是派了这样的用场。
只是那兖州太守赵世桓数十年来的经营;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临了;变成了这成车成车的军粮与棉衣。他要是知道他的真金白银作了这个用场;不知道会怎么样气青了脸。
“看来我这一趟是来对了!”坐在马车上的男人跳下车来;将鞭子递到申屠衍的手里;“将军;粮草已经送到,我也该回兖州了,我那婆娘还在家里等着我咧!”
申屠衍看着穆大有,想着人生事总是聚少离多,才相聚便要分离,便学着当年在军队里的语气,眯了眯眼,“穆大有,你这么急着逃,莫不是怕我治你一个服役期间临阵脱逃的罪名么?”
穆大有看着申屠衍严肃的神情,心中一沉,回过劲来,大笑,“怕!我怕得很!我穆大有一生没出息,就想经营点小买卖,谁知道误打误撞进了军营,沉浮这几年,胜仗,埋伏,沦陷,被俘,死里逃生,什么都经历过了,现在老胳膊老腿了,折腾不动了,就像回家搂着婆娘好好过日子……”
申屠衍凝视着这个毁容得面目全非的男人,忽然觉得有些感伤,这个残缺的人,几乎已经很难和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联系在一起,穆大有比申屠衍略长几岁,也比他早入伍许多年,所以他入伍的时候便是一直叫穆大有穆大哥的,甚至到了现在也不曾改口,那时,他们一营的弟兄同生死共患难,在一起很多年,甚至连对方身上有几道疤,这些疤从哪里来,都一清二楚,从年少到如今,十余年的功夫,却是同道殊途,青衫枯骨,两不相知。
——同来何事不同归。
同来……何事……不同归……
“我倒是真的很想治你的罪,”申屠衍回过神来,拍拍他的胸膛,“可惜你的军籍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哎……”
“将军……你!”穆大有抬头,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军籍丢失意味着什么,可是终究不能到明面上来说,他向着他的将军抱拳告别,“大恩不言谢!将军,从此山高水长,后会无期,请多保重!”
“保重!”申屠衍也抱拳。再多的话语也比不上一句保重,所以他们也只能道一声保重。
马车在草原上疾驰而去,割开暗夜里的风,溅起满地的草芥子,纵然是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依旧有不顾严寒冒出头的细小植物,它们这样一意孤行,只为曾经来到过这个人间。
他目送他的兄弟离开,忽然觉察到,远处城门上重新亮起了烽火,星星点点,恍然是这无尽天地间的幽灵,他知道,另一场战役就此来开了帷幕。
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对面的城楼上,也同样有一双眼睛在默默看着他们。
无悲无喜。
李胥接到军情的时候,是他进爵的第二天。
李胥年少时封王,在大晁的历史上已经非常少见,这些年来战功卓绝,陛下圣宠,日益鼎盛。
所有的人都以为,在前太子被废之时,所有人都以为,缙王会是日后的东宫之主。然而,皇帝只是不断的赏赐,一赏再赏。
李胥心中冷笑,到底还是那一半血的缘故。
他恭敬的退下,神情肃恭,举止得体得天衣无缝,一回宫,就得到了急报,“恭喜王爷,我军已经收复一都二城,现已经军临玉门关下。”
李胥许久,才抬眸,修长的眉轻挑,“哦,比想象中要快,看来这个申屠衍也不是草包,玉门关守将是谁?”
“回王爷,是拓跋凛麾下最得意的副将之一,耶律跶鲁,此人身长八尺,体宽如山,踱足如震,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他嗤笑一声,“再难对付也不过是一个莽夫……”
“另外,据不可靠消息称,拓跋凛似乎派了一只队伍暗中朝玉门关的方向中来……据目睹的探子称,为首的……很可能是拓跋凛本人。”
他的指节发白,微微颤抖,“都下去吧。”
皇城的春意总是最先在花枝嫩柳中冒出头来,在鸟雀儿的跳动中传递着,他望着满目的春光,却忽然生出了许多惆怅,他这些年来在边关,是极少能够见到这样完整的春天的,今年,却在京中,度过了完完整整的春天,却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他终于缓缓闭上了眼,试图将这人间虚景遗忘,可是还是不能平静,他拔出剑鞘里的剑,剑花飞旋,扬起满园落英缤纷。
几番剑招下来,花瓣慢悠悠的飘落在他的肩头和发间,他抬起头,额头上的汗水从额头冒出来。
——到底是意难平。
这些年的挣扎,荣耀,他的戎马半生,他的父严子孝,都是一场笑话,到头来不过仍是一场空。他和他的那些哥哥们终究是不同的,甚至比不上废太子的地位。从他记事起,他就没有同别的孩子一般在父皇面前撒过娇,比起儿子,他一直是臣子。
宫宇的檐上不知什么时候起停了一只浑身白色的雀儿,他将纸条塞进竹筒里,向天空一抛,那雀儿就飞过来,伸出朱红的小爪儿,抓起它,飞向天际。
——那纸张力透纸背,却只有两行。
人在珍珑中,身常不由己。
五月来时,农忙将尽,忙完桑麻事的人们喜欢常聚在一起谈论些闲话,从王家生的儿子很可能不是王二少爷的种到张家的小娘子居然跟他的公公有一腿,总之,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八卦。
而暮归楼,就是东阙八卦的聚集地。
这些天来,钟檐就时常上暮归楼,当然,不是为了酒。
凡是个人,总是有八卦之心的,被人八卦了一遭,自然又要将别人八卦回去。所以钟师傅上暮归楼,总共就是两件事:八卦了别人,被别人八卦回去。
“话说我们的军队在大将军的带领下,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到了玉门关前……”那好汉眉飞色舞,如同说书一般,钟师傅却高兴不起来。
依旧和昨天一样,自从军队被困玉门关前,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他反反复复听了第五遍了。
可是座上的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出钟檐的异样,依旧雷打不动的进行着第二件事情:将钟檐八卦了回来。
“呀,钟师傅,我们战事说完了,说说你的事吧,听说你讨了一房新媳妇呀,如花似玉什么的?”
“呀,人家小娘子怎么还是没有回来,不会跟前一个一眼,跟人跑了吧?”
“钟师傅,你别太气馁,三天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婆娘还不是满街都是啊,改天叔给你说一个靠谱的……”
如果按照平日的脾气,钟檐是一定要用利嘴说回来的,此时他却不言不语的站起了身,径直朝楼下走去。
云宣是徽州典型的布局,粉墙黛瓦,街道阡陌交错,这些街道他不知道走了多少次,哪里有口古井,哪里有高耸的马头墙,哪里有节妇的牌坊,他闭着眼都能够清楚,但是,他想看到的,却不是这些,他心心念念惦记着的,只是后院的一畦菜地。
他推门进去的时候,一抹灰突突的泥土颜色映入眼帘。
布衣长衫的伞匠忽然蹲下来,喉头滚动着难以抑制的悲伤,他忘记了,那些菜早已上了芯,开了花,老得不能再吃,早就在昨日锄土的时候挖掉了最后一颗菜。
伞铺在第二天就再也没有开过门。
作伞的钟师傅是连夜走的,所以谁也没有惊动,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他是去找了迟迟不肯回来的小媳妇儿。
可是谁知道呢?
——路过的春风总是知道其中的秘密的。
☆、第七支伞骨·合(上)
钟檐没有想到今生今世;他还会会重新踏入这座都城。
如果说犯人塔的那场死劫是他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水岭;那么东阙两个字;无疑是筑在上面的围墙。
在城里;他是青衫红袖招的官家少年郎钟檐;出了城;他是病骨支离万事休的制伞师傅钟檐。
晌午的街上很热闹;这种热闹;是与别的地方很不同的;即使同样烟火风尘;他也带着古都独有的骄傲与荣耀,他牵着马走过蜿蜒曲折的街道,城池的变化总是说不清的,说不清哪里便了,可是心底就是知道,它变了。
就像许多年前一样,拉着一个小尾巴一样的小女孩,后面还跟着满脸怨念的面瘫少年,就这样在这个街道上横冲直撞,为了看游街经过的新科状元郎。
他在东阙城中,走了一阵子,想着还是要回去看看的,十多年前的路已经记不太清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家,严格意义上已经算不得自己的家了,哪里早已经被拆迁,重造,成了或喧哗或冷清的集市……他早该想到,或许他们被流放离京,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以后,这里就没有一个叫做“家”的存在了。
但是终究还是不死心,他拉住了旁边的一个赌骰子的老汉问,“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一户姓钟的人家?”
老汉念着胡须想了很久,才想到,“好像是有,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啦,好像还是个什么官,他们家败落后,好像家底儿都被管家儿卷走了……”
钟檐疑惑,当年他是看着福伯回乡下的,怎么会是他呢?不过钟檐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