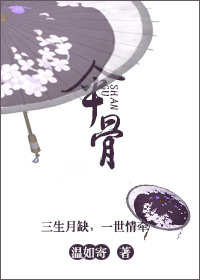伞骨-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伞,而且巧了,昨日我正好遇上当时这批货进入兖州仓库时的守库人,就请这位大哥为钟某作了证,也在这里,既然进仓库之前是没有这些利器的,自然不可能是我或者胡老板放进去的……我相信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的。”
钟师傅说完这一些,太守捻着胡子思忖了半刻,却转变了态度,连声说会秉公办理,钟檐便宽了心,他们又说了一些面上的话,那赵太守便来拉钟檐喝酒,他推辞不过,一一敬了酒,不过是几杯浊酒下肚,那赵太守就有些犯浑,上来牵一旁秦了了的手,便是又亲又摸。
钟檐待秦了了如妹,自然上来阻止,推搡着赵世桓倒地,竟然恰好撞到案桌旁的烛台上,昏死过去。
“这就是全部?赵太守期间可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奇怪的话?”主事猛的想起,“想起来了,席间赵太守看了钟师傅许久,忽然问,‘你姓钟,可不会与云间杜氏有什么关系?’钟师傅那时一愣,马上笑着回答,‘我一个平头小民,怎么可能与这些大人物扯上关系?’太守笑笑,就没有再问下去,这大概是最奇怪的对话了吧?”
申屠衍神色如常,答了一声知道了,便径自走了,剩身后秦了了的哭哭啼啼,和主事的叹息声,“什么表哥啊,终究不是亲的,遇上也不上心……”
申屠衍沿着并不繁华的街道走了一路,想着这件事情的始末,当他听到云间杜氏时,只觉得两耳震得一嗡,心弦崩塌。
他站在兖州境内的街道上,黑云低垂,凛风有摧城之势,他抬头望天,一滴雨水打在他的脸颊上,他心中了然,这兖州城,只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一夜,申屠衍睡得并不踏实,开了窗,听见对面房里琴音传来,一整夜都是反反复复的《伊川歌》。
清幽苦涩,呜咽反恻。
申屠衍心头很不是滋味,他以为自己死里逃生以后,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可是因为钟檐他回来了。
兖州位于边防,北临祁镧山脉,与金渡川也不过是数百里之远。
他心念一动,向楼下酒肆买了好酒,借了马,径直向城门外策马而去。
夜如穹庐,他沿着河岸逆向而行,已经入冬,河水接近干涸,依旧可以听到溪水潺潺漏过石缝的声音。
经过长途的跋涉,马儿已经累得呼呼喘气,申屠索性下马,沿着干涸的河岸又走了一段,这一段河域他们曾经驻扎过一段时间,因此分外熟络。这里的河水常年浑浊不堪,没有一处是干净水源,那时,他常年听手下的将士口无遮拦的胡侃,金渡川,金渡川,浪花儿淘尽的不是英雄,是淤泥和草根。
可是那时申屠衍就知道,他们是以污泥和草根自比,他们都不是英雄,如果不是参军入了伍,他们都不过是桥边镇尾做着小营生的普通人。
他们不是能把握战事走向和生杀予夺的贵族统治,没有人喜欢打仗,他们之所以当兵,只是因为有想要守护的土地和家人。
眼前忽然出现一堆乱石和土堆,横七竖八,离离草枯荣,越发显得萧瑟和荒凉,他的目光一沉,膝盖狠狠的落下。
八千将士,尽葬于此。
——这是他欠他们的一跪,他现在来还了。
如果不是有那一番际遇,他也埋在这里了。他将酒慢慢洒入土中,他们死的时候,很多已经面目全非,肢体不全,如今都一齐埋在这里,他只是一个挨一个唤过名去,就像旧时练兵点名一般,黄泉路上若能听见个,就应一声。
“水三儿,王二狗,刘小幺,……还有,穆大哥。”
他的声音越发洪亮,回旋在这夜色中,好像下一秒,土里就会有人蹦出来,响亮地答应着,“到!”
在他念出最后一个名字时,他的嘴角浮现了笑意,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候,一个一个青葱般的苗又重新回到他的面前,都说世间最蹉跎,莫过于美人辞镜,英雄白头,还好,他们都永不会老去了。
“哎,现在世道艰难,北有虎狼之势,墙内手足干戈,朝中又有与高俅秦桧比肩之人……但是有我在之日,必定护你们的家园一日周全……以后忘记了所有,也不会忘记”
“还记得我说起过的小檐儿,我找到他了,他很好。会手艺会扎伞会骂人……他活得这样好,唯一的缺憾,就是不能娶上一门好的媳妇……说来也是好笑,我盼着他能娶上好媳妇,又不希望他能娶上媳妇……”
“如果来年……怕是没有来年了,我就带着他,来你们的坟头看你们,他脾气不好,可是没有什么坏心……”
那天晚上他唠唠叨叨说了许多,该说的,不能说的,掏心掏窝的,都说了,到了最后,忽的想起自己参军的缘由,竟然已经是许久之前的事了。
************
那时钟檐和赵小姐的亲事刚黄,钟檐自从淋雨发烧之后便整日整日的呆在屋里,很有些魔怔了的前兆,他去像往常一般去给他理衣,他竟然跟见鬼了一般跳到了三丈外,后来因着他犯了一件天大的事,他就莫名配回了柴房,重新干起了杂役。
岁月深长,过了一季又一季的严冬腊月。
那一年是永熙十年,北边流寇横行,加上戎狄不断清扰,游民不断涌入东阙城,钟夫人和杜夫人心肠软,便在自家门口搭起了粥篷施粥。
一个一个面黄肌瘦的人排着队伍在面前缓缓挪动,路边却有一个老乞丐白眼相对,面有嘲讽之气,钟檐奇怪的问他为什么,老乞丐笑,“夫人固然心善,可是想过没有,今日这一顿饱了,明日呢?内墙不宁,人不过是无巢之鸟,离土之树……再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老乞丐看似邋遢,却比世人都看得清,钟檐狠狠的握紧了拳头,吐出八个字,“文可安内,武能定国。”
站在一旁施粥的申屠衍听得分明,也为他后来的路布下了潜生暗长的种子。
****************
第一日清早,胡老板竟然出乎寻常被无罪释放,这个可把胡家的主事也乐坏了,就差扑到主人身上,泪眼汪汪,演一场主仆情深。
申屠衍被他们主仆二人腻歪的不行,所以他们两个很是不仗义拐弯抹角的提出家中生意无人照顾自家婆娘要出墙要先云宣时,立马答应了。
送走两尊大佛以后,申屠衍就去监狱探了监。
那狱卒拦在门口,死活都不让进,说是刺杀朝廷官员的重犯,多少钱都不好使,申屠衍不愿意正面与他们起冲突,只得回了头。
可是乘着狱卒不留心,他已经上了房,循着声音,他终于找到了钟檐的那间牢房。扒开一片瓦片,光线从瓦片的缝隙里漏进去,依旧昏暗不明,但可以影影绰绰的看清那墙角是蹲着一个一个人的,头发散乱,手脚被铁链锁着,身下的稻草都被凝成块的污血浸透了,像是被上了刑。
他想要来口喊他,却终究觉得不合时宜,只能蹲着看着,好像他是一块揉碎了的伤药,只要多看几眼,那人身上的伤便会好一块儿似的。
那个清晨,申屠将军蹲在牢房的屋顶上,迎着风蹲了好几个时辰,却最终起身,他想,他的小檐儿,终究是要自己堂堂正正从牢房里接出来的。
他起身的时候,觉得日头有些刺眼,看似一叶障目,却仍旧不得不迎接这一场风波。
☆、第四支伞骨·起(上)
钟檐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被铁栏杆分割成几块的一角天空。
——是冬天的模样。
昨日刚被押着去问询,几个狱卒将他绑在铁链上,嘿嘿笑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用皮鞭老虎凳之类的刑具,就足以让一个寻常百姓吓去了半条魂。
也难怪,在这黑漆漆的无间地狱里呆久了,是人也变成半条鬼了。
钟师傅半辈子在这尘世摸爬滚打,怎么能不把这个世间那点犄角旮旯事看得明白,“快说,你刺杀朝廷命官又什么企图?”“是谁派你来的?”“快说!你是不是北靖奸细?”
钟檐觉得实在是荒谬,咬紧了牙关,狠狠地看了一眼那一群人,嘴边扯了一丝笑,“肮赃腌渍泼辣的狗杂碎!”他素来一张嘴不饶人,既然知道结果都会是一顿毒打,不如让这口舌爽利些。
他被重新丢进这湿冷的牢房时,全身已经动弹不得,他只能一动不动的歪在墙边,说来也是巧,他的这间牢房巧好就是胡老板蹲着的那一间,他万万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他蹲了。
胡老板见了他,就哭爹喊娘,一会儿说着连累了钟师傅,真是罪过大发了,一会儿说认识这么仗义的人值了,如果有朝一日出去就把自己的东西统统分给他一半,就是老婆孩子也……
“别介,胡老板,我怕折寿!”
受了重刑,他的精神却很好,只淡笑看着他。也许是疼痛刺激了神经,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里,有狱卒看守,犯人们都不敢太造次,到了晚上,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偷了嫂子的书生,盘踞山上的流扉,失子心智不正常的疯女人……一厢唱罢一方又登场,正是好不热闹。
钟檐眯了眼,静静的看戏,想着应该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二次牢狱之灾了吧。
他的第一次牢狱之灾,在他的二十岁,与他同受的有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小妍,他们像牲畜一般白天被赶到石料场干活,夜里被关进这深不见底的犯人塔中,那时,他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那暗无天日的流放生涯中。
他却还活着,可是除了命,他什么都失去了。
这一次,不知道他还可以失去什么。次日清晨,胡老板就被放了出去,临去前,又哭带闹的演了一出,咬着帕子就是梨花带雨。
钟檐想,果然是一家子,都那么爱演。胡老板闹腾了一场,出牢门的步伐却没有慢半步,一溜烟儿就没影了。
安静下来,大把大把的时间空着,钟檐也想通了许多的事。从扣下那批货,到抓捕胡老板,再到赵世桓的死,恐怕都是彻头彻尾的圈套罢了。
而他,胡老板,秦了了,甚至赵世桓,都是这局棋中的棋子。
——不!这局棋,恐怕从申屠衍找到了他,就开始了。
他忽然想起了申屠衍,衣襟上已经布满了汗滴,冷而稠密的感觉紧紧抓住他的背。
***************
兖州缺水,到了冬天一瓢水便更是稀罕,兖州城十里外便有这样一处地,荒地黄沙,只有突兀的一口口枯井。
水面干涸,一口枯井便是这大地的一个疮疤。
在钟檐在牢中蹲着的时候,申屠衍正盯着一口又一口的枯井,看了约莫有半个时辰。
——他为什么在此处?
他是尾随了官府的衙役而来的,他为什么会尾随衙役呢?还要从昨晚说起,那晚上,他思前想后,将这件事情也重新想了一遍,觉得整件事情实在蹊跷,赵世桓在席上问钟檐这样一句话,那么他肯定也应该认出了钟檐,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是在席间才看出钟檐的身份,说明他事先是不知情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引钟檐来云宣呢?
他想了许久,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年头,或许不是钟檐,任何人都可以……或许,事情的源头……是那一堆忽然冒出来的兵器?
他这样想着,便连夜潜入了看守兵器的库房,说巧不巧,正好遇上了这监守自盗的衙役了。
申屠衍想,这群衙役不穿官府,黑衣蒙面的装束,定然是要做不好的事情去了。于是他一路跟踪,看见那些黑衣人青骑出城停在这里,纷纷将兵刃扔入了一口又一口的枯井。
天已经大亮了起来,他低头朝枯井望去,深不见底,黑漆漆的一片。申屠衍不能肯定,这口井到底有多深,没有把握自己下了井,有没有活命上来的机会。
烈日当空,他却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忽然,他看到了土堆枯井之间有几个人影闪过,他怀疑是那群人去而复返,加快了脚步,追了上去。
一直到了进城的城门中,那些人影却失去了踪影。
*************************
而此时,钟檐正坐在牢底闭目养身。
他虽然闭着眼,却没有睡着,闭了眼,种种声音都朝耳边而来,谩骂的,啜泣的,咬耳朵嘀咕的,地面上蚊虫爬行的,都没有转弯没有分别的入了耳。
“咱们老爷可真是……大半辈子的官儿,什么酒色财气没见过,偏偏被一个小姑娘迷得没了命,啧啧啧……色字头上一把刀呀。”
“可不是,听说小姐和姑爷正从京城里往这边赶。你看……那个人……多半是死人了。”
“可不是……姑爷是萧相跟前的红人,指定不会放过他……不过那妹子可真是个美人啊,水捏的冰砌的,等她阿哥一死,不是红姑娘的命啊,就是当外室的。”
钟檐听着他们议论,他忽然想起来,就在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