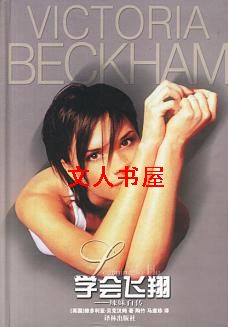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一家大型俱乐部,名叫BCM,滑稽的是,我记得这是洁芮很久以前做舞女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从里到外都挤满了人。这地方几乎有足球场那么大,上下两层,绝对有数千人。楼上是声音很响的汽车库摇滚乐,楼下更具流行乐的旋律——这其实更让我喜欢一点。我们的演出在楼上。那人群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从台上看到的尽是一片人海。
“那么,”当欢呼声、尖叫声静下来一点足以让我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我说道,“很明显,今晚这里有些人‘心神迷乱’了。”
接着人群又开始爆发。即使我们拿了第一也不会这么快乐。
演出结束后,戴恩说他要到楼下去主持,所以我们俩都下去了,结果我们在音乐主持人的包厢里,一浪接一浪的人群要我们在他们拿出来的T恤衫上签名。
“好的,伙计们”——这是戴恩的主持风格——“我们这里有一位嘉宾主持,想来客串一下。这就是‘高贵辣妹’。”
我戴上耳机,以前我从来没干过这个。一片寂静。我本该在唱片开始播放的时候再开始刮碟。而我在唱片开始之前就刮了起来。
这让人非常尴尬,所以戴恩说:“这首歌你们也许熟悉。”
这是《斯皮勒》。戴恩将它刮成了碎片,唱片真的被刮碎了,然后换成了《心神迷乱》。人群欢呼起来。
我从音乐主持人的包厢跳到了台上,开始疯狂地跳了起来。人群也疯狂了。保安们不高兴,而我高兴。然后我的伴舞们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台上,开始随意地跳了起来。那绝对让人难以相信。
接着戴恩通过麦克风说,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签名,你们得脱下衣服。突然,数千人脱下了他们的衣服,有些人,让我告诉你,并不雅观,洗了上百次的内裤、看起来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胸罩,一切都变成了可怕的内衣裤灰色的阴影。一切都变得非常粗俗——就像伊维萨岛的“红灯区”,但是要滑稽无数倍。
这时,保安建议我们离开,我们没有争辩。那场面已经不堪人目了。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女孩在台下向戴恩喊着,请他在她的胸部签个名,同时,她镇静自若地脱下了衣服。我不记得他是否那么做了。
我们在马略卡岛呆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感到已经做好准备面对外界可能给我的任何评价。第二天也正是民事法庭贝克汉姆和莫顿案关键的一次听证会。听证会在高级法院举行,幸运的是我们无须出席。
大约一星期前我花了一个下午在律师办公室浏览安德鲁·莫顿从剪报上拼凑起来的一堆垃圾,还有叛徒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一些偷来的新闻。坦白地讲,这真可怜,也许是因为从我们听说安德鲁·莫顿被牵涉在内的那一刻起,我的律师已经获得了针对他们所有人的禁令:安德鲁·莫顿、出版商以及马克·尼波里特——因此,即使安德鲁·莫顿正在写,他也知道他的手已经被法院捆住了。在马克·尼波里特交给安德鲁·莫顿的东西里——法院后来坚持让马克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有六卷胶片,包括布鲁克林的照片、马克和另外一个人在我们公寓里拍的照片、我们新房子的照片,照片背后还仔细地写着文字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拍照。正是因为法院的禁令,安德鲁·莫顿才无法使用这些照片。即使他无法使用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任何机密材料,但是看到你的生活那样被摊在桌子上还是非常令人沮丧,出来的时候我气得像一头母牛,但是大卫倒像人人离不开的“飘洗”牌洗衣粉:马克·尼波里特不会对他的金童指指点点,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问题的一半可能出于嫉妒。书里没有什么特别恶意中伤的内容——还是重复报纸上的老一套,那些话本来就不真实——但只是说得有点下流。安德鲁·莫顿真的没有做什么研究·。他自认为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只是一个收集剪报的人。
惟一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他们怎么会拼凑出我的父母和大卫的父母不和的事情。那太让人痛苦了。
随着法庭听证的临近,我们整理出对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反对意见,接着我们了结了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
他们双方都对法庭做了保证,我不能说——虽然我也许想说出——具体的调解条款是什么,但是,莫顿一方依然可以声称这场官司对他们是一个胜利,他们利用法庭听证宣传了这本窃取来的书。后来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言谈又作出道歉。
就这样我们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结束了,但是我们对马克·尼波里特的诉讼还在继续。
第二天我们去了德国。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星期的生菜。但是,你知道,“演出必须继续”。
兴奋感让我坚持到了表演结束,但是,那些灯光真的对我有影响,突然,我感到头部剧烈疼痛,我感到恶心。我受不…了那灯光,在化妆室里我蜷缩成一团。我不住地呻吟,说着“我不知道怎么了”,戴恩说“你还好吗,维珂?”我回答说“不好,戴恩。”我感觉一点也不好。
戴恩把我送回旅馆,同时保安设法找来了医生。
“我的头疼得厉害,我感到恶心,我的脖子痛,我有点昏昏沉沉的。我无法正常工作,”我告诉她。
“你受病毒感染了,”她说。“我要给你打一针。”
“不,不要打针。”
医生可能认为我是什么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大卫曾经说过,无论你做什么,不要让他们给你打针。我无法对她说明情况。
所以这位医生给我开了个药方,原来是一个小瓶,有一个可以挤压的滴管。二十滴。
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头疼得厉害。我特别容易焦虑,如果我伤心,我就会哭,闭上眼睛,拼命地挤,然后,我就会听到某种声音,脑袋里产生噪音,好像是警报声还有回声。我经常对妈妈说,是什么东西在我的脑袋里让我发疯?接着头痛就来了。
我不知道那些滴剂是用来干什么的,但是,我无法人睡,翻过来,掉过去。我特别好出汗。每次看到光的时候,都像一把匕首插在我的头上。我能听到自己用极高的音调尖叫着,不是通常那种痛苦的声音,而是猫发出的噪声。我知道我必须得再用一些那种药,但是我把它搁在套间的客厅里了。我在卧室里,想到要起床、走几英尺远——这简直就像让我去游英吉利海峡。
我拿起电话,接通了总台。他们那里只有值夜班的人,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要的是“‘真步者’中的一员”——他们以为我在抱怨什么晚会,什么也没听明白,因此什么也帮不了我。
最后,我找到了菲奥纳,这次旅行中,她负责为我化妆。
菲奥纳找来了护理人员,还是那位医生。
太可怕了。我感到恶心,我讲不了话,我在颤抖——感觉既热又冷。我确信患了脑膜炎。我作为脑膜炎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人已有好几年了,这是一个全国性慈善机构——“力争阻止脑膜炎和败血病致命或致残”,事实上,最近我还获得了某个奖项的提名以表彰我的工作。不管怎么说,我因此而了解所有那些症状和检查。一个症状是皮疹。但是当时我感到极其不舒服,我不想费神去找皮疹了。我只是在想,假如我患上了脑炎横竖是个死。
我打了一针,不过,坦率地讲,这一点用也没有。我动不了,因为我的后背和脖子疼得厉害——又一个脑膜炎的症状——我整夜没睡觉。
一切安排都被取消了,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回家了。我妈妈已经为我预约了当地的全科医生。我颤抖不止,眼神直愣愣的,像个疯女人。
“你的压力太大了,”他说。按他的观点,这是一次严重的偏头痛。我妈妈不相信。她为我约好了一位脑颅专家,让我一大早去见他。
他花了一个小时为我做检查。他的结论不一样。“你患了病毒性脑膜炎,”他说。
无须治疗,只须休息。它不会致命,但是可能停留在我的肌体内长达一年。
第二天这就成了头版新闻,不过半数报纸遗漏了病毒性这个部分。但是又有谁在乎它的准确性呢?
第二十六章 找回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不喜欢,你一定会解雇我的,”当南希告诉我,她已安排我两个星期之内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她这样说道。
两个星期?难道她不明白我有歌要写、和我合作的人要从美国飞来吗?
显然,她和大卫已经谈过了:大卫认为我需要照顾,而做这件事惟一的人选就是他。南希同意了。
结果,我在曼彻斯特呆了近三个星期。开始的几天我感觉糟糕透了。除了所有这一切以外,有一家报纸甚至问我要病假条。但是,慢慢地我又有了一点力气,情况有了转机。首先,我的耳朵上不再经常夹着个电话。生平第一次我感觉无事可做真好;大卫训练回来时就能看到我,收拾屋子,忙着做午饭,真好;和“坦克发动机托马斯”(玩具名)、“邮差帕特”以及它们的小朋友布鲁克林一起玩真好;全家人一起开车去游泳真好;不紧不慢懒洋洋地洗把澡真好。我开始意识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我说的话:我为自己做的事太少。我从来不和朋友出去吃饭,从来不去健身房。因为时间从来都不够用。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感觉我要工作、工作、工作呢?自从我开始在贾森学校上学,我就一直有目标。
首先是一级,接着是二级,连续不断。每一个证书只是进入下一个目标的踏脚石,然后是再下一个目标,直至我的最后的目标——荣誉。
那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它给了我思考的时间。我真的希望不再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曼彻斯特,不要工作。从我16岁起,我就一直靠着一只手提箱过日子。我只想卸下衣箱,有一个真正的家。但是如此简单、大部分人都拥有的东西对我却只是一个梦。我有时对大卫说,告诉我那种生活我们会有的,告诉我。
除了努力思考我的生活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影响,我也开始掂量它对我父母的影响。不解内情的人肯定想,哦,漂亮的房子、漂亮的汽车、大把大把的钱、奢侈的度假;但是他们意识不到与之相伴的是什么:事实是我妈妈每次听收音机或拿起一份报纸都会听到、看到关于我的不好的东西。直到我有了布鲁克林我才理解这对他们该有多难。如果有人关于我的孩子说出那样的话,我不会有我的父母一半的理智。生布鲁克林之前,当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经常会发脾气,并且说,我不明白你们操的哪门子心。他们写的又不是你们。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住在家里的时候,和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在一起时我整天都尽量地幽默一些、轻松一些,但是回到家里,我会把所有的压力都发泄在我爸爸或者妈妈身上。我本不该那么做的,应该换个方向才对。对你最亲近的人不应该成为你的受气包。
而且无论多少钱都不能弥补那一点。虽然我总是和他们分享所有的东西,正如他们和我分享一切,但是,不能一直都是你付账,这会让人觉得难堪。让父亲或者母亲接受这一点肯定很难,尤其是爸爸。因为我爸爸一直是家里挣面包的人,而现在我比他富裕得多了。
我家里从没有人妒忌我,他们从来不向我要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给他们一些我知道他们肯定喜爱、欣赏的东西。但是我为他们买东西的惟一途径是把它们作为意外的礼物。克里斯琴甚至不肯接受20英镑买汽油的钱。
那就是说,虽然我给爸爸买了一辆“保时捷”,给妈妈买了钻石耳饰,给我的弟弟、妹妹买了房子,给他们所有的人买了手表——所有那些东西,但是,你为他们买这么多东西一定不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在接受施舍。
一家人出去吃饭时,如果我要付账,我爸爸就会说,不,他来付账,然后我就感到内疚。内疚是因为没有我的家人,我什么都不会有。为了实现我的梦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我。从我们家到布罗克斯堡,我妈妈开车走过了无数个小时,有时通宵为我做服装;我爸爸在经营方面为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榜样,总是提醒我是他的女儿,他知道我不会放弃。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总是站在我的一边,对我讲实话,而其他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露易丝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人们说,你知道要把他带大将会很艰难。但是我不明白。我认定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被教会说请、谢谢。他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现在我开始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这不是我或大卫做与不做的事,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太忙。
当然我可以把布鲁克林培养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