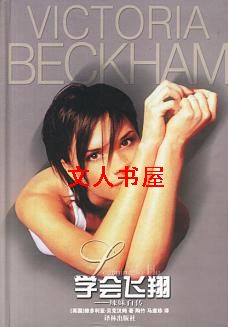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
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
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
他挣钱不多——没有什么野心,但也绝不懒惰。他从来跟我开口要过一个英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他会成为某个人极好的丈夫。
虽然有同样的父母,我们的差别却如此大,这依然让我吃惊。露易丝小的时候,长得像秀兰·邓波儿,一头红色鬈发,酒窝,微笑。她非常淘气,还喜欢指使人,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绝对是多动症,跑出去玩的总是她,而我所做的好像就是干活儿——维多利亚,不好动又懂事的那一个。
有些时候,露易丝一定不喜欢看见我。因为我不是个感觉迟钝的人,我能想像这个情景:姐姐总是被人注意,而妹妹几乎总是被人忽视。而别人却是那么不敏感。就像几天前我遇见露易丝的一个朋友的妈妈,露易丝的这个朋友快要结婚了。这位女士问我,“你能来参加婚礼吗?”我说,“是的;露易丝也去。”但是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说,“是的;但你和大卫能来吗?”听到这话露易丝走了。发生那样的事,你简直感到糟糕透了。
但至少从表面来看,我想露易丝很喜欢做“高贵辣妹”的妹妹。我对她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她不会喜欢做我这样的人。露易丝太喜欢玩,不可能成为工作狂。事实上她参加的名人聚会比我和大卫都多。因为当我工作时,我就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社交活动。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社交生活。但当我累极了,十一点钟疲惫不堪地进家门,我问,“露易丝呢?”我妈妈说,“出去了。”这时我就有些恼火了。我确实会想,老天,我忙得头都掉了,而其他人倒出去玩了。但事实是,那正是我喜欢的。
我想我可能是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不是因为钱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做一个“辣妹”给了我保持自我的信心。我总是明智而谨慎,但我不是天生的反复无常讨人厌的女人。现在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防御机制,它的产生是因为我脸上的粉刺以及我没有朋友。?公园晚会“的前四天是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真是绝妙的安排。没有像我计划的那样外出度个真正的长假(这意味着两周时间),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在”公园晚会“后休息一周。按计划”辣妹“要为双A主打单曲《怨》和《让爱引路》拍摄影像。
似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同一时刻。《心神迷乱》计划在8月14日发行,大卫在这个时候又要回到曼彻斯特,但大部分艰辛的宣传工作会在发行之前做,其时大卫还和我在一起。
首都电台和“亲吻”调频台播放这首歌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而且很快就热播起来——尽管它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也让我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因为这首歌六周以后才能进商店——电台不停地播,却没有人能买到。尽管问题是有的,但是这倒也是件好事,只是我们得想办法保持这个势头。首先,我们得把影像制作好。
影像制作的导演杰克·内华说他想让我用长发造型。他想塑造一个“霹雳神探”般的未来派形象,用一台鼓风机把我的长发吹起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单曲的封面,还有其他一些宣传品,如杂志。“辣妹”巡演的时候我已经让詹妮给我剪了短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个发型,因此在宣传品里我只有短短的头发站在头上。
因此泰勒——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就遇到他了,当时他在给梅尔·B做头发,现在他给我做——拿来一条一条数英尺长的头发。做法是这样的,他把我的头发分缝,把一条长发剪短几英寸,再把它黏到我的头皮上。花了几个小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疼,只是有几秒钟我感到头皮有些冷,但实在是令人厌倦。
只是在我们拍摄这部影像时,布鲁克林才第一次看到我留着长发。至少他看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长头发女人。他奇怪地看着我。戴恩甚至称我为“犹太辣妹”,“忧郁辣妹”又有了变化。但不容否认的是,长发很适合我的服装,当鼓风机吹起时,看上去真的不错。
我们的造型师是个叫威尔·阿迪亚米的小伙子,是戴恩带来的,他为“超凡四帅”做事。而且我知道他曾经与米西·艾略特(美国说唱歌手)、普夫·戴迪(词曲创作者、混音师、制作人、“坏男孩”唱片公司总裁)一起工作。但威尔是个纯粹的伦敦南部人。我不是那种把什么都交给造型师的人。但威尔很不错,有很多非常好的主意,而且一点也不固执,总能接受他人意见。
在影像拍摄的间隙,我们拍了一部采访宣传片。因此我们都穿着演出服,化好妆,而我,还有头发。所以人们看了宣传片之后,所有人都喜欢那个长发造型。这真是痛苦。“抓住安特和戴克”(安特和戴克是独立电视台极为成功的演唱新秀节目的主持人)每星期六早晨在独立电视台的SM:TV(后来变成了CD:UK)节目播出。为了在十点钟之前准备好,我和泰勒六点半就得赶到工作室,那就是说,我五点半就得从我妈妈家里出发。我的发型每次都得重新做。我本可以说,别做了,还是回到短发型吧,给我每天省下几个小时。但我知道长发更适合那首歌。
与我共事肯定很糟糕,因为正像我爸爸一样,我确信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并不是说我是最好的,我还没那么自大,或者至少我希望不是。只是每件事我都要过问,所以要是出什么错的话,事后我除了自己谁也不能责备。不论是在电视录播室,还是在摄影间,我都要预先知道灯光怎样,摄像镜头如何,舞者穿什么,我穿什么。正是由于我在工作室和舞台上做过一些时候,所以我知道什么造型最适合我,我知道什么看上去不错,我知道什么面料在什么灯光下最出彩。我知道我想具有什么样的外表,我知道我想要怎样的声音效果,我知道我想怎样推销自己。所有这些事我都担心,假如这关系到我的名誉,我会总是为这些事担心,因为我相信这能够说明问题:服装、舞蹈、表演、音乐、以及绝对专业的安排。
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因此我总是很忙。
过去,唱片发行后,你只是等着它登上排行榜,它极少会直达榜首。而现在,唱片发行的第一周你经常能拿到第一。实际上,唱片公司通常在发行的第二天就知道它是否能在本周日拿到第一。
我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因如下:洁芮已拿到了第一,梅兰妮·B、梅兰妮·C都已拿到了第一。爱玛是惟一没拿到第一的“辣妹”,因为她总是和洁芮撞车,而洁芮就是洁芮,她是铁了心要赢的。不满足于仅仅看到歌迷喜欢谁的歌,洁芮还很方便地在克里斯·伊文斯(英国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曾经是洁芮的男友)的臂弯里找到了爱情,或者至少是找到了宣传的工具。那一周到处都是洁芮,爱玛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屈居第二。
其实我这么说有点荒唐。有时候,我们忘了在这个圈子里能进入前五名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了。
我、戴恩没有和洁芮撞车,但在制作影像时,我们发现将和一个叫斯皮勒的意大利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一较高下,他的那首歌已在俱乐部里演奏了若干个月,名叫《老一套的喷气式(如果这不是爱)》。它已经出现在了汇编专辑里,这些俱乐部舞曲经常这,样,但还没有作为单曲发行。直到现在,唱片公司才意识到他们埋没了一首冠军曲。
正如《心神迷乱》,《斯皮勒》——我们一直这么指代它——是一张舞曲唱片。《斯皮勒》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歌手演唱的。它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这首歌,而且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歌与它在同一个星期推出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赢。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推后一周,因为下一周有梅尔·C的歌,两家唱片公司之间有口头协议,我们不能和她撞车。若提前一周,我们将撞上麦当娜。(结果证明,第一周我们比麦当娜多卖出四万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付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
至少,我们谁也没指望拿第一。
数周的排练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害怕了。我们做了影像摄制的常规工作,也为“流行音乐排行榜”做了常规工作,但在数万名观众面前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宣传——电台采访、报纸采访、电视采访——车进,车出,我却很兴奋,我真不知道大卫怎么能容忍我的。
7月4日:去年今日是我们的婚礼;今年却一如往常,一刻不停地做宣传。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一小时的车去伦敦北边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那是我给大卫的一个惊喜,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我们在那儿做了时间允许的所有项目:面部保健、全身按摩,等等。第二天是大卫为我准备的惊喜——我们新家露台上的烛光晚餐——有点疯狂,因为那还只是个建筑工地,还要等几个月才能完工。他得买所有的东西:可加热的推车、桌子、椅子、白色台布、枝行大烛台、碗、盘子、筷子。由于他没时间亲自做每件事,我妈妈和露易丝得去把家具运回家。到家后,打开盒子,他们才发现是要自己安装的,所以他们打电话叫迪和戴尔来帮忙。我妈妈说有点像“挑战安妮卡”(BBC一台的一档游戏节目),拿着桌子的组装件、春卷、香槟楼上楼下地跑。但那么做是值得的。天气真好,我们坐在露台上,用五十支蜡烛照明,风总是把它们吹灭,但这太浪漫了。只有我们,俯瞰着花园,想像着完工后的样子。
三天后天气转阴,天气预报说天气会更糟,英格兰上空有暴风雨。尽管我们不会淋雨,但观众却没有避雨的场所。
会有人不怕麻烦来观看吗?
尽管我很紧张,这是我记忆中最紧张的一次,但当音乐会开始,特拉维斯(苏格兰的摇滚乐队,又译“崔维斯合唱团”)唱起《为什么总让我淋雨》时,甚至连我也大笑起来。事实上没下雨,但是云层却越聚越厚。
我在骑士桥的曼登林旅馆做好发型,化好妆。到后台时,我才见到其他人。
看着我们前面的乐队在表演,我庆幸我们已改了装束;似乎所有的女孩子——从“台阶”到“真命天女”——都穿着桌布式的上衣。
在我们前面表演的是“野人花园”,这是两个澳大利亚来的男孩。此时我已紧张到连厕所都不要去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惊慌中,我听到他们正在唱奇怪的歌词,像什么直到你受伤后才知道珍惜爱情,直到你失去了才知道你曾拥有什么,你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就是我们了。戴恩先唱《烦扰》。我能看到的是,舞台上到处都是电线、电缆、坑洞。我一直在想,千万别跌倒了。戴恩和他的伴舞、我和我的伴舞、加上安迪和约翰尼上了台,大概有二十四人。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舞台上,人显得特别多,尤其是你都没机会去排练。当然其他乐队也没有排练。
然后我走出来,听到了巨大的声浪。舞台高出地面大约十英尺,我往下看去,看到的是成千上万只脑袋。我以前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甚至连“辣妹”演唱组也没有过。
就在台下站成半圆形的摄影记者中间有一张我非常熟悉的脸在向我微笑,多迷人的微笑。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举起那台便携式摄像机。这时音乐响起来了。
第二十四章 漫步“绿野仙踪”
身穿未来派的白色皮装,金色的腰带,一头亮闪闪的飘洒的长发,胳膊上有一道条形码——那是凯琳——她像往常一样为我化妆——从一只塑料包上剪下来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成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版新闻,从《观察家》到《世界新闻周刊》。大多数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只有一两家说我在假唱。
该死,我当然要假唱。这是一支舞曲,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像一支舞曲,你得在你的声音上加些电子效果。每一支舞曲都有——包括《斯皮勒》。现场演唱时谁的声音听起来会是那种样子?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乔·米克——我爸爸曾是他的签约歌手——发明了混响录音,曾在他好莱威公寓的洗澡间里为约翰·列顿(英国歌星)录了音(《约翰尼记得我》,1961,你们这些喜欢收集流行音乐的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