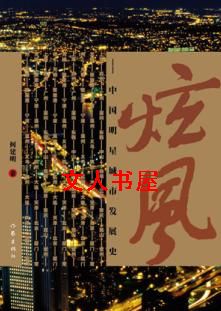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管勤、我和老龚一齐盯着陈涛,陈涛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当然如果设身处地为陈涛(也包括我和老龚)想想,管勤从这里跑出去会受牵连的,怂恿逃犯出逃,知情不报,罪名都现成。可我们能为洗刷清自己而把管勤抓起来上交吗?这样十之八九要送掉管勤的命。这一层管勤也是明白的,他冲陈涛说老陈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么?陈涛不语。管勤又说老陈不管怎么说咱一个锅里摸勺子一年多,总还有点交情吧。陈涛说我和你讲交情可人家不和咱讲交情。管勤说陈涛你可以把我抓起来去邀功,可这样你就扮演了杀人凶手的角色。咱们当右派并没有真罪行,可把一个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就是真正的犯了罪,成了千古罪人。陈涛你一辈子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你好好想想吧。
我、老龚、也包括陈涛都没料到管勤会说出这么一通话来,眼光又一齐转到他的脸上。我发现管勤的脸生动起来,也有了光泽,抬头一看,晨曦已从窝棚窗口照进屋里,天亮了。但升起的太阳并不能驱散我们心中的阴影,局面是严峻的,也是不可捉摸的。我猜不透别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可我清楚我自己的。我觉得无论如何是不能把管勤推向死路的,那样真的会像管勤所说的,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看着管勤那张差不多已由鬼变成人的脸,说老管你从这儿跑出去要是被抓住,能不说你到过“御花园”吗?管勤说我不会说,肯定不会说。陈涛哼了声,说现在许诺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攻守同盟这一套对付日本人和国民党还行,对付共产党可是打错了算盘。管勤急了,眼盯着陈涛说老陈我对天发誓行不行啊,以后出事我要是把你们供出来就天打五雷轰!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陈涛不语了。不住地摇头叹气,过会儿说老管你当我老陈是铁石心肠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可……老龚打断说老陈有你这句话我就往下说了,咱都是有良心的人,不是作恶事的人,以前咱和老管相处得也很不错,不能看着他往悬崖里掉。陈涛又打断老龚说可这遭乱事摆在这儿,叫咱咋办好哩。老龚说关键是看我们想怎么着,打什么谱,有了谱办法总能想得出来的,不信咱们就找不到一个既让老管离开这儿咱们又不会担干系的办法。又应了姜是老的辣那句话。经老龚这么一说,我和陈涛不由对视了一眼,我说会有一个两全办法的。陈涛说那就想想看吧,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想糊弄共产党是不容易的。
说起来陈涛还是讲交情的,他杀蛇款待了管勤,之后我们又帮管勤从他的藏匿点刨出了衣物。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两全”办法业已在头脑里成熟。再之后我们便在“御花园”窝棚门前出演了一场除我们当事人外,任何人都不会有眼福看到的人间戏剧(是喜剧?还是悲剧?难以判断),每个人的台词都十分地精彩:
陈:管勤,逃跑是罪上加罪,党的政策你也很清楚,你打谱咋办呢?
管:我愿意去大场自首,听候上级处理。
陈:这很好,这是摆在你面前惟一的光明大道。
管:是。
陈:老龚、老周,你们说是现在立即把管勤押送大场呢,还是等到下午,看管教今天来不来,来了让管教带走,不来咱们就送了去。
龚:等下午。
周:等管教来了好。
陈:那好吧,可咱们上午干活,该把他怎样处置呢?
周:把他绑在树上。
龚:这办法好,我绑。
陈:(向管勤)要老老实实的。
管:我不跑。
陈:老龚你动手吧。
我们在打井工地干了一会儿活,回来后管勤不见踪影了。我们并不吃惊,只是相互嘟囔几句:咋叫这小子跑掉了呢?但每个人心里都透明,该演的戏是演过了。这戏既是演给自己看的,也备以后说给管教听。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现实。
·15·
第三部 御花园遥祭
四
这是个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日子。这一天收到了场部发放口粮的通知,这一天老龚病倒了,这一天陈涛被蛇咬。
老龚并不是一下子病倒的,他的身体是一天一天虚弱下去,光合作用和营养丰富的草没有阻拦住垮下去的步伐,到十日这天早晨他没爬起来。
本来我和老龚一起去场部运粮,老龚一病不起,陈涛就让我留下来照顾老龚,他说那十斤半(能领多少我们早就算得一清二楚)粮食他自己也背得回来。他到“御花园”后面储养蛇的地方卷了一条很粗的“蛇卷”系在腰上,就出发了。他说今天一定要赶回来,保证老龚当天能吃到药(粮食)。
上午天空晴朗,中午开始变阴,沼泽地上空低垂着浓黑的乌云,冷风一阵阵从“御花园”后面方向刮来,将窝棚刮得吱吱响。看情势下雨是不可免的,只希望能等到陈涛回来再下。但老天不从人愿,傍晚时分雨飘下来,不大,淅淅沥沥。我站在窝棚门口望着通向场部道路的蒙蒙雨帘,心急如焚。
老龚一整天都躺在铺上,时睡时醒。醒来时我便坐在他身旁说话。这时我不知怎么把他和崔老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一个是阅历丰富性格锐利的军人,一个是知识渊博性格怪僻的教书先生,可我从这不同中感受到相同的东西,那就是堂堂正正的人格以及柔软和善的悲悯之心。他们都把我当成一个晚辈,以各自的方式对我施以关照与体恤。
我终生都不会忘记崔老临走时对我说的那番肺腑之言,我也不会忘记老龚在吃草的时候把野菜剔出来留给我。想想这些我是既感动又内疚的,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我没能为崔老做些什么,如果我能对昏睡中的他悉心照料,那么孝子也就插不上手了,因此也就不容易骗取崔老的信任而得到所需要的东西,从而将崔老置于死地。在这里,老龚身患重病,我却什么都不能做。陈涛让我留下来照顾老龚,这谈不上的,面对虚脱的老龚我束手无策。陈涛说得对,眼下粮食就是治老龚的药。可我不能为老龚做一口饭,做一碗汤,只能一遍一遍让他喝水。
我动过为老龚杀条蛇吃的念头,就像当初我昏迷时陈涛做的那样,可思考再三,觉得这样是对老龚最大的亵渎和伤害,便放弃了。将全部希望转向陈涛即将背回来的口粮。
老龚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睡的时候十分的安静,如果不是见到胸脯还在起伏,你会误认为已经死过去了。醒来后话很多。平时他寡言少语,现在倒成了健谈之人。他把他的许多事告诉我,他的童年,他的第一次恋爱,他的婚姻,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他对社会人生的诸多见解。也许是受到他这种袒露心胸的感染,我也向他倾吐出我自己的心声。我着重谈了我和冯俐的关系,他是过来人,我希望他能向我提出一些建议。记得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对婚姻的失望情绪,说过向太监和和尚看齐的话。当时他持以否定态度。一个婚姻的失败者,却对婚姻仍心存企盼,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前几天从大场回来我只是轻描淡写说接受了一次外调。不知什么原因,我或多或少还是对陈涛有种戒备之心。趁陈涛不在,我将在大场外调人员逼迫我揭发冯俐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老龚。老龚听毕哼了一声,说这不奇怪的,什么叫各司其职?这就是嘛。庄稼人多打粮食是丰收,工人多造机器是成果,司法人员多抓人多判人也是他们的工作成绩。停会又叹了口气说:这是个好人蒙难的时代啊!老龚如此抨击社会的话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连我听了都有些心惊肉跳。我想老龚敢于出口一是说明他相信我不会告密,另外,大概那时他便清楚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他用不着担心阎王爷追究什么。当然也知道发感慨于事无补,后来就说到了一些具体问题。老龚问我冯俐判了几年刑,我告诉他是三年。老龚说得设法告诉她,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弱女子当不成思想者,要好自为之,平安度过刑期。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问题是我无法见到她啊。老龚又说怕只怕你的朋友是夏天生长的昆虫,过不了冬啊。我吓了一跳,问是什么意思。老龚说世界上有些生物无法适应冬天的寒冷,便在冬天来临时纷纷死去。有的可以越冬,像人、马、猪、狗都属这一类,还有一类是需要借助冬眠来度过冬季,像蛇、青蛙这一类就是。现在看来人也是需要进入冬眠的。我说你是说躲避政治气候的严冬?老龚点点头。说尽管不是人人都有所意识,而事实上劳改农场所有的犯人都已进入了冬眠状态,等待着春天到来后的苏醒。老龚的话使我半晌无语,他打了一个多么恰切的比方啊。他总是能从他掌握的生物学知识中领悟出人生的意义来。我只是担心他自己能否像他说的那样平安过冬。
陈涛是黑天后回到“御花园”的,他撞开窝棚的门,我和老龚都惊呆了。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分明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泥猴。快看看粮食湿没湿。听声音是陈涛,这时我们看见他扔在地上的一个水淋淋的大布包。我上前解布包,发现布包是他的衣裤,他是脱了衣裳包粮食防止被雨水浸湿。谢天谢地粮食没湿。陈涛长长地吁了口气,接着说出了那个让我们惊骇万分的消息:我叫蛇咬了我完了!陈涛说完便倒在地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时间惊惶失措,张着手不知怎样才好。老龚慢慢从铺上爬起,对我说:快弄盆水来给老陈擦擦身。我诺诺照办。擦身子的时候陈涛不时“我完了,我活不了了,我要死了”地叫唤,声音十分凄凉。我们也顾不上安慰,全力以赴给他擦身之后,把他抬上铺。这时老龚问他蛇咬了哪个部位,他说左脚背。老龚让我把灯端来,借着灯光我们在陈涛左脚背和脚脖子相连处找到了伤口。两颗“八”状的牙痕十分明显,淤着紫血。
原来事故发生在回“御花园”的途中,也就是在刚刚踏进沼泽地时,陈涛发现一条蛇在泥水中缓慢爬行,当时他犹豫了一下,意识中清楚此刻不是捉蛇的时候,但终是经不住诱惑,决定将其捉拿。他追蛇捕蛇时不慎滑倒在地,这时蛇瞅准时机咬了他一口,逃走了。当时天已快黑,雨还下着。返回场部就医已不可能,只好回到“御花园”。这就是陈涛被蛇咬的全过程。
你不能断定咬你的是有毒蛇。老龚说。
是毒蛇,长着一颗三角形头。陈涛说。
这不完全说明问题,长三角形头的蛇不见得都是有毒蛇。老龚说。
陈涛开始发烧了,浑身很烫,又冻得在被窝里打哆嗦,完全是中蛇毒的症状。对此老龚也不再怀疑。但我们没有对症下药,只能硬撑,我和老龚都清楚陈涛能不能过这一关,取决于他自己的生命力。
我完了,老周。陈涛用绝望的目光看着我:那天咱们还唱打回老家去,看来我回不去了,我要死在这儿啦。老陈,你别胡思乱想,不是所有中蛇毒的人都没救,关键是要有活下去的信心,精神是第一位的。我极力安慰他,我知道自己的话有多么苍白无力。
龚教授,平日里我对你不尊重,没大没小,这都怪我政治觉悟不高,我现在提前向你道个歉,否则我死了……你不会死的,老陈,你好好睡一觉,明早就会好的。老龚安慰地说。
我不要睡,我知道一睡就醒不过来了,我,我才二十七岁呀,我还戴着帽子,我还没结婚,呜呜……陈涛说着哭泣起来。
我和老龚都不知怎样安抚他,只是木木地看着他。
我知道,是我做了孽呀,我杀了那么多蛇,这是报应啊,呜呜,我发誓,只要别叫我死,以后就不再杀蛇了,呜呜。陈涛边哭边说,像对自己,又像对沼泽地里的蛇们,我怀疑他的神志已有些不清楚了。
这时老龚也有些支撑不住了,他本来就虚弱,加上刚才一番折腾,额头往下掉着大颗汗珠,身体也摇摇晃晃,我赶紧把他扶到铺上让他躺下。老龚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让我把油灯挂在他头上的墙上,他从枕边摸出一本书看起来。
陈涛渐渐安静下来,慢慢合上眼。
雨下大了,雨声很响。
陈涛又睁开眼,把头歪向老龚的铺,声音微弱地问道:龚教授,你说神经性蛇毒和血液性蛇毒哪样厉害呢?
我说:老龚讲过血液性蛇毒厉害。但你中的肯定不是这一种毒。
你有根据么?他问。
有,根据就是你现在还活着。我说。
陈涛将信将疑地盯着我,看得出我这句话很入他的耳。
这时老龚将目光从书本上移到陈涛脸上,问:老陈,你看见咬你的蛇么?
陈涛哭丧着脸说:看见了,要不是当时顾脚就能把它抓回来了。
老龚说:这本书里有各类蛇的照片,你看看有没有咬你的那一种?老龚说着将书递给我。我交到陈涛手里。陈涛就看起来,过会摇摇头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