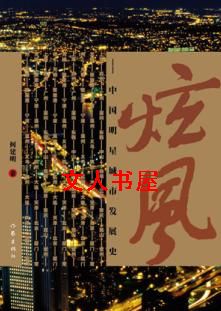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涛一如既往地动员我和他一块儿抓蛇、吃蛇,这不能说不是种诱惑,可我难以和他为伍。我并不同意老龚关于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的说法,不是因为这个才不抓蛇吃蛇,而是实实在在地怕蛇。如果让我在满世界无论是地上天上和水里所有生物中举出最惧怕的一种来,那就不是狮子,不是老虎和狼,不是鲨鱼鳄鱼,而是蛇。这种惧怕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记得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村里叔辈一伙人黑下在村外大水湾里洗澡,到半夜时都又累又饿,有人提议抓鱼烧了吃。他们就下湾抓了许多鳝鱼。烧上火堆,在火上烧鱼。边烧边吃,吃饱了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有人从水湾边路过,看见熄灭的火堆旁堆满了蛇骨,吓得飞跑回村,向村人诉说有人在湾边烧了蛇吃。立刻全村哗然。这话传到那伙叔辈们的耳朵里,他们承认这事是他们做的,但说吃的是鳝鱼。目睹的人咬钢嚼铁说看见的是蛇骨不是鱼骨。叔辈们这才惊惧起来,立刻奔到湾边去看,果然看见的是绿色的蛇骨。他们当时就吓蒙了,死人似的直挺挺不动,而后便一齐呕吐起来,那是翻江倒海样的大吐,吐出了五脏六腑吐出了苦胆水。回家后都大病一场。再看见他们个个都脱了形,蔫蔫的一点精神没有,像掉了魂。这件事当时被当着一桩奇行凶为在周围一带地面流传,可见我们那里的人对蛇是怎样一种恐惧心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也同样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不敢想象自己去靠近一条蛇,追逐一条蛇,捉拿一条蛇,更不敢想象能用手杀蛇和张口吃蛇。
每当进入沼泽地意识里一方面对蛇回避,另外也打着别的生物的主意。饿极了的人看见所有的东西都与食物相联系,考虑能不能吃。眼下的时节沼泽地里除了蛇其他的动物极少,一年生的动物大都是幼虫,如水湾里的小蝌蚪,蹦来蹦去的小蚂蚱、小蟑螂、小蟋蟀、小金钟儿,小油葫芦。在灾荒年里我家乡的人有吃青蛙、癞蛤蟆、蚂蚱和螳螂的,我没吃过,现在会吃,只是没有长大。也有人抓老鼠吃,我没吃过,现在也会吃。只是老鼠的穴很深,掘不出来,老鼠出洞时又总是跑得飞快(躲避蛇也躲避人),别说我身体虚弱,就是身强力壮也难能捉住它,于是鼠肉也吃不成。沼泽地上空有各种鸟类;它们或是成群结队飞来飞去觅食,或是独来独往,啼叫声给沼泽地带来一点活气。我对这些鸟有着强烈的兴趣,看着它们就有些馋涎欲滴,可我找不到网,找不到枪。没有网和枪,吃鸟肉是妄想。
在清水塘我们曾捉过雁。那是前面我曾提到那个叫曹先佩的犯人的绝招。曹是狩猎方面的专家,不仅会猎雁,还会捅马蜂窝。他说捉雁最好方法是智取:黑夜,成百上千只的雁群在麦地里栖息,有一只更雁在执勤。更雁多是失偶的“单身汉”,地位卑下,又被叫做雁奴。捉雁人朝警惕守护雁群的更雁划一根火柴,更雁见到火光立刻向同类发出危险信号,雁们从睡梦中惊醒来仓皇起飞,但不远飞,只在空中盘旋,发现没有真实“敌情”便又落回地面,继续睡觉。这时捉雁人再对着更雁划一根火柴,更雁不敢疏忽,又再次发出撤离信号,后面的过程和前面就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雁们不得安稳。于是便恼怒了,以为是更雁“谎报军情”,戏弄“全军”,便一齐去啄更雁,施以罚戒。更雁很委屈,要是它和人一样有思维准会大发牢骚,骂骂咧咧:操,你们睡觉,老子辛苦,反倒出力不讨好,啥世道啊。思维反映于行动便是更雁脱离了集体,独自飞去了。这时捉雁的机会便来到了,你可以大摇大摆走到雁群中去,抓到哪个算哪个。就像从地里拔萝卜似的。这几乎是发生在雁族中的“狼来了”的故事(可见许多事理不仅适应人类,也适应整个生物界)。用这种方法捉雁可称得上人类狩猎行为中的一绝,只可惜不适用于我们犯人,因为我们不能使用火光,那会被岗楼上的警卫发现,一旦被发现我们就成了被捉拿的雁了。我们惟有徒手捉雁,这办法同样奏效,但要历尽艰辛。在离更雁几百米的地方我们匍匐下身子,慢慢向雁爬去,那是极其缓慢的爬行,不能出一点声响。这时要是遇到水湾也绝对不能迂回,得老老实实从水湾里过去。离雁愈近,爬的速度愈缓慢,完全像一只蜗牛,一丝一毫向前挪动,十几米的距离竟需一个多时辰。这样直爬到雁的近前,雁也不会发现。它们将人当成了静止不动的物体,不加提防。捉雁的瞬间可以说惊心动魄,与爬行时的缓慢截然相反,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雁的长脖抓住,雁都来不及叫一声,就做了俘虏(我们戏谑地将捉雁叫捉俘虏)。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夜夜出来捉“俘虏”也天天晚上有雁肉吃。
这是清水塘留给我的最美好的回忆。在沼泽地里想着这些时我盼望着秋天和冬天早些到来,那时我会给老龚和陈涛露一手,我们就会吃到鲜美洁净的雁肉,那时的“御花园”就是真正的人间天堂。我不时抬头看看老龚,他在我左前方不远的地方,正一口一口地吃草。劳改农场是个没有“自我”的地方,任何行为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老龚吃草也不例外。他看好草地一般先在范围内巡察一番,看有没有蛇躲在草丛里,如果不放心,就用棍子搅动草丛——打草惊蛇。要是还见不到蛇,他就蹲下身子或坐在草地上,开始辨认各种草类混杂的草棵(我知道在这之前他已对照着书本对各种草类的可食性进行了研究)。沼泽地土质肥沃草也长得肥美,绿油油的,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老龚毕竟是人,他不像羊那样用嘴啃草,也不像羊那样打嘴便吃不加辨别。老龚吃草充分运用了人类的智慧,先用手掐下了可食草的嫩叶和草心,填进嘴里慢慢咀嚼。这是一个品味鉴别的过程,味觉对草的反应完全呈现在他的脸上:苦、淡、异、良好、尚可……我敢说这是我所见老龚表情最丰富多样的时刻。最后他将嚼过的草或咽下肚,或吐出来。看着老龚安静地吃草,我的心出奇的平静,以极其超然的态度看着眼前的一切,似乎觉得这是世界的一种惯常景象,不稀奇,用不着大惊小怪。
正如老龚说过的:我们正面临人类进化史的新纪元,人必须按原路返回到进化的初始。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吃草。现在想想老龚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是个大预言家。我知道在大饥饿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吃草,说人吃草并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诋毁“一片大好”的国家经济形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像老龚这般以最动物化的方式吃草。吃生草,坐在草地上吃草(这一点又与羊吃草很类似),吃不经过任何加工的草。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老龚便是先驱者,对昭示后人功不可没。在沼泽地里,饿得晕眩的人的思维竟出奇的活跃,不,不是活跃,是迷乱,真的是迷乱。我感觉自己全部的精神都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也无援无救。绝望像一口大铁锅罩在头顶上。而老龚却不乱方寸,仍不慌不忙地吃草。有时抬头看看我,有时招手将我唤到他身边。这种情况大多是他在草间发现一棵野菜,他总是把野菜给我。自从吃草,他就不吃野菜了,似乎他的返祖过程已超越人吃野菜的阶段,对野菜已不再有兴趣,不屑于再吃了。当然也可能出于对我的友好,帮助我这个顽冥不化的既不肯吃蛇又不肯吃草的俗人。不管怎样我对他都是很感激的,我愿意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
在近处看老龚吃草忽然就有一种不堪入目的感觉,从草的入口到咀嚼再到下咽这一连贯过程,以及他满嘴涂染草汁的绿色,都让人作呕让人心悸,我好像看到一只真正的老羊在吞食青草,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记得有次我直截了当向老龚提出问题: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那么草就属于人的食物链么?再说人毕竟已经进化到今天,能一厢情愿想退就退回去吗?老龚凝神一刻,说:我累了,咱到那块干地方坐一会儿吧。坐下后老龚两眼望天,问:老周你看看天上太阳在不在?我不知他为啥问出这个不搭界的问题,我说在,怎么会不在呢?老龚说你再闭上眼。我仍然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可还是照他说的做了,闭了眼。这时老龚说你现在能不能看见太阳?我说看不见。他又问:老周你说这时候太阳还在不在天上呢?我说这算什么问题?当然在天上。我睁开眼见老龚狡黠地笑了,露出一口绿牙,他说老弟你错了,错了。我说错了什么?他说当你看不见太阳时,太阳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我惊奇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违反物理学的常识哩。老龚说我是学物理的,后来教授学生的物理课,我会不懂得物理学的常识么?但是我告诉你,按照新的物理学学说:当你看不见某一物体时这物体便是不存在的,而且人们还能通过计算和实验对这一理论进行验证。我说真是不可思议。他说我举一个例子吧,把一只猫和一个扳机同置于一个钢箱内,扳机有少许放射物质,它在一小时之内可能有原子衰变也可能没有原子衰变,两者的概率相等。如果有原子衰变,扳机将杀死猫。因此,一小时之后,箱中的猫死去和活着的概率相等,或者说,是死猫的概率是二分之一,是活猫的概率也是二分之一。这意味着猫处于死活未卜的状态。现在你打开箱子,发现猫还活着,这样猫的状态的概率分布发生了突变,死猫的概率从二分之一变成0,活猫的概率从二分之一变成1。于是,由于你的观察,半死半活的猫变成了完全的活猫。由此看来,猫的死活决定于“人眼的一瞥”。这是一个叫薛定谔的物理学家提出的定律,叫“薛定谔猫”。它说明,不是事物的客观状态决定观察者的主观认识,而是相反,观察者的主观认识决定事物的客观状态。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一时像掉进了云里雾里,难以判断是非。过一会老龚说下去: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你用不着深究,我说这个就是想说明一点:常识这东西不够用也不可靠,人必须认同常识之外的事物并找到合理的根据。比如吃草,既然非吃不可为什么要把它想象得那么悲惨可怕?完全可以这么想:草和蔬菜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被人食用之前所有的蔬菜都被看成草,就说蕨菜,原先叫蕨草,当人开始吃了就改叫蕨菜。后来皇上吃了,就叫了贡菜,被当成菜中珍品。世上事情无定规。我说草没有营养。老龚说不对,植物不但有营养,而且营养极为丰富,甚至超过肉类。我说这是海外奇谈,不可能。老龚说可能不可能要由事实说话,拿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比较,以身体的大小论,世界上最庞大的动物是食草动物而不是食肉动物;以活的寿命论,世界上活得最久的还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我惊奇老龚怎么有这么多的古怪念头,而且听起来总是有理有据的,叫你无可辩驳。这时我想起陈涛曾提的“蛇能不能毒死自己”的问题,老龚一直没做回答,我也生出刁难他一下的念头,想想说:有的草有毒,人吃了会送命的,怎能辨别出有毒和无毒的草呢?老龚想想说:大多数的草都有一种草苦味儿,小部分的草没有味道,我不吃没味道的草,这样的草有毒的可能性最大。我问这是书本上说的吗?他说这个书本上没有,是他推断出来的结论。他说他坚信有毒的物质是无味的,无味才有欺骗性。要是毒药有异味,世界上就不会有毒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我无话可说,无法反驳他,也无法相信他。我觉得老龚太自负,走到吃草这一步仍以哲人自居,谈天说地,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怎么是这样的不可救药?
此刻,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老龚和陈涛已经成为沼泽地上的生物了,尽管有人吃蛇有人吃草有人吃野菜,我们与人类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属于北大荒里的这片沼泽地,是衍生于这沼泽地的新物种。
我不想说自己死过一回,不是那么回事。人生是一回,死也是一回,不再有多,大活人说死过一回其实就是昏过去一回,昏不等于死,但接近死。昏的过程是人在生死之间徘徊的过程,是生命的千钧一发,是命运的非此即彼,这状况大致相同于老龚所说“薛定谔猫”理论中的那只箱子里的猫。猫的生死决定于人眼的一瞥,而那天我的生死则决定于老龚和陈涛的一瞥。
他活过来了!我听出是陈涛的声音。很轻,像从天边飘过来的。也很悦耳,像出自笙管。
我看见了陈涛和老龚,同时产生了意念:我这是怎么啦?
陈涛告诉我,昨天打井我昏倒在工地上,是他和老龚把我抬回来的,昏迷了一天一夜。
老龚安慰地朝我笑笑,露出他的绿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