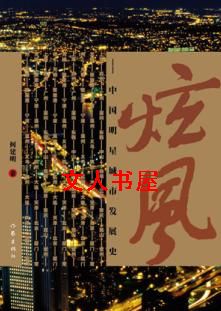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希望变成了失望。这里的一切就像随同火车从清水塘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一样肮脏的监房,一样高强度的劳动和一样少得可怜的食物……这种种的不变会使你觉得犯人的待遇是从上帝那里颁下来的,天南海北都得照章行事,不得走样儿。当然大同之下的小异还是感觉得出来的,比如气候,清水塘的四月已是春暖花开,而兴湖这里冰雪还没完全融化;再比如伙食,同样杂和面儿窝头清水塘的发黑(地瓜面为主),兴湖的发红(高粱面为主);还有管教干部的口音也明显不同,初听东北口音怪怪的,脆中带柔,唱曲儿似的,再严厉的训斥都让我们犯人感到很温和,很有人情味儿。仅凭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兴湖好,别的犯人也觉得兴湖好。如果此时让我们返回故里大家肯定是不情愿的。“月是故乡明”对我们犯人可不切实际。
但——我在兴湖农场只劳动了两个月又接到转场的命令。“收拾东西”,管教只说了这四个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我立刻反省自己(劳改最大的收获是知道遇事先反省自己),回顾到兴湖后的一言一行,看是否违反过场规,是否冒犯过管教,是否放松了改造。我像晒谷物样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情况与清水塘的农闲时节差不多,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和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比清水塘农场大得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面,见不到山岭,土地连着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这是句大实话,无论哪里的管教干部都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讲硬邦邦的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秋天打的粮食堆成山,我们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没“撑破肚子”一说。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褪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我们不是初到农场改造的雏儿,我们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清水塘农场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原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的。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做“小场”。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做“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管教干部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活口也实是情有可原。“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逃跑了一个,逃者是北京S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四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俩被劳改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做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过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户平常人家。确也不错,是由三个劳改犯人组合的特殊人家。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地由我们自己安排耕种,伙食也由我们自己料理,没有硬性作息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可以随便说话,大声说话,高兴了也可以唱上几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请示报告,够了,这就够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大场的犯人羡慕一千年。“御花园”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还穿着劳改服,我们会忘记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干啊,好好表现。满意中我告诫自己。人交了好运总希望与别人分享,到“御花园”的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信纸上不停笔地写: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个好。只可惜这里寄信困难,好消息家里人至少晚知道一个月。
陈涛是我们三个人的头儿,这是场方宣布的。只是让他负责却没明确职务。是“御花园”劳改组组长?还是“御花园”劳改小场场长?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长?不清楚。我刚来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不论大小是官就不宜直呼其名,笼统地喊他“头儿”难免有嘲讽意味儿,以年龄论叫他小陈既恰当又亲切,只是亲切有余恭敬不足了。瞧我们犯人遇事就是这么思前想后的没出息。后来我听龚教授叫他老陈,我也就叫他老陈。这么叫心里却不住地嘀咕:我新来乍到姑且不论,龚教授无论年龄和资历都比陈涛高,为何场方不用龚教授而用陈涛?如果陈涛是“内矛”也情有可原(前面说过劳改部门如有需犯人担当的差事大多派给刑事犯),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敌矛”。另一种可能是陈涛所犯错误(罪行)比较轻,因此获得场方信任。后来龚教授告诉我陈涛是从陕北老区考上S大的,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他家乡对革命做出的贡献说了一通话,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后毛主席一次也没回陕北”,这话是事实不假,但难免不叫人觉得话中有话,果然就有人指出这话是影射毛主席共产党忘本。本质一经点出,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他说那天他没把话说完,后面要说的是“革命老区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可这话还没出口就被别人打断了。但没人同意把他没出口的话狗尾续貂接到上面去,何况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杀不了反动的。
他的话没人听,他继续为自己申辩,后来问题就升了级:将他批捕劳教。他的问题就这样。
平心而论,陈涛本质上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人,他的心术不坏,处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负责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画脚不干活,可他和我们一样干;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可他也有不少叫人讨厌的地方,一是咋咋唬唬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领导身份自居动辄训人。这一点我来到“御花园”的当天就领教过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场部情况,问我听没听到政府为右派摘帽解教的消息。我们犯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摘帽解教”这个时代词语就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悬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热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梦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梦(而不是“做梦娶媳妇”),但梦境与现实又是那么遥远,两不相及。
我在清水塘的两年里,只听说有一个作家因表现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众多的右派犯人却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我们的刑期被无限制地延长着。想想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劳教犯,他们原本三年的教养期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创造了教养二十二年的“吉尼斯”纪录——这自是后话。“御花园”与“世”隔绝,信息不畅,所以我一到这里陈涛和龚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听这方面消息。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好消息。以前关于“中央政策放宽”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烟消云散,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突变,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还因此受到批评。这是流传在兴湖的普遍说法,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无保留地说出来,龚教授听了只是摇摇头,没再吭声。而陈涛听后脸刷地变成了死人样,两只透出绝望和愤怒的眼珠凶凶地盯着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权归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贵手那样。我被他盯得不知所措,我说老陈……你先闭嘴!陈涛把手一挥。随之将眼光转向在油灯下看书的龚教授,说老龚你出去一下。出去?龚教授抬眼看着陈涛。出去。陈涛口气很横。老陈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啥?龚教授满脸疑惑,不动。我心里也纳闷,不晓得陈涛耍的是啥威风。只听他说老龚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周谈话。他把“谈话”两字咬得很重,我不由一怔,不由想起流传在劳改犯人中间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教找谈话。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周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待。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山东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说好。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
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
主要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