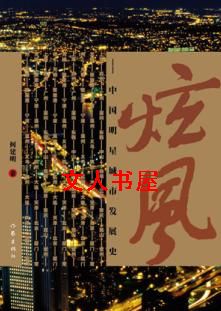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搓灭。说崔老是条汉子啊,有能力,只可惜是个国民党,要是一开始投身革命队伍,命运就完全改观了。我没吱声。他接着说他是有血债的,训练特务杀害革命者,血债累累哩。死有余辜啊。我还不吱声。我又能说什么呢?他指指黄瓜说你吃吧。为缓和一下气氛我拿起一条吃起来,他也拿起一条吃。边吃边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问来人探视过吗?我说到这儿还没有。他问到农场后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说有一位同学来过。他说在草庙子时我听说你有个未婚妻,是她吗?我说不是她。他问为什么她不来?和你一刀两断了?我说不是。他好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接着说保持关系不来看你,也太薄情寡义了。我知道只能如实说了。就把冯俐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现出颇惊讶的神情,说倒是个烈性女子呀,又何苦这样呢?也是太天真了。我知道他说的太天真指的是什么。我说她确实好钻牛角尖。又说我不能看着她往深渊里滑,就向场领导提出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领导没批准。他把吃剩的黄瓜把丢在地上,也像搓烟头那样用脚搓了。他说什么事都得有机会,要是我来后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会帮你办的。停停又问知道她离开帽儿山农场后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我说谢谢你了邹场长。后来邹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共过患难嘛,尽管他这话说的界限含混,但我还是连连称是。
9月15日:晚上梦见竹川,一块锄玉米。我见他情绪很高,满脸喜色,问他遇上什么好事。他说是好事,管教已经通知给减了刑,不久就要出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问为什么会给减刑,因为是班长吗?他说与当班长无关,只因表现得好。又说希望我像他一样好好表现,也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我受到鼓舞,说表现好就能减刑回家谁能不好好表现呢?醒了方知是梦。
——上述梦境是完全真实的,因记忆清楚又不犯忌,所以如实照记。光棍做梦娶媳妇,囚犯做梦释放回家,看来符合“梦是愿望之达成”原理。白天满脑子“表现”、“减刑”、“释放”、“回家”之类的念头转悠,夜里就梦想成真了。记这种梦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画饼充饥一样。我记下这个梦是因为由此我联想到竹川逃跑后的一些情况(竹川跑回家后的情况是从他儿子口中知道的),我发现梦想与现实竟然在竹川身上完全融合为一体,很奇异,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就生出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李戍孟的榜样在我也不会凭空生出这念头的,我想既然管教默许他写,那我也没问题,前有车后有辙嘛。我想通过写这篇小说缅怀好友竹川,同时也排解一下内心的苦闷,自从得知冯俐判刑又去向不明,心情一直压抑着,有时候觉得精神快要崩溃。写小说也算是一种精神转移。当然我也清楚,写这种作品是犯忌的,而我又领会李戍孟那天所说:如果今天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以后便无颜面对历史了。他说得极透彻的。像一个哲人。我觉得要写就现在写,可以找到一种写法,既真实又不犯忌,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尽管那时对这种可能性的状态尚不清楚……
9月20日:吴启都病情加重,小建国倾尽全力为他提供营养。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吴启都一家可以说陷入四面楚歌。吴本人的病情加重,医务室仍然不肯收留。也不见给他吃什么药。每天昏睡的时间多,似乎进入垂危状态。小建国由于天气渐凉,已不能经常下塘捉鸭子取蛋了,为继续给他爹提供营养,自做了弹弓射鸟,到河里抓鱼虾,捅马蜂窝取蜂蜜(有一次被马蜂蜇得满脸红包)。整天东奔西窜,腿一瘸一瘸地走路,看了让人心怜。齐韵琴的心情有点难以说清,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佟管教,从一开始大家便分析出佟可能对齐居心不良,他一反常态,不仅允许齐每周三次来管区探视,而且还将接待室作为齐落脚的地方。这种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行为与大家心目中的佟相去甚远,一直认为其中有“诈”。通常是逻辑如果正确,而认证逻辑的事实便会接踵而至。果然,佟的“诈”不久便显露出来,有人发现他在午饭后偷偷溜进接待室里,呆一阵子又鬼鬼祟祟地出来。至于在里面干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佟知齐知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佟觊觎齐是一厢情愿的,也不可能得手,因为齐吴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已被“历史”所证明,别人也许不知,而我知且深信不移,所以当别人议论的时候我断言这不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的看法,说不了解齐却了解佟,“佟大鸭子”这方面有无数次前科,可以说是流氓成性的。如依法而论他倒应该是在这里服刑改造的流氓犯。他这么一个人决不会放过一块到口的肉。当然这些都是推断,不是抓在手里的事实,我们也不可能抓到事实。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仅是心中对佟的谴责以及对吴一家的同情而已。
9月24日:邹场长告诉我冯俐新的服刑场所,我没料到会这样快,十分感谢他。
——情况是这样,午饭后坐在铺上休息,听到外面喊周文祥出来。我出去了,见邹站在门外。我朝他鞠一个躬,等着他说话。他说你女朋友的事我问到了,她被判了三年,转到黄河边上的“广原”劳改农场。我说谢谢你邹场长。他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写信与她联系。我说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在清水塘的这一年我给她写了许多信,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和我建立联系。不管怎么说,知道了她的去处心里踏实多了。也真的很感谢邹。由邹我想到一句“明人不做暗事”的成语,邹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一个犯人谈私事,高腔大嗓的毫无顾忌。邹可谓是个不做暗事的“明人”,而在草庙子监舍里当“暗人”时,他高超的“演出”瞒过了包括崔老将军在内的所有人。可怜巴巴说哭便哭,像个鼻涕虫。就是说我无法将“明人”邹与从前的“暗人”孝子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只能将其分割开。我鄙夷从前的那个孝子陈(那时他说姓陈),感谢今天这个场长邹。
9月25日:给冯俐写信。晚上说了梦话,受到管教的批评。决心痛改前非。
——上述记录虽是两码事,却有内在联系,先说写信。以前曾托齐韵琴给冯俐捎去几封信,都没得回音。这次知道了冯俐的服刑新址,对建立联系重新燃起了希望。信写得很短,半行不到:见字如面吾好望复切切切。虽连着写了好几个切字,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只当是投石问路吧。做梦显然与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有关,我梦见了冯俐,地点在一根绳,隔着半截石墙谈了不少话。至于是否说话出声,自己自然是不清楚的。说梦话挨批这事听起来犹同天方夜谭,有句话叫“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按说做梦说梦话也不应在管制之例。当然这只是常理,而对我们犯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事。并不是说管教苛刻,而是说我们的身份特殊,倘若不加以限制,干活累了都一齐去蹲了茅坑,心情不好时都借说梦话发泄,那怎么可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将听到别人的梦话作为向管教报告的内容,梦话不受理智的约束,常常会暴露出内心的隐秘。管教们认识到内中的价值。只要有人报告,便顺藤摸瓜进行查询。在清水塘曾出现过有人梦里咒骂管教的事,尽管本人指天指地地发誓予以否认,仍然受到了严厉惩处。这就说到了我自己由梦话招惹出的事端,后来才知道举报者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和我睡邻铺的强奸犯,只因抵制他的性骚扰,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与我谈话的是佟管教,佟盯着我的眼光俨然透出我是个犯了新罪的人。好处是他并不拐弯抹角,张口便说有人听到我污蔑劳改制度的言论。已经记录在案,现在要看看我的认罪态度。那一刻我还不晓得祸从梦来,便否认有此类言论。佟仍然是胡同赶驴直来直去,说他提示我一下,犯罪的时间不是白天是黑下。我说昨晚学习我没发言,一熄灯就睡了。佟接着问我做梦了没有。说到这儿我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做梦的事大概会有,我这人一向爱做梦。佟说那就交待一下做了什么梦。我做出想的模样,实际上却在思索要不要把梦和盘托出。思索的结果是不允许佟破坏那个留下美好记忆的梦。我说报告佟队长,我梦见自己回家了。佟管教追问:回家都干了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回家我妈为我包饺子吃。我饱餐一顿,还和我爹谈了不少话。佟说交待谈话内容。我说报告佟队长,主要是向我爹报告在这里的改造成果。佟问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说报告佟队长这个记不起来了。佟抬高声音说你不老实,自己做过的事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佟有意无意混淆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而我又不敢明确指出,只有不吭声。佟仍穷追不舍非要我交待出在梦里说的对抗劳改制度的话。还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是耳朵不是眼),想蒙混过去是不成的。再往下我硬是给他来个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佟大概也觉得再追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把我训了一顿。说句以后要好好端正改造态度,惟有这样才有出路。我说是佟队长。这“是佟队长”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决心痛改前非”了。
9月26日:开始写小说。
——这一天想了半天也不知该怎样记。小说是在大事记本子的后面写,起的题目叫《回家》。从晚饭后写到晚点名前,写了两页纸,看看不满意,临睡觉前我悄悄对李戍孟说很费劲,看来我不是写小说的料。李戍孟鼓励说别灰心,坚持往下写。我把写好的那页撕了,想重新开个头。
9月27日:今天公检法来人宣布将三名顽固反革命分子改判为死刑,并在老地方执行。
——也许是惯例,每逢重大节日前夕要处决一批犯人。死犯早晚要死,选在一个有意义时刻执行也无可厚非。据老犯人讲,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