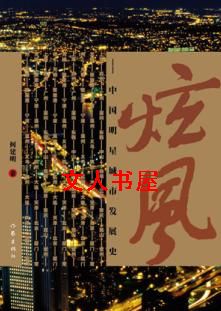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驰的。我说你在这劳改农场能发现到美吗?他说当然能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我想讽刺他几句,问他在管教的面孔上在警卫的刺刀尖上在高墙的电网上发现了哪样的美。但话没有出口。也许就是在井底下张撰与我大谈美的无所不在的这一刻,我心里开始产生出对艺术人的一种成见。我觉得他们属于情感畸形的一类人。或者进一步说都是些精神有毛病的人。我知道和张撰再说也白搭,就闭口。张撰却继续大谈他的美。他问我听没听说“东宫”里面有五妃子的事。我说听说了。他说既然是王子看中的女子一定是绝代佳人,你看,这不是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么?我说对,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他说你同意了?我说我同意,太同意了。
后来想想这一天我好像犯了邪,锲而不舍地寻找与高干斗争的同盟者,我几乎游说了班里所有的右派犯人,但只有一两个人说可以考虑。其余的人都表示不想惹是生非。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张来场较晚(大约是十月中旬),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S大历史系助教,平日观察,对谁都很谦恭,属大学里人们司空见惯了的那种好好先生。最后一个找张也属偶然。我俩快收工时才一起下到井里,本来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想再对他游说,可后来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又说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倒是很爽直,说这事他不想参与,因为劳改当局最忌讳犯人之间的这类串联活动,在他们看来串联与暴乱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发现就重重的处理。他说他的刑期是三年,一咬牙就过去了,不想再无事生非,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是他的最大心愿。听他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前面我所以说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是因为他后来的表现并非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不想再无事生非”,而是惹是生非,且矛头对准的是他的同类。其卑劣比之高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2月12日:终于得到冯俐的消息。喜乎?悲乎?
——冯俐的消息姗姗来迟。世上的事有时的确很奇异,人穷了,穷上穷,人富了,富上富。这是比如。我说的是冯俐要么消息全无,要么同时有多种渠道传来。先是早晨郝管教告诉我他已经打听到,劳教农场妇女队有个叫冯俐的大学生。接着是中午吴启都接见了来探视的妻子孩子后急匆匆找到我,告诉我他妻子说曾和K大女学生冯俐同在妇女队。因当时正是出工时候,不能多谈。傍晚收工回营,又碰上来维修水塔的李德志(水塔在夏季遭了一次雷击,当时未见明显破坏,后来开始渗水),李德志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周文祥我告诉你咱校的冯俐在东宫。我冷冷地说知道了。这么说是不想领他的情,我是很生他的气的。距离我的托付已经三四个月了,本来他能早些带给我消息(教养犯人星期天可以请假外出,何况他还是个很有自由度的技术员)。可他没当回事,今天是拾草打兔子当捎带把消息告诉了我。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都不会忘。虽然消息来得确实晚,可毕竟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情波动,夜里我用被蒙着头,阻隔了狱灯的光线后我流下了泪,我不知道这泪是出自喜还是出自悲。
12月17日:冯俐。
——离一九五九年元旦愈来愈近,雪不间断地下。雪并没有阻止我们的施工,每天都重演着“大雪满锨镐”。而我的心每天都被冯俐所占据。消息令我振奋,但没有使我满足,我急于知道她的现状,更迫切想见到她。在工地作业时我总是占据可以望向“东宫”的位置,“东宫”永远在我的视线中。帽儿山已被白雪覆盖,与白茫茫的大地连为一体,“东宫”变成了“白宫”,远远望去犹如帽檐上方的一颗白花结。相距不过三四里路,可以说近在咫尺,但在我的意识中却是万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头脑里跳出这个句子。又忽然感到骇怕。骇怕这句子不仅是我和冯俐现状的写照,而且是一种宿命的预示。
·8·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三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
——我没有料到李德志会来探视我。劳教犯探视劳改犯没有这种先例。他来了我很高兴,不仅带来了同学情谊,更给我带来了希望。我想如果李德志有这样的自由度,那么冯俐也能够来探视我。|Qī…shu…ωang|这希望使我不计前嫌,对李德志表现出友好。李德志前后两次来这里施工,和管教们很熟,因此管教对他表现出信任和照顾,让他到监舍直接找我。我和他坐在新增的一个铺位上说话,可以不受干扰。有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劳改营里的李德志与校舍里的李德志已变得相去甚远,但最本质的东西要变也难。李德志又再次向我道歉,说这次他是来戴罪立功的。详细谈谈冯俐的情况。他说他是通过内线关系才知道冯俐的现状。因发生了几起男犯与女犯的乱搞事件,场方对这方面控制得很严。男犯人未经批准进入妇女队营区可视为越狱行为,格杀勿论。他说从他掌握的情况冯俐很令人担忧,须赶紧告诉我,以采取相应对策。李德志这番话立刻使我紧张起来,我让他如实告诉究竟出了什么事。李德志说冯俐是九月份到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劳教农场就是劳教农场,不是学校,到这里来的人必须按这里的条文行事,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一样。可冯俐不懂这一点,或者说不是不懂,是不愿意按这个去做。她对管教说她的案子是错的,她没有罪。管教说你的案子不是劳教农场判的,只要到了这里就是犯人,犯人就得在这里好好改造自己。农场不管你的案子只管你的改造。不能说管教说的不在理,赶猪的和杀猪的各司其职。冯俐也认可了这个道理,说她可以按照农场的要求去做,无论是劳动还是改造。但在这之前必须对她的一个问题进行澄清。管教问澄清什么问题。她就把K大中文系党总支以她的名义骗取《大地》稿件作为罪证的事实说了。管教说这是学校党组织的做法,对与不对劳改单位没有义务澄清。管教这么说也同样无可厚非,如果冯俐明智,应到此为止。可不是这样,她钻了牛角尖。向管教反复陈述她自认为正确无误的道理。她说她并不要求农场当局复审她的案子,她知道这办不到。她只要求农场领导对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哪怕仅仅从道德角度有一个说法。管教说这不可以,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应保持一致。冯俐问也包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一致?管教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冯俐又问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放到你的头上,你们也同样会这么做?管教说是的。冯俐说我明白了。管教问你明白了什么?冯俐说我明白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当时管教对她的话只做一般性理解,没料到从此以后冯俐再不与她搭一句腔。哪怕是向她发出指令,她也是装聋作哑。一个犯人敢如此与管教对抗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关她的禁闭。关完了她还是老样子,就再关。找另外的管教和她谈话,她说要谈可以,前提是必须对那个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进行澄清。她说她也不要求公开澄清,只要当着她个人的面表明一下态度就成。她说还可以为管教的态度保密。如能这样,今后她就照农场的要求去做。事实上任何人都能看出冯俐的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幼稚可笑的。没有哪一个管教会“牺牲”原则与她妥协。况且管教与犯人之间压根儿就不存在妥协这一说。一段时间里冯俐基本上是在小号里度过。偶尔在小号之外也不积极劳动,不认真改造。她沉默不语,完全以一个“自由人”的姿态行事,想干就干想歇就歇。这种我行我素的“大小姐做派”实际上就是破罐子破摔。其结果自然是到摔碎为止。听了李德志所说冯俐的现状,一股冷汗从我的脊背上流了下来,我骇怕极了,也担心极了。这就是冯俐。我太了解冯俐了,她的性格是绵里藏针,柔弱其外,锋利其内。而更要命的是不思变通的认死理。须知“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过大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全部的信念集中为一点:赶紧拯救冯俐,拯救冯俐……这是当务之急……
元月31日:今天过小年。休息一天。改善生活。
——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得知冯俐处于危急之中就是。别的都不在话下了,什么过节,什么吃炖猪肉和白面饽饽,什么他妈的高干捣蛋和什么他妈的“联合阵线”,这些统统丢到脑后去了。埋怨冯俐是无济于事的,说她失去理智也好,说她不自量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也好,都没半点用处。关键是赶紧制止,对她这种“自杀性行为”进行制止,让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让她悬崖勒马。最直接的方法是能够见她一面,当面向她陈说利害。只是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办到。我没有探视她的自由,一定要见,只有不顾一切,冒“格杀勿论”的危险撞进“东宫”。细想想这样做也正如冯俐的所作所为不足取。我又想到给她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信里。但存在着一个传递问题。正常邮寄要交管教检查,这样的信很难写,要写也是“一定要好好改造一定要遵守场规一定要服从管教”这一套。这一套在劳改农场是老和尚念经不新鲜,对任何人都没用处。那就请人把信带给她。我首先想到吴启都。我私下找了他,问他老婆什么时候再来清水塘探视。吴启都说本来今天要来的,可不知为何没来,正担心着。我说来了请她给冯俐带封信。吴启都说你得提前把信给我,探视之前带在身上,否则来不及。我说我立马就写。按说这一天的大事记应落一笔“今天给冯俐写信”,没写自是因为怕犯忌。
2月3日:今天继续打井。我再次听到从帽儿山方向传来的歌声。高冲关心我的改造。
——元旦后不久二大队打的几口井陆续竣工,水很旺,水质也很好。正要选新址另打却停了下来。原因是其他中队要求进行轮换,修渠艰苦且不见成效,也想打井。场部考虑到二大队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轮换使熟手都变成了生手,非明智之举,于是决定仍各干各的。二中队的人高兴得很。我的高兴比其他人更多几分,因为新址的战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离冯俐所在的妇女队近了许多。白白的帽儿山比先前大了许多,胖胖的(形容山胖一定是受了韩复渠那两句描绘雪落在狗身上而使原貌改观的诗的启发: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同时肿胖的还有“东宫”。我问高冲到“东宫”有多少距离,高冲眯着眼向前望望说二里多路吧。我说有这么近吗?高冲说是的。看我一直向“东宫”凝望,高冲朝我挤挤眼说是不是对“东宫”里头的妃子们动了心思?可别异想天开啊,妃子只有皇帝老儿才动得。我的眼前一下子模糊起来,天地间“肿”在了一起。这瞬间我耳畔又响起那首“西波涅”优美感伤的旋律,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为了证实我问高冲可否听见有什么声音,他说除了风声什么也没听见。我又问若有人在山半坡唱歌这里能不能听见,他说听见不成问题。一定是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引起他的注意,他说老周你今天是怎么啦?这时只听新来的黄管教一声吼:你俩在那儿搞什么小动作?!你真得承认黄管教眼尖,我和高冲说话的时候并没停下干活,所谓的“小动作”不过是嘴唇的翕动而已,却也没逃过他的眼睛。我们一度为黄管教来替代佟管教而庆幸(佟管教元旦前打猎摔坏了腿,从场部宣传处抽来黄暂时顶替),以为任何一个新来的管教都会比佟管教好。事实就像我们老家的一句不雅的俗语:爷俩比鸡巴,一个繲样。我们庆幸得有些早。
2月4日:气温骤然下降,许多人出现冻伤。我的冻处在左耳。
——早晨离开营区时并没觉出怎么冷,走到半途就觉出有些不对头,手、脸、耳朵等身体暴露的部位像有把刀子在割,再过一会刀子就伸进衣服里面了。这时候就意识到今天的不同寻常,如早知道这样,临出门就会多穿衣裳。关于犯人的家当尽管口头溜说的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可衣裳总还是有几件的,只不过平常舍不得拿出来穿罢了,现在后悔也晚了。为了抵抗寒冷,到工地后大家便拼命干活,新井已挖进两米多深了,里面像个暖房。可每次只能下去两个人,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竹川班长是东北人,抗冻,也有防冻的经验,他说人身上最抗冻的地方是脸,脸不要管它(有人打趣说这叫不要脸),要管好的是手和脚。比较起来,脚的防冻好解决,人动防冻。从井里挖出来的生土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