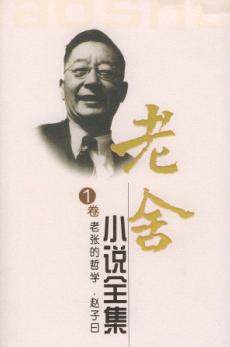戏梦长安-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韩文殊记得灵鸢曾说过,之所以叫她公子,全是因为怕自己时常改口,若是有一日没换过来,叫错了称号,惹来大祸,韩府上上下下几十人都躲不过去。韩文殊觉得这个丫鬟都比过去的她聪明,过去的韩文殊存了这么点儿小心思在雪梅亭,纯粹是自找苦吃,有一日露了馅,那可是欺君之罪。
“都处理干净了?记住连灰都给我洒在郊外的乱葬岗,不许留下一丝痕迹!”韩文殊严命。
灵鸢郑重应了一声,正要退下,韩文殊却又想起了什么,叫住她道:“回来时叫人搬个靶子,就安在这雪梅亭,本公子闲来无事想练练骑射。”
灵鸢虽心有疑问,却也不敢多说,喏喏应了便退了下去。
韩文殊边舞着剑,边回忆昨晚所遇之事。
昨晚从沛国公府出来的早,纪澄又一心扑在了锦芳阁的秦川姑娘身上,她回去也无事,便寻了一处酒馆要了几样小菜,不过这酒她可不敢喝了,保不齐喝醉了又捅出什么篓子。
然而这越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所能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多,恰巧一旁有说书的,韩文殊这一听可收获颇丰。
原来如今大秦先帝三十年前,以清君侧的名义诛杀奸宦赵高,秦二世胡亥不降,且为求苟且通奸叛国,先帝万般无奈之下派韩信带兵逼宫,最终夺位登基。
这段书原是讲大将军韩信内可平奸佞,外可镇匈奴的神武壮举。而那些关于先帝的事迹是韩文殊从字里行间中推断出来的,寻常百姓不敢妄议皇室,言语中只以“先帝”代称。然而这个文才武略知人善用的先帝,韩文殊却知晓了个大概。
韩文殊收剑站定,虽然照猫画虎耍了一通花枪,但也已经是大汗淋漓,她看了看时辰,随手抓起一块帛布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取了一旁的狐裘斗篷披在身后,便匆匆出门去了。
长安城西郊,一个飒爽身影策马扬鞭绝尘而来,韩文殊拨转马头遥遥望着远处掀起的一卷尘土。
年轻的公子身着黑衣大氅,金丝银线织就的腾云纹彰显着华贵之气。他勒马顿步,意气风发地看着韩文殊。
“你倒好兴致,如今可是突出长安城的囚笼了?”韩文殊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含笑调侃道。
纪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这一身浮夸的衣饰妆扮,撇了撇嘴道:“还不是家母的杰作?你还没看我那身银甲,里里外外十多个平安扣护身符。今早圣旨一下来,府里都闹翻天了,哭哭啼啼一直送我到出城,为着这个我都没敢走北路,不然撞上陛下迎冬祭祀的人马,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笑话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走你是没什么,纪夫人可要夜夜牵肠挂肚,你又走得这么突然,眼看又到了年下,这事儿换谁家都不乐意,你也要多体谅体谅她。”韩文殊耐心劝道。
“子卿兄说的我都明白,不过我纪澄生为男儿,自然要提剑扬眉保家卫国,我平生最大心愿便是率兵北上杀退匈奴,提着胡狗的头颅祭奠我大秦数万将士的亡魂!”
纪澄说的慷慨激昂,韩文殊为他这番陈词所感染,心中也生了些凌云壮志,多余的嘱咐的话也不必说,只叫他安心北上,纪府这边她会多多关照。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纪府的随行车队这时也慢悠悠地赶了上来,纪澄无奈地望了望,看着韩文殊的眼神也有几分自嘲。
韩文殊见他如此,急忙拦口道:“可别发牢骚,你这车队里还有我韩家送去的年货,你要是偷懒在半路上给我扔了,看你回来我不收拾你!”
纪澄惊呼:“竟然一下就被你看穿了!”
“就你那点儿小心思。”韩文殊白了他一眼。
纪澄“嘿嘿”坏笑两声,“知我者,莫若子卿兄也。”
二人又玩笑了几句,随后韩文殊收起笑脸,蔼声叮嘱道:“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前路漫漫,一切小心。”
纪澄飞扬一笑,挥手告辞。
韩文殊远远望着马背上那个不是很强壮、却带着一股坚韧劲儿的背影,霎时对这个年轻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似是敬仰又像是有那么一点欣慰。
昨日大雪,今晨雪虽已停,但是天空中仍是一片阴霾,雾蒙蒙的让人感觉压抑。纪澄的车队渐渐淡出她的视线,韩文殊觉得身上有些寒意,独自呆立了一会,便掉转马头踢了两脚马腹朝城中行去。
大秦的冬祭往年都要举行到午后才会结束,皇帝往往也会就近宿于林光宫,此宫殿时位于甘泉山上,乃是秦二世在位时修建的离宫,因其地势高而天高气爽,所以历代皇帝皆在此避暑,每年仲夏的朝会也在此举行。
她身为公侯将军,若是整个祭祀大礼都不露面恐不妥,韩文殊正思量着要不要绕一圈北郊,她抬头望了望天,这个时辰皇帝应该正在赐宫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袄子。恰在这时,从长安城方向传来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待离近时她看清是自己银羽军中的士兵,那人在她面前勒马顿住,翻身便跳下来,大声禀报:“将军,刚才军中派人来报,执金吾的人和咱们打起来了。”
“他们巡逻他们的,怎么跑到咱们驻扎的军营去了?”韩文殊皱眉。
“就在刚刚,他们执金吾剿匪追到了咱们军营门口,自己没留神让那飞贼给跑了,执金吾的人要到军营中搜捕,语气有些不善,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赵将军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失手打死了一人,现在人家北军不干,赖着不走,非要赵将军以死谢罪。”那家仆将知道的尽数告知。
韩文殊面色越来越沉,还未等他说完,便拨转马头朝城北林光宫奔去。
韩文殊快马扬鞭,不到片刻便赶到了甘泉山脚下银羽军驻扎之地。银羽军乃是韩家麾下军队,虽扎营于长安城北郊,却不归南北两军编制。不过多年来,因三军所辖不同,银羽军与南北军相处虽算不上和睦友善,但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遥遥便望见军旗上大大的“韩”字,相比起前几日来过的那一次,今日整个军营都弥漫着一股压抑肃穆的气氛。韩文殊翻身从马上跳下,两旁巡守的士兵急忙上前相迎。
“人呢?”韩文殊声音冷澈如冰。
那两个士兵听闻她语中寒意皆是一抖,互相对视一眼,只能老老实实答道:“北军的人赖着不走,赵将军拉不下面子,正等在帅帐里负荆请罪呢。”
韩文殊冷冽地瞪了他二人一眼,随即一甩袍袖,朝帅帐而去。
执金吾乃是保卫长安城内治安的禁军,直属于北军管辖。穿越而来的这半个多月,每每与军营中将领议事,多少还是能听出来将士们对南北二军的不满,尤其是北军,因驻扎营地相距不远,皆是围绕在甘泉山附近,时有冲突,好在两军将领与主帅息事宁人,这些年来倒也相安无事。韩文殊心里犯愁,正是彼此看不对眼的时候,又出了人命,北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赵奕,要如何保他啊……
她一路直奔帅营,眼尖的士兵看到怒形于色的韩文殊,都是沉默不语免得自讨苦吃。帅帐的布帘被掀起,里面乌压压站了一众人,皆是银羽军麾下大将,见到韩文殊走进,都面色忧忡地看着她。正中昂首跪着一个体格彪悍身材魁梧的男子,虽然是背对着她而跪,韩文殊却一眼便认出那就是失手闯祸打死人的赵奕。
赵奕见身旁之人皆向身后移步,他便知主帅已到,便掉头跪向韩文殊。
“末将有罪,请韩将军责罚!”赵奕高声道。
此时韩文殊正在气头上,一个不怕死的年轻将领上前几步,拱一拱手,扬声为赵奕辩解道:“韩将军明鉴,今日之事,实不全怪赵将军!”
“是啊,北军这次是欺人太甚了!”
“北军得理不饶人,非叫咱们给他们一个说法,我呸,明明是他们先恶语伤人的!”
“先动起手来的也是他们!”
“韩将军明鉴!”
……
众将士你一言我一语,地上跪着的赵奕却始终灼灼地望着韩文殊。
“都住口!”一声清冽的呵斥声打断众人周围喧闹的议论声。韩文殊自进帐以来始终未发一言,但在场所有人都已看出她面色不善,皆知她怒极欲发 ,众人生怕她急怒之下重罚赵奕。
“说。”韩文殊睨着赵奕,薄唇中吐出这一个字。
赵奕深吸一口气,眼中有些愤愤,道:“今日一早,末将刚从四营练兵回来,就看见执金吾的人在军营围栏外鬼鬼祟祟,不过今日的围外巡逻与站岗值守轮班到三哥,末将也不好直接插手,便私下里与三哥说了这情况。”
说完他斜眼望向左手边一个年纪稍长,有些精瘦的银甲将士,那将士乃是韩文殊麾下一员大将,名叫许志臻,只见他朝韩文殊肯定地颔首,道:“赵奕所言不差,末将也派人去巡查了一圈,执金吾的人确是在离咱们不远的地方扎了个营,末将亲自去询问了一番,为首那人说是追查匪贼,字里行间中暗指咱们银羽军里进了贼——”
许志臻说到后面语气有些梗塞,似有难言之隐,赵奕便接过话头,拦口道:“三哥你说话客气,我可没你这么好脾气!他执金吾就是无事生非,找咱们银羽军的麻烦,韩将军您没听见他们那话说得多难听,那就是指名道姓地骂咱们领着朝廷的俸禄却一无是处连进了贼都不知道,最后连‘私藏贼寇’这样的词都用出来了,您说这事谁听了不蹿火!而且他还、他还说——”
“赵奕,别说了!”许志臻见他险些要脱口而出,忙喝住他的话。
赵奕斜目看到他投射而来的眼色,长叹一声泄了气。
韩文殊见他二人欲言又止,轩眉一挑,寒声询问:“他们还说了什么?”
“先不说这个,总之他们言语挑衅,一个没搂住,赵奕一拳打死他们那一个巡捕。”许志臻愁眉不展道。
韩文殊面沉如水,以他二人的说辞听来,执金吾并未硬闯,而是己方前去探询时两方发生口角,最终大打出手以致误伤。韩文殊心一沉,怒其不争,低声问道:“谁先动得手?”
“当时双方都有争吵,场面太乱,根本没看清……”许志臻实话实说。
这时,一身着铁甲的中年男子步入,身后跟着几个大摇大摆的巡捕,只听他们扬声问责:“管事的既然来了,为何又要躲起来训话,把咱们冤死的兄弟晾在一旁不管,韩将军真当我们北军是吃素的啊!”
韩文殊心中冷笑,这些人哪像是刚死了同伴,一点受害者的样子都没有,一脸阴险得意,分明是蓄意制造这场事故,成心陷害她银羽军。这其中盘根错节她还不甚明了,但是北军的恶意却已显而易见。
韩文殊冷眼瞧着,因她官职仅次于丞相,便未先开口。
“下官北军中尉左丞魏肃,见过韩将军。”那人弯腰躬身态度傲慢地行了一礼。
“魏左丞的来意本将军已经知晓了。”韩文殊面色铁青。
“那韩将军打算如何处置?”说着他眼角瞟向一旁跪着的赵奕,眼中阴毒的邪光一闪而过。
韩文殊面色阴沉,公事公办道:“派人将尸首送到京兆尹,将赵奕……”
说着顿了顿,微微侧首看向赵奕,随即沉声道:“收押天牢,听后处理。”
☆、面圣
林光宫。
嬴珩从长生殿行完祭神大典,便回到寝宫。然而他却一反常态,面无表情地对窗而坐,丝毫没有要翻动桌上奏折的意思。
一个年纪尚轻的寺人从门外闪进,因为动作很轻,并没有吵动嬴珩。陈顺朝那寺人使了个眼色,随后悄无声息地告退。
每每到林光宫,嬴珩总会想起曾经在此处饮了一大壶桂花酒,肚子都喝胀了也没有一丁点醉意,对饮之人却已经酩酊大醉,倒在桌上一动不动了。
嬴珩会想尽办法让她清醒,招数千奇百怪,总之她那时只要清醒着就挺有意思。而现在,他倒是希望她安安静静地睡下,没人打扰,也只有她睡着,他才敢肆无忌惮地望着她。
这林光宫乃是他二人幽会之地。自从三年前那件事发生后,嬴珩便不敢再召她到林光宫,即便是仲夏,他也极少离宫来此避暑,他心中踌躇着今年是不是应该试探试探,他最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韩文殊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哀恸却又只能憋在心里的女子……他就这样对着窗外的雪梅发呆,左右拿捏不定。
雪梅,雪梅。雪梅亭的名字也是他起的……
“陛下,江辙来了。”陈顺低声说道。
寝殿的一片宁静被打断,嬴珩皱了皱眉,从思绪中被拉回。
“让他进来。”嬴珩将托腮的手放下,坐直身体,神经严肃仿佛在等待宣判。
随后从门外进来一个青衫男子,约莫三十多岁,黑黝的皮肤满是风霜。他站定后从怀中取出一本奏折样的物件,递到嬴珩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