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别离开我-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对我说那句话时,忍不住滚下两行浑浊的眼泪。
这是我看见的第几次?第二次?第三次?我记不清楚了。但能记清楚的是,小的时候,我从没见过他流泪,即使在奶奶去世那天。
不过,我很快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后悔。
他吼完,立即上来抓住我肩膀说:“你真的太倔强了,就当真不能求求你哥嫂吗?爸实在不想看到你还要一个人在外面漂泊。”
他说话时,显得慌张,又似唯唯诺诺的样子。
连自己都没想到,刹那间,我再也控制不住了,仿佛心里最柔软的某个地方被他的话击中似的。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在哆嗦,咸咸的液体已经顺着脸颊流淌到嘴角——我哭了,因为觉得他可怜,真的很可怜——我可怜的父亲。
他已经很老了。
白头翁似的头发,跟他五十刚出头的年龄,显得极不对称。脸色苍白,嘴唇黑紫,颧骨突起,皱纹起伏,嶙峋的手指关节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瘦小的身体裹在宽大的羽绒服里,是那么不伦不类。早上刚刮尽胡须的地方,还留着几道新鲜的血痕——
此刻,他正一手抓着我的肩膀,一手捂着自己的胃子——或许,那里现在很疼。或许,他感觉最疼的地方并不是胃子。
忽然间,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捂着胃子的手松开了,伸向我,用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手,替我擦拭眼泪。
他哆嗦着手指,似乎很艰难。
“三儿,爸对不起你啊!”
擦吧,你也该替儿子擦回眼泪了,就算把欠着的补上吧!知道吗?那时,你就该来,来替我擦去眼泪,因为我总是想——要是爸爸在,一切就好了。
我甚至做过梦,如果他一直在我身边,如果还有人骂我是杂种,那么我一定会勇敢地冲上去,小拳头将不停地落在他的身上,最后把他撕了,像疯子一样。
可这始终是一个白日梦,就如现在他要为我擦去眼泪,结果却越擦越多。
“他爸,你们站门口干吗呢?进屋说啊。”背后传来那女人的声音。
我们都没说话。
很快,我听到身后的铁门“咣当”一下,猛地被关上了。
我立即推开父亲放在我肩膀上的手,转身,然后对着那道铁门,使劲平生最大的气力,一脚踹了上去。
我想,所有人都震惊了,包括我,包括整个房子——
我的脚裸大概崴了,有些疼。但并不罢休。
父亲上来,一把拉住我:“三儿,你别这样,别这样——”
然后,他拖着我要离开。
可是,他终究老了,拉不住我。我还是挣脱了,站在门口,拼命地踢打着那道门。我已经准备好,准备好等那女人出来叫骂——来吧,我会回敬你最恶毒的咒骂!
然而,里面出奇地安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恨她,恨第一次来这里时,她说我是小破孩子,说让我去喝西北风,恨她以前对我的种种辱骂,再也伪装不下去了,尤其在听到那女人猛地关上门之后。除了这,我还始终牢记她那张冷漠的笑脸,特别是在奶奶去世的那天。
那天,我正在村小的土墙教室里上课。
四周的墙壁都快掉渣子,上课时,会突然落下一块,幸运的,砸在脚下,不幸运的,直接砸在头上或背上。前后各两扇窗户,都是没玻璃的,下课或放学,我通常直接从那里出教室。学生并不多,十来个吧,名字全忘了,都坐在破旧不堪的长凳上,共用一张缺腿的课桌。
我习惯一个人蹲在最靠边的地方,不是因为没凳子,而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坐凳子。即使从家里带来,也都要被他们抢了去。担心奶奶知道后,又要骂我胆小无用,于是也怕敢跟她提。所以,上课时,我总蹲在那里,空着双手,听老师讲。蹲累了,就直接跪着,把屁股放在脚后跟上。
老师是个女的,姓蒯,叫蒯玉梅,我至今记得她。那时,整个村小只有她一个老师,什么都教,除了做人。
有一次,课上到一半,她让我们一起去帮着浇她家的菜园子。我当时听得清楚——大家一起去吧。所以,我立即把屁股从脚后跟上提起,很开心。哪知,她指着我说:“还蹲在那里,我没叫你。”
当时,我只是泄气,觉得很不公平。注意,我只说当时,而不说现在,现在的感受,读者大大一定非常明白,也明白我为什么到现在都能准确叫出她的名字。
一个人孤独地守着偌大一间破烂似的教室,真让人感觉害怕——我总要担心,房顶上那即将脱落的石灰块会突然砸下来。于是,我仰着头,专等它脱落的一瞬间,好及时躲避。
脖子僵硬时,我听到窗外小鸟在唧唧喳喳,“看到”狗子在路口摇尾巴等我,想到奶奶为我做的茄子蛋汤——
不知什么时候,我听到教室外面有人叫我。
停止仰望,我转过头看教室外,阳光里闪着一个身影:“是爱华吗?”
说真的,我以为他是神,太阳神。
我赶忙站起来,等他走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来不及等我回答,他立即又对我说:“快,你奶奶不行了,要看你最后一眼——”
那时虽小,但是我懂得“不行了”的意思。所以,坐在他自行车后面,听他“呼哧呼哧”的喘气时,我伤心地大哭起来,而且越哭越厉害,浑身抽搐,像打饱嗝一样。
自行车的轮子再快,也赶不上死神的脚步,奶奶终究没能见到我最后一眼。
后来,我就见到了奶奶在病床前跟我说过的父亲。那时,他刚从城里来,很年轻,总是很严肃的样子,同来的还有一个女人。
那几天,我整天戴着用黑布制成的丧服,按大人们的要求,一直跪在奶奶的灵床前。他们让我哭,我就号啕大哭,他们说歇歇再哭,我就低头小声抽泣。
我一直记得在灵床上的奶奶的脸,惨白惨白,安详沉睡——永远无法忘记,就如永远无法忘记后来看到的那张女人的笑脸。
下葬那天,我已经不会哭了。在一个已经挖好的泥坑前,我被一个陌生人死死地抓着两条胳膊,然后看着棺材被小心地放下去,再目无表情地看着父亲一锹一锹往坑里填泥土。
忽然间,我看到父亲带来的那个女人,正捂着嘴和她身旁的几个人在说笑。他们都是从城里来,衣着打扮和村里人区别很大。
我就一直看着他们,在身旁一些同村妇女伤心痛哭中。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高兴事儿,一直说,一直笑,直到我脚下的泥坑平了,身旁的哭声停了——
第四十六章 精灵
叫我感到奇怪的是,那天我狠蹬铁门时,整个世界为何那么安静?连父亲都震惊了,木瓜似的一动也不动。 我恍惚看到一个勇敢的自己,冲杀在抗日的战场上,进行着一个人的复仇式浴血奋战。哦,原来我也有勇气。
晚上,父亲和那女人在厨房里拌了几句嘴后,又来到我的房间,并且端来了一些饭食。
“三儿,吃饭吧。”他边说,边把手里的盘子小心地放在我的床头桌上。
“你拿走,我不饿。”
“别这样,三儿,算我求你,还是吃点吧。”他的语气明显是哀求。
我干脆把头捂在被子里,随他说去。很明显,他端来的饭食是乞讨来的。
随后,我听见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再听到关房门的声音。
夜里,我关了灯,把一对眼睛留在黑暗里,思考该尽早离开这里。
正想着,枕头底下的手机响了。
“你大爷的,谁啊?都几点了?有屁快放。”对着电话,我一阵喊。
“谁大爷?谁大爷?亲爱的,你吃火药了?”
其实,我向来接电话不鲁莽,一般都是很绅士地说:“喂,你好,请问——”但那天心情郁闷,烦躁不已。
小邵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有些乐,没等我回答,继续说:“这才几天啊,我都成你大爷了,哈哈——”
“我错了,应该叫你他娘的。说吧,他娘的,什么事儿?”
“你怎么开始骂人了?烦我了,是吧?
电话里,小邵像要吃我耳朵似的,使我突然意识到该收敛自己的坏脾气。
“我骂了吗?没啊。这不逗你乐嘛,哈哈——”我故意笑出声来。
“别装了!你以为几天不见,自己真变成没良心的黄鼠狼了?我告诉你,你要真成了没良心的黄鼠狼,我非咬死你不可。”
“哎呀,这还让不让人过年了,净咒我。”我想终止这话题。
“那你就告诉我,刚才怎么了?”
“没怎么啊?就是跟你开一玩笑啊。”
“还把我当小姑娘呢?记得吗?你早就承认,我是个女人。直接说吧,今天白天是不是遇到不开心事儿了?”
有些时候,你得承认,谎言会很快把你从尴尬中解救出来,而真话却不可能办到,因为我永远不愿意跟她提及任何关于家里的破事。
因此,我说:“是的,刚才跟家里人争执了下。”
“啊?难得回去一趟,干吗争执呢?”
“因为我想你了,就跟他们说要提前走,而他们根本不愿意。”
“哈哈——这么说来,错误还是可以原谅的嘛,”她笑着,很开心,“不过,你也跟我商量商量啊。”
“纪律中,好像没有这条吧?”
“对了,你不说,我倒要忘记了,纪律中有一条,好像是说至少两天要给我打一次电话的哦。”
“啊?”我真给忘了。
“说,被哪个小狐狸精给缠住了?”
她又来,呵呵——
“哦,这样啊,那你等等,我把电话给她,你直接问她吧。”我装着磨磨蹭蹭,把电话从耳朵上摘下来。
即便这样,小邵的尖叫声还是清晰地从听筒里传出来:“黄胜,你混蛋——”
接着,她又急了:“喂,喂,说话啊,黄胜,你这样欺负我,天理不容!天理不容,知道吗?”
“我哪儿敢啊,明摆着是你欺负我,硬把一个狐狸精往我房间里塞,然后再诬赖我窝藏。我不正找找看嘛,看看你是否真的对我这么好。我多好一人啊,规矩又老实,哪能受得了这等诬赖?”我笑着说。
“臭美吧,你。我不管,反正你以后绝对不能欺负我。你要真欺负我,我就——我就——”显然,她在思考。
“就怎样?”
“喀嚓——再喀嚓——”
“啥意思?”
“笨蛋,剪掉呗,让你一辈子后悔。”
我记得,去年快回家时,她就这么说过一次。
“你看你,都快成一女流氓了。”
“就女流氓,就女流氓就女流氓就女流氓流氓流氓流氓——”
“什么啊?”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说你是流氓呢,亲爱的,哈哈——”
我倒是惊喜地发现,她早就学会耍赖了。但我并不觉得厌烦,相反,我很喜欢,让我多了几分对她的怜惜。
“现在是夜里几点?”我问她。
“十一点多吧,差不多。”
“哦——”
“哦什么啊?”
“我想你了——”
“什么?”她装着没听见,但我已经能感觉到她的嘴正在咧开笑。
“我说,想你了!”我加大了分贝。
“没听见,没听见,再来一遍,快,快点儿。”
“我说,我——想——你——了——”
“哈哈——哦,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亲爱的,我爱你。”
这时,父亲一下推开房间的门,伸过头来问:“三儿,怎么了?”
我赶紧用手捂紧手机,张口道:“没——没什么,好像是做梦了吧。”
等父亲疑惑地重新帮我带上房门走了,我立即对着电话埋怨道:“都怪你,害我半夜学鬼叫。”
“哈哈——刚才怎么了,亲爱的?”
“你准公公来查房,看看我们有没有乱来。”
“呵呵,去你的。你告诉他,他儿媳可不是个女流氓。”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煮着电话粥,直到它能烫着耳朵了。
某个时候,我们突然安静异常,气氛有些凝固。
她说:“亲爱的,你没憋坏吧?”
我说:“那你呢?憋坏了吗?”
她说:“我一直憋着,怪难受的。”
我说:“那赶紧去卫生间啊,要我把你当婴儿一样端着尿吗?”
她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混蛋啊?我可是好想好想你的啊!”
我说:“哪儿想?上面还是下面?”
她说:“这里想,就这里。”
我赶紧问:“哪里?在哪里?”
她赶紧说:“就这里,这里,你看,就这里。”
“我能看到个屁啊!你就折磨我吧。”我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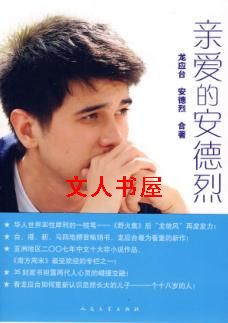


![[韩娱GD]我亲爱的小冤家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3/1392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