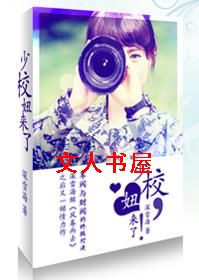花孔雀攻vs武力值爆表受-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雁随,你说句话。”
花雁随看着他:“本君昨天说喜欢你,你听见了吗?”
黎韶点点头。
花雁随上前一步,黎韶却后退了,那俨然不再亲昵的表情,让人无法再进一步。花雁随按着心口,其实,心一点儿也不疼,就觉得按着舒服,按得越进越舒服,估计抠出来摔地上更舒服:“黎韶,你都是在逢场作戏吗?”
“对不起。”
“就没有过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
黎韶摇头。
“不管以前那些原因是什么,本君不在意,只要和你就好。”
黎韶摇头,目光坚定:“对不起。我只是为了天罡九气才来的,没想到会成现在这样。再这么玩下去,都不好,你可以找个举案齐眉的花夫人白头偕老一辈子。对不起,雁随,若知道会成现在这样,我宁愿当初没有来花府。”
花雁随咬牙,半天吐出一句:“你对本君到底有没有一点情,即使一点点。”
黎韶摇了摇头。
花雁随覆在池边的阑干上,手紧紧抓住了阑干:“很好,本君也能了无牵挂。你走吧,不用还了。本君,不在乎!”
沉默,像刀。
望着氤氲的池中水气,花雁随的心一点一点浸下去,泡得透明,他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并非完全不在乎。黎韶,在花府冷静几天好不好,至少还是朋友。”
身后,沉默。
退一步是朋友,至少情分还在,也好。花雁随重复着:“黎韶,朋友,总还行吧?”
依旧无边的静默。
沉默,就是默许吧?或许黎韶也有一丝暧昧不清的眷恋,因为说不清而没有办法承认?若是如此,等待一些时日,他会有所心动的。氤氲的热气腾上来,花雁随的心暖了一些:“黎韶,本君就当你默许了。”
静无一音。
花雁随升腾起一丝希望,欣喜地回过头来。
身后,空空如也。
身后的天际不着一缕云彩。
天际与湖相接,漾漾着一湖深深的冷冷的湖水,没有一丝波澜。花雁随站在汤池边,呆呆地望着,只有无边的静寂,默默地回应他的目光。花雁随往前踏了一步,一头栽进水里。
许久,慢慢地浮了上来。一脸的水珠,怎么抹都不抹不完。
整个冬天,花雁随都在花洲温暖的锦席上躺着,缱绻了两个月。
每天都懒懒的。
明明笑着闹着的时候,都当真了。走的时候,比笑的时候还认真,冷冰冰,冰冰冷,连背影都没有留下。
侍女服侍时,那些珠宝也懒得戴了,反正一个人呆着一件白寝衣就够了。更主要的是,他一看见珠宝就来气,想到竟然有人只看重珠宝和所谓的宝气,却连自己这么活生生一个人都不在意,火冒三丈。
那股火埋在心里,烧得心都焦了。
想到黎韶那么坚定的摇头,那一点儿情分都不留的走了,又心里发酸嘴里发涩。
其实,没有情又何妨?
慢慢来,总可以的。你但凡有一点儿情,本君都可以每天浇点儿水施点儿肥,慢慢养成长情,本君有的是耐性。
抑或,做不了情眷做朋友也行。
大不了不要亲不要抱,每天泡泡茶,下下棋,也成。不是只到七气吗?还有两气,你也可以继续在倾心院里修炼啊!花府有的是独门独院,闲得发慌,本君不在乎那点儿地方。
奈何,那个人就这么头也不回的,走了。
珠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什么用。
覆在铺满锦被的大床上,花雁随叹了口气,安慰自己:冬日里,万物萧条,人所以容易气短容易感怀。等到春天、夏天,万物复苏,本君一定可以洒脱地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宝气什么武功,不在乎!
、人不痴情枉年少
【第十八章】
混混沌沌,到了二月初,暖风习习。花雁随只一件薄薄寝衣,斜卧在花洲的床上,微微出汗。花洲热气上蒸太过暖和,呆不住了,可他就是懒得挪地方。
懒懒的也不想做什么。
这天,裴老六过来问询事务。
吩咐完毕后,裴老六犹豫了一下,道:“花君,犬子子洲近日来对砂石很感兴趣,半月前就跟着胡老九跑了几天。胡老九说子洲虽然愚钝,腿很勤快凑合能使唤。我就想趁着这大好机会,干脆让他跟着胡老九历练历练,长长见识。”
怕是裴子洲自己的主意吧?
好端端的秀才不做,乱打什么算盘,花雁随淡淡地说:“历练是好事,你与胡老九决定就好。”
裴老六又说:“子洲想去新挖的瑠山看看,胡老九说瑠山产玉石,寻常人不得入内,得花君准了才行。我老来得子,平日里多加宠爱,宠得他性子倔强,执拗不过,特来问问花君。”
不对劲了。
胡老九一向有主意,裴老六也不是拎不清的人,裴子洲更不会打滚撒泼,怎么说着说着家事都缠上来了。本君自家的家事都理不清,你还敢来烦!
花雁随道:“老六,你知道,本君向来不太管底下的细事,但凡砂石矿产还得老九裁定才行。”
难得啊,裴老六一向老奸巨猾,今天竟然这么没眼色,见自己心情不好还敢不停叨叨,奇了。
裴老六果然还没走。
小心地捧出几块未雕琢的璞玉,道:“花君见多识广,不知这几块璧玉的成色如何。胡老九就给我这么几块,说是让子洲练练眼。”
这还要练眼?
花雁随将璧石放在手中,观了观色,略是抚摩过去:“成色中等偏上,子洲这是,喜好上了赌石?”
裴老六喜滋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洲还未婚娶,介绍了许多女子都看不上。前些时候,忽然喜欢上了一位女子,喜欢得不得了。四处搜罗璞玉,他想自己磨出一块送人——咳咳,人不痴情枉年少。”
真有雅兴。
不过裴老六你真不至于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吧,现如今长眼睛的都看出本君不爽、不爽、很不爽,你再敢这么兴高采烈,保不准本君见一对拆一对,你们就哭去吧!
花雁随腹诽,没做声。
裴老六继续陪着笑:“没开的璞玉不值钱,上次让胡老九弄了一马车石头,这是其中几块。但子洲都说成色不行,非要亲自到瑠山去看。我回去就告诉他,花君都说成色偏上,让他再别胡闹了,老老实实在家玩琴棋书画,别琢磨什么砂石玉石了。”
一马车石头,子洲都没相中一块?
花雁随豁然坐直了身体:“你那未来的儿媳妇是百司哪家的姑娘?难得子洲相中,本君该为他主婚才是!”
花雁随豁然坐直了身体:“你那未来的儿媳妇是百司哪家的姑娘?难得子洲相中,本君该为他主婚才是!”
裴老六大喜:“不是本地姑娘,前几日遇难被子洲救下的。”
花雁随皱眉:“你见过?”
“不曾,子洲性子倔,说是万事好了就迎娶上门,不消我们操心。哈,我这个父亲拗不过他,也懒得操心,不就是弄块玉石做信物么,应了就是。但据说那女子身子极虚弱,呀,要不能生养可不行!”
没见过,你都敢应下来当儿媳?
裴老六不是将就的人。
裴子洲这人,花雁随也很清楚。好几次布匹生意受挫,裴老六力挽狂澜,花雁随却看出有些东西就不是裴老六能想出来的,他没点破,也犯不着点破。龙生龙,凤生凤,裴子洲自小跟着裴老六,绝对不是迂腐秀才。
金屋藏娇。
子洲将女子藏在了瑠山脚下,藏得真够远。
极少出花府的花雁随查看了老黄历之后,精心部署,终于坐着花车摇到了瑠山脚下。
胡老九见了花雁随,吃惊得下巴差点掉一地,问清来意之后,瞬间释然,往树林中一指:“老伙计的儿子,我就让他在瑠山随意走动了。再者,瑠山虽产玉,也上乘,但实在是稀少,还不如原先那些砂矿制铁赚钱呢。”
花雁随沉思。
胡老九继续叨叨:“现在挖下去,水就多了,更少。我正寻思着要不要换座山,昨天子洲还说这瑠山留给他,我正要向花君请示呢。”
“子洲和那女子都在此处?”
胡老九一愣,咧嘴笑了:“可不是嘛,如胶似漆。我那些好事的手下还窥探过呢,可惜人家女子足不出户,没一个见着真相的,听说长得倾国倾城,把子洲迷得不像话,一天扎在竹楼里不出来。
花雁随那阵势。
比皇帝巡视还吓人,方圆百里是没人,惊得百鸟都扑哧哧乱飞。裴子洲自然闻讯早早站在竹楼门口迎接。
竹楼有三间小屋,中间是正堂,两侧是偏房。虽然极为简陋,外面有绿篱笆圈成了一个小园子,种花的种花,栽树的栽树,二三月树绿花红,很有些雅趣。
花雁随端坐在竹楼的正堂的正座之上,一言不发。
只是品茶。
裴子洲耐性也好,没水了添水,没茶味了添茶,丝毫没有懈怠。花雁随不愿多说话,他也很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不多时,整整三壶茶入肚,天都黑了,裴子洲起身致歉:“子洲不知花君爱茶,不曾备好茶。”
花雁随懒懒道:“无妨。”
裴子洲到底沉不住气,微笑着问:“不知花君来瑠山所为何事,子洲可有幸为花君分忧。”
“本君为子洲主婚来的,奈何至今不见新人来拜见。”
“主婚?她体弱多病经不得风寒。”
“连本君也见不得?”
“花君见谅。”
挡得滴水不漏,花雁随将裴子洲上下打量一番,眉宇间甚是清朗,无论说什么都含着笑,真不爽利。花雁随环视一圈:“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一月有余。”
“只羡鸳鸯不羡仙,不知子洲是怎么与他认识的。”
裴子洲答得文雅:“一见倾情,惜彼时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再见时她不幸落难,子洲得幸,方能一近芳泽……”
听了这话,花雁随豁然起身,二话没说一巴掌扇过去。
裴子洲端直被扇得倒退数步,左脸红色血印,嘴角流出血来,扶着桌子勉强站定,手指青筋暴露,半天才抬起头直视花雁随,眼中是愤怒。
“本君的人你也敢动!”花雁随冷冷地说。
“子洲愚钝还请花君明示。”
“他在哪里!”
、灯下黑
【第二十章】
裴子洲忍痛,慢慢直起腰来:“请恕子洲愚钝,不明所以。花君若觉得子洲有所隐藏,请尽管叫护卫搜查。”
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装!
花雁随二话没说大步走出正堂,一脚踹开了左偏房的大门:一个案子、纸墨笔砚、几本旧书,再无余物。
花雁随转身离开,一脚踹开了右偏房的大门。
一声尖叫。
一个赤裸的纤细背影。
花雁随呆了,愣在了原地,眼睛难以置信地分辨着,裴子洲迅速挡在花雁随前方:“花君,见谅,小林更衣之后,再来拜见花君。”
非礼勿视,狼狈退出。
哐当一声巨响,门关上了。
花雁随恍惚了一会儿,裴子洲无声地站在一旁。
缓过来后,花雁随正色地致歉:“子洲,方才本君误会了,多有冒犯,还请子洲见谅。”
“子洲思虑不周,给花君添麻烦了。”
很快,一女子款款前来。女子娥眉淡扫,面有红晕,款款施礼并致歉:“小林拜见不及,惊扰了花君。”
彬彬有礼,气氛尴尬,花雁随少不了说几句套话,末了文绉绉地说:“子洲,令尊和胡老九都与本君说了。如今瑠山并不宜采矿,你若是十分中意此处,这山就当本君给你与小林姑娘的赔礼了。”
裴子洲微微一笑:“谢过花君。”
这叫什么事!
狼狈走出花楼,花雁随拳头才慢慢松开,召来护卫赵甲:“周围都搜过了?没有吗?这山多石,也藏不下什么!”
赵甲道:“只有这个竹楼没搜,要不要属下直接进去?”
花雁随大怒:“刚才那两脚把一座瑠山都赔进去了,明着进去,再搜不出,本君还能拿什么赔给他,把你们全送他当禁脔行不行!”
“是是是!”
花雁随俯身揉了揉大腿,刚才真是气得够呛心又急了点儿,要不,踹门这种粗鲁又掉价的事,他才不做呢!
赵甲见状恭维:“刚才那两脚,花君踹的是波澜壮阔、势不可当!”
滚!
几天不见,本君你都敢花狡了。
花雁随平复了一下心情:“等裴子洲出门后,你们去搜右边那个房间,都细心着点。”
赵甲如花雁随命令,守在竹楼附近。
裴子洲倒是机灵,特地避嫌,并给护卫们机会一样,大方地和小林姑娘出门去,你弹琴来我弹瑟,甚是逍遥。
护卫们进竹楼去翻了个底朝天 ,把床都卸成一片一片,谁知还真什么都没有,次次无功而返。
花雁随则在胡老九处住下了。
因是挖完就走,胡老九的住处也极为潦草,就建在山脚下,几个孤零零的石头房子,有些住人,有些堆玉石,实在乏善可陈。
花雁随极少出门,这一出竟然来到鸟不拉屎的瑠山,且一住就不像立即走的样子,真叫胡老九受宠若惊。胡老九费了老大周章,三两天把住处铺得华丽,天天轻歌曼舞伺候着。
当然,胡老九也没琢磨出花雁随的来意。
这天,正饮花茶,胡老九随口说起杭竺那事
![[重生VS穿越]渣!滚你丫的蛋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9/96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