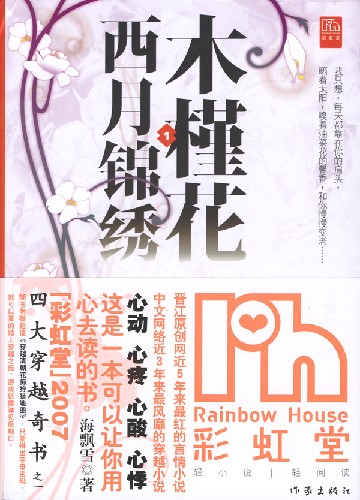木槿花西月锦绣-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城池?”
他这么扯开我的话题,再饶回去不免有些奇怪,只得依言走过去看了一眼那熟悉模型,不由得露出笑容:“二哥,这是紫禁城吧?”
“紫禁城?”他一愣。
“这不是京都的皇城紫禁城吗?”我也迷惑了,难道在这个时空里,紫禁城不叫紫禁城,那叫什么?
他笑一笑:“正是京都的皇城,不过叫昭明宫,连二哥也不知道它还有个别名叫紫禁城?四妹从哪里看来的。”
啊!说溜嘴了,我照老规矩,说是从建州老家的一堆破书中看到的。
旁边一张地图,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古代的地图,和历史课上的果然一样,他见我感兴趣,便兴致勃勃指着地图为我讲解当前形式。
真正让我傻眼的是属于当今东庭皇朝的土地比南宋年间的更少,南边一大片土地都是大理国的!
西北边是大突厥和柔然的地界
东北我们有强大的邻居契丹,东面的东瀛和高句丽这时幸好还没有怎么强大。
突厥前几年被原大将军打败后,东庭国难以负荷战争支出,只好又采取和亲政策,现在两国关系还算马马虎虎,但突厥连年骚挠柔然边界,而柔然是东庭的属国,这场战争,其实意味着突厥和东庭在丝绸之路上的控制权。
然而东庭皇朝却忙着和拥兵谋反的淮南王,胶东王开战,无瑕顾忌,
比较严重的是南边的大理头角峥嵘,越来越不满足于做东庭的属国,大有独立的意识,而他的国土早已包括我那个时代云南全镜,西藏,贵州、四川、越南、缅甸,比东庭的疆域要大得多,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像他的属国了,而且大理最近也在边境不断扰民。
宋明磊侃侃而谈,分析时势,还真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有些所谓当世英雄的苗子。
连我一介女流也听得有些热血沸腾,我心中一动:“宋二哥,刚才你和西枫苑的韩先生也是在论天下时势吗?”
他也不瞒我,当下点头,还直言相告那个韩先生有意要他归到白三爷帐下,我渐渐笑不出来了,而他盯着我的眼睛,轻轻道:“四妹觉得有何不妥?”
我皱着眉头道:“木槿知道大哥和二哥是当世少有的少年英雄,未来的风流人物,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宋明磊轻叹一声,幽幽说道:“四妹所言极是,我们小五义本都是家中遭逢变故,天涯不幸之人,有时别说是愚兄,就连大哥也常叹生不逢时,然则若没有原家,我等又将何去何从,可能流落街头,沦为市井苦力,又或烟花柳巷之所?”
他苦笑一声,我不由赞同地点点头,如果没有原家,我和锦绣还真得可能会卖到娼门中吧,只听他语调一变:“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既入了原家,也命中注定入了这浊世,四妹,如今轩辕氏倾颓,奸臣窃命,外戚专权,边境外族入侵,欲夺我华夏九州,天灾人祸令天下苍生深处厄难,韩先生推算十年之后东庭皇朝必定江山移主。”
他轻嗤一声,炯炯有神地望着我:“何须十年,四妹信不信,愚兄的断言,不出五年,天将大乱,原家必能逐鹿中原,若能助其成就霸业,必能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扶我华夏不为外族所侮也,我等亦能创一番事业,流芳百世。”
他停了下来,略略平复了一下激动,深不可测地望着我,朗朗道:“我一向引四妹为知已,不知四妹以为如何。”
其时我张口结舌,久久说不出话来,我暗自思忖是应该吟颂一下,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还是立刻建议他先定西川为家,后即取荆州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中原可徐图也。
望着那张年青而坚毅的脸,那眼中热切的信任,那句引我为知已的宣言,让我想到了前世我有个曾在飞行大队服过役的小叔叔,虽然退役后下海成了富商,依然又红又专,一生爱好除了攒钱之外便是古今中外战争,我高考加的是历史,所以黑色七月那阵子没事就往小叔叔家跑。
相比起小叔叔的爱好,小婶婶可能对于PARADA的包包和香奈尔的服饰更感到亲切,于是难得他将我这小屁孩当作绝佳的倾吐对象,每每说到北宋的外族屈辱史,近代鸦片战争后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他便捶胸顿足,长吁短叹,毫无CEO形象可言,恨自己不能生逢其时,然则必是中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当朝的汉武大帝,必能令中华民族荡平九州,横扫欧亚大陆。
我当时也听得如痴如醉,以后便效法小叔从商以经济强国,直到遇到长安偷情,紫浮大闹地府,莫名其妙地到了这个奇怪的时空。
塞尔维亚大史馆被炸时,小叔叔曾激愤地挥舞着手臂说:“如果祖国需要,我还是能够重上蓝天的。”
我的心一动,小叔叔的脸庞和宋明磊的脸交叠在一起,一时间恍惚地不知我究竟在那个时空,也许在这个历史的剪影中,我可以替小叔完成他的梦想,亦可保护这一世的亲人,建州的老父,旺财,后妈,锦绣,碧莹,宋明磊,于飞燕,还有原非珏,原来就像宋明磊说的一样,我们生不逢时,但是没有原家,我们可能会更惨,于是从踏入原家大门的一刻起,我们的命运就和原家联在了一起。
我朝宋明磊笑着点点头:“二哥的志向,木槿好生佩服,”对面的年青人明显脸色一喜,我接着道:“既然二哥引木槿为知已,我亦以二哥马首是瞻,前几日二哥提到大哥来信论和突厥的战法,我回去想了想,现在就写给二哥看看,不知能否帮到大哥。”
掏出自制的鹅毛笔,沾了宋明磊的墨,写了几个曾在小叔叔的战争书籍里看到的古代保卫战的战法,比如雀杏,行烟,扬尘车。
还有令美国人很头疼的化学武器,其时我们中国早在北宋年间便有了,那便是毒药烟球,这在本朝肯定是没有的,历史中宋朝有着太强大的若干个邻居,本身又重文轻武,所以一直处于下峰,但神奇的是用于战争上的发明却相当多,只可惜宋朝年间要么是皇帝无能,将军有才,又或是等皇帝有意反击时,朝中又无良将可用,也许这些相对在这个时代先进的战法通过能人之手,会有其用武之地,令我华夏民族抵御外侮。
那宋明磊看了,双眼一下子亮得惊人,一把夺过我的纸,细细地看了起来,他的力太大,一下子把我长满冻疮的手给拉破了,专心直疼。
我吃力地掏出手娟,要包起那红肿的手,他慢半拍地发现我右手血流如注,一把抓过我的手,皱着那好看的剑眉,责问道:“我给你的金创药呢?”
早用完了,这几天不是忙着和你冷战嘛?我当然没好意思问我你要呗,我心说,偏口中讪讪说着:“刚用完。”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生气,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瓷瓶,他拍开我欲接的手,仔细地帮我摸着,我疼得呲牙咧嘴,还得口中称谢,心想这浑小子绝对是故意的。
“宋大哥,”一个娇美的声音传了进来,救了我的,呃!手,我和宋明磊望去,只见门口俏生生地站着一个可人儿,正目光闪烁地盯着我们,这不是二小姐身边那个很红的香芹,她是大房兄妹乳母的独生女,且又和大少爷,二小姐一起长大,据说如果大少爷没有取当今长公主,夫人是打算送她去大少爷那作二房,如今她的方向很有可能是作二小姐的陪房丫环,也就是王熙凤身边平儿的角色。
我对她福了一福:“香芹姐姐。”
看在宋明磊的面上,她对我微微点了一点头,算打了个招呼,冷漠地经过我,径直地走向宋明磊,绽出一丝无比甜美的笑容:“二小姐从法门寺回来了,让我来传个话。”
太好了锦绣那丫头总算回来了,我难掩色。
那香芹看了我一眼,便闭了口。
明白了,我便向宋明磊告辞,他也是聪明人,也不挽留,只将我写到一半的战策,鹅毛笔,卷在一起,又塞入了一盒金创药,一盒治孝喘的稀有灵芝蛇胆粉,是给碧莹的。
他不顾香芹的脸色有些难看,只是温言送别我:“天色已晚,恕二哥不能远送,四妹路上小心,记得代我问候三妹,你定要按时抹药。”
我心头一热,将手卷塞入衣襟,诺了一声,走了出去,但香芹的目光冰冰冷冷。
第一卷西枫夜酿玉桂酒第七章幽径冲鸣鸟
原武递上一盏“气死风”,我道了个谢,慢慢往回走。
我一边走,一边猜想那原非烟要香芹给宋明磊传什么话,奇怪了,看宋明磊也不吃惊的样子,这原小姐经常给宋明磊传话啊,莫非是要学西厢记里周莺莺私会张生不成,虽说以宋明磊这样文武双全的优等生,原非烟看上他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可是他毕竟只是一个身无功名的家臣啊。
我改明得问问锦绣,如果原非烟看上宋明磊,那碧莹二女事一夫的甜蜜计划,很有可能会变成原非烟和香芹霸占小韩信的恶梦了。
想起苦命的碧莹,我暗叹一声,选了条小道,加快脚步,天渐渐黑了起来,起入了幽密的西林,浓雾忽地降了下来,我看不清方向,只能按照旧路的感觉摸索着,“气死风”微弱的光芒在风中飘摇,灭了又亮,亮了一灭。
忽地脚下一绊,我摔倒在地,双手撑着一片湿润,不小心踏进泥溏了吗?我赶紧扶着灯笼,稳住了火心子,往手上一看,悚然一惊,那双手竟满是鲜血,打着灯笼一照,原来前面横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那人身着西枫宛青色的下人服。
我大着胆子往鼻息一探,早已没气了,我哆嗦着正想回去求救,却听到前方脚步声传来,我吹灭了“气死风”,爬着躲到大树后,夜色中两个人影,一高一矮,其中一个打着火把,那两个人着黑色夜行衣,蒙着脸,来到尸体边。
高个的看着地上的死人,对矮个的说:“中了我的九品断肠红,还能撑到这西林,不愧是个幽冥教的人。”
矮个子对高个之人甚为恭敬:“大人果然神机妙算,难怪主公如此信任大人。”
“废话少说,察探如何?可找到东西了?”
“玉北斋内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没有结果,至于那西枫宛……。。大人恕罪,那韩修竹布下的梅花七星阵着实了得,小人实在,实在无法潜入。”
“没用的东西,那上房的紫园呢?”
“紫园的兄弟回过话说也是一无所获,除非紫栖山庄有暗阁,本待再将整个庄园翻个个,只是柳言生陪着夫人回来了,只好再突另谋。”
“主公马上就要起兵了,在那以前,一定要比幽冥教早一步找到‘无泪经’。不然等大军进了西安城,人多眼杂,就难办了。”
“是!请问大人,小人是否该按老规矩处置这厮?”
“去吧。”
树后传来奇怪的嘶嘶声,伴着阵阵的恶臭,我偷偷瞄了一眼,那两个人已经飞向夜空消失了,哇!武打片!
而那尸体正在起着某种化学反映,月光下,血水混着白沫嘶嘶地融化,我的鸡皮疙瘩满身长!这可不是什么恐怖片哪!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眼前,恐怖之极。
我看那尸体化得快差不多了,便软着脚跑出来,我抖着手亮了火折子,点燃气死风,那尸体原来的地方只剩一淌白沫。
月黑风高杀人夜,一灯幽灭,一个柔弱美丽的少女(自我陶醉),独自对着一淌尸水哆嗦得如同寒风中的枯叶,然后一丝呼吸,毫无预兆地在我耳边吹起,像是贞子在我身后似得,我更胆破心惊。
“你将他化尸了?”一个男子的声音轻轻从背后传来,比这入夜深冬还要冷。
我啊地一声把气死风丢在地上,跳开了去,一个颀长的身影,长长的黑发飘飘,白衣渺渺,脸上戴着陶制的白面具,那面具轮廓分明,表情冷酷,像古希腊的雕像,没有眼珠,如鬼魅一般,毫无人气。
我骇地跌倒在地上,张嘴想说什么,半天没发出声音,这究竟是人是鬼?莫非是刚才那个死人的鬼魂?
那个白影越飘越近,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声音:“不,不,不,不是我杀的,你,你,你,是,是,是谁?”
白影忽地在我面前消失,正当我以为那只是受了严重惊吓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时,忽地呼吸又出现在我的耳边。
“你是幽冥教的还是大理国来的?”他开口了,那声音优雅,却冷酷无比。
“我,我,我不,不,是奸,奸,细,细,什,什,什,什么无赖经。”我爬开一米远,脚那个软哪。
“乖乖告诉我,你的主上是谁,为什么要找寻无泪经?不然我让你求生不能,求生不得。”他很轻很柔地说着,仿佛饭店服务员在说,我可以来收了吗,要我帮您打包吗?
我提起些勇气,指着那“白面具”:“你,你,你又是什么人,这么大黑夜里穿得一身孝服,戴个白面具像吊死鬼似得,你,你,你以为你在拍电视剧吗?”
话一出口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