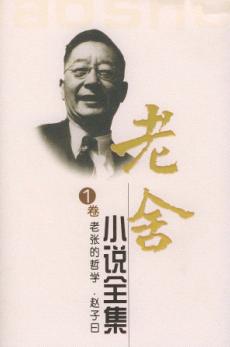绿皮火车-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结果出乎意料,人是越来越多。我被迫让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过一会儿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门后的角落里。耳闻卖票的人解释:“里面只有小板凳可以坐了。”过一会儿,小板凳也没有了,只能站着了。再过一会儿,站也站不下,差一点要卖挂票了。
演出气氛非常好。观众很多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艺青年。三个小时的现场,静悄悄地专注地聆听。我们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现场是对自己音乐的加持。如饮美酒,如对良人。
春节也不是只吃吃喝喝。虽然没有电视,却看了一场更跌宕起伏的连续剧,那就是韩寒大战方舟子。
先是麦田质疑韩寒作品有人代笔,紧接着道歉,方舟子等人又冲了上来,感觉就像是那种二战大片——《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保卫战》……方称自己挖了个大坑,支持韩寒的人都会被陷在里面。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面有罗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认识的人。越看越心痒,结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发微博如下:“这场混战,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只是一厢情愿的虚幻。韩寒电话里声音很好听,用你文章,先电话感谢,杂志出来后,亲自写信致谢,这样有情商的做书人不多。他还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个人相信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做人的基本礼节。”结果被转发了四百次。有一条回复很可爱,“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节,谁和谁再吵上一架,照这样下去,电视台就要倒闭了。
年过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拥挤在未来。抓紧订机票,北京像一个大磁石,你不喜欢,但总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国贸的地铁、三环的堵车,以及一个个人山人海的饭局,不怀好意地召唤你。
虽是末世之年,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煞有介事地继续下去。小车不倒向前推,有个词叫“飞龙在天”,然而我们只是大地上,蝼蚁一样忙碌的龙的传人。
“龙年吉祥。”对自己说,也祝福全中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上的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而被打。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二十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的事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回到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我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人家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到家还念叨着,人家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地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写文章,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的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果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家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他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我和她妹妹,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槃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他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铁西区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个小孩。他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失踪的人
词曲:周云蓬
交给陌生人五分钱
妈妈买了一颗子弹
该把它放到哪里
想看见又害怕看见
妈妈成了一个小姑娘
光着脚跑到大街上
她想把子弹藏起来
躲开众人的目光
时间请你停下吧
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让她跑完所有的街道
再放她死去
在一条街的转弯处
一群孩子追上了她
慌忙中她把子弹藏进了
她女儿的身体中
她又把女儿埋在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谁也别想找到她
在苏州城的阊门外
梦中的家门窗紧闭
只有海鸥从海上飞来
报告大海依然胜利
报告亲人们早已离散
再没有什么消息
吹不散的烟
词:周云蓬
曲:来自迈克尔·杰克逊《拯救地球》
汶川,
汶川,
你在哪里,在天上吗?
我的婆婆,在虚空里做了一碗,担担面。
那天空镀了金,
晃得人人都看不清,
有谁能够,扶起一所房子呢?
人说,
今年的汶川,满山的樱桃都熟了,
已没有人来收割。
一阵烟,化成了云烟,
像山一样,
凝固在我们头上。
不管,
长年的北风还是来自海上的南风,
都不能把他们吹散。
请你,
勤劳的土地,
请你不要再五谷丰登,
因为土地上已经没有了他们。
散场曲
词:周云蓬
曲:美国民谣
灯已黯了,
客人们就要退场了,
这是最后的音乐,
没有人需要鼓掌。
只剩下你,
来自异乡的姑娘,
坐在吧台旁,
想着你爱人已睡了。
今天不是周末,
没有人需要疯狂。
外面雨下个不停,
只有我在这里唱。
没有公共汽车了,
通向你郊区的住房,
找个大排档,
一杯一杯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