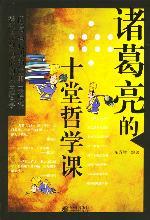从诸葛亮到潘金莲-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角得的不是血癌,而是肚子会鼓得像青蛙一样,上面血管盘结的肝癌;那么她们的浪漫爱必然会大为“失色”。我们若考虑疾病的隐喻作用,则不仅能更确认林黛玉得的是肺结核,而且可以说,林黛玉“只能”得肺结核,因为其他病都不“合适”。
在第八十三回,贾府请了高明的王太医来为黛玉诊病,王太医说她是“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本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笔者虽不懂这种夹杂阴阳五行的中医病理学,但知道他意思是说林黛玉的病是“平日郁结所致”。王太医更说,这种病“即日间作息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
稍懂现代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它的病源是“结核菌”(TBbacilli)。但在将王太医的一番话打为“胡说八道”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人的观点。在科霍(R。Koch)发现结核菌并证实它是肺结核的病源(1882年)之前,西方人也一直认为遗传体质、气候不顺、少活动、心情郁闷等才是它的病因。即使到了近20世纪中叶,罹患肺结核的小说家卡夫卡依然认为“我的心灵病了,肺部的毛病只是我心灵疾病的泛滥”,“我开始认为结核病不是什么特殊的病,而是‘死亡之菌’的猖狂所致”。
文学家甚少以科学观点去看疾病的,他们着重的是疾病的文学观。即使确知结核菌是肺结核的病源,但这也只是“外在的物理因素”,它另有“内在的精神因素”,王太医所说“平日郁结所致”指的似乎就是这一点。文学家在以疾病来作为隐喻前,已将疾病本身浪漫化了。
优雅的艺术家之病
肺结核是自18世纪以来,被文学家“浪漫化”得最彻底的一种疾病。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在《病的隐喻》(DiscasesasMetaphor)这本书里,对肺结核在西方文学作品里的浪漫化与隐喻化过程,作了一些独到的阐述,下面笔者就借用她的几个观点,来进一步分析林黛玉的才情、人格与爱情。
拜伦、济慈、萧邦、史蒂文生、劳伦斯、梭罗、卡夫卡等知名的艺术家都患有肺结核,肺结核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之病”,它不仅是一个人“优雅”“细腻”“善感”的指标,更是一个人“才情”的戳记,雪莱就曾对“肺病鬼”济慈说:“这种痨病特别喜欢像你这种能写出如此优美诗文的人。”浪漫主义的兴起,跟当时很多艺术家都是“肺病鬼”也许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有人就指出,当代文学与艺术的没落,乃是因为艺术家较少得肺病的关系。
到底是多愁善感的人较易得肺结核?或得了肺结核的人较易变得多愁善感?我们不拟探究它们的因果关系。虽然绝大多数的肺结核患者都属于生活条件很差的贫民阶级,但肺结核还是被美化成多愁善感与才华横溢的象征。作为一种“艺术家之病”,它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也一再出现于文学作品中。
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是一个最多愁善感、最优雅细腻、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她不仅写得一手好诗,弹得一首好琴,而且还经常“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怕落地的花瓣被糟蹋了,而为它们准备了花,一面葬花,一面哽咽低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种“美丽的哀愁”、“细腻的才情”正需要肺结核这种病来衬托。
一个艺术家如果能死于肺结核,可以说比死于其他疾病都要来得“高贵”,因为肺结核有“美化死亡”的效果。狄更斯就曾说:“肺结核……灵魂与肉体间的搏斗是如此的缓慢、安静而庄严,结局又是如此的确定。日复一日,点点滴滴,肉身逐渐枯萎消蚀,以致于精神也变得轻盈,而在它轻飘飘的负荷中焕发出异样的血色。”
………………………………………
林黛玉的爱情、疾病与死亡(4)
………………………………………
林黛玉的死于肺结核,除了象征“浪漫爱”的必然结局外,更代表了一个“艺术家”的理想归宿。“艺术家”决定她死亡的方式,而“浪漫爱”则决定了她死亡的时刻。一八二八年,拜伦望着自己镜中苍白的容颜说:“我希望死于肺痨”,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拜伦回答说:“因为若如此,那些女士们就会说:‘看看那可怜的拜伦,他死时的样子多么魅人!’”林黛玉的死,正有着这种魅人的意味。
事实上,肺结核的美感乃是来自一种“欺蒙”,譬如病人的“容颜似雪”,是生命快被淘光的危象,而“香腮带赤”则是发烧的一种反应。在文学作品里,被浪漫化的肺结核说的通常只是它美丽的一面;而《红楼梦》很难得地也触及了它的另一面,那就是林黛玉令人不敢领教的脾性。
林黛玉“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除了服侍她的雪雁、紫鹃外,不得下人之心,而雪雁、紫鹃先时还解劝她,“用话来安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她,由她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
她的细腻,使她的心像针儿一样,在善感之中经常刺伤了别人,被刺伤得最多的,当然就是爱她最深的宝玉。
这些不好的脾性跟她的才情、优雅、细腻、善感乃是一体的两面。疾病可以引出一个人最好的一面,但同时也会暴露他最坏的一面。透过肺结核这个隐喻,我们似乎可以更加了解曹雪芹所欲赋予林黛玉的才情与人格本质。
内心闷烧的热情
前面已提及,林黛玉的病象征她对贾宝玉的爱是一种“有病的爱”“自虐性的爱”。那么当这种病已明确化为肺结核时,它是否另有其他意涵呢?
托马斯·曼在《魔山》(TheMagicMountain)这本小说里曾说:“疾病的症状是爱情力量的假面演出,所有的病都只是爱的变形。”肺结核的患者会发烧,而使脸颊现出红晕,所以它是一种“热情之病”(adiseaseofpassion);但因为它发烧时的体温通常不会很高,所以这种热情较接近于“在内心闷烧”,有着压抑的性质。
我们若以此来考查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情,那的确是属于有些压抑的,在“内心闷烧”的热情。
笔者在前面介绍林黛玉肺结核的症状时,曾提到在第三十四回,她在宝玉送来的绢子上题诗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照镜子发现“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这一方面固然是肺结核发烧的症状,但一方面也是她“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的结果。病欤?情欤?我们宜两者合而观之。
在贾宝玉有了提亲之说后,我们最可以看出黛玉的热情在“体内闷烧”的变化。当她听到丫环误传宝玉已订下知府千金小姐亲事的消息后,热情失去了归依的对象,于是在自己“体内闷烧”,病情加剧;后来又听说没那回事,贾母希望“亲上加亲”,属意“园里的姑娘”,黛玉觉得那就是自己,在体内闷烧的热情又有了出口,病情也跟着好转;到最后确定宝玉要娶的是宝钗后,无处发泄的热情终于又退回体内急剧燃烧,以致香消玉殒。
在这段期间内,大观园里的众人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邢夫人和王夫人是“有些疑惑”,而贾母“倒是略猜着了八九”,她知道黛玉的病“时好时坏”代表的是她心中热情的波涛起伏。
纪德在《背德者》这本小说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布局,书中主角米契尔是个肺结核患者,他有同性恋的倾向,但他压抑这种爱,直到有一天,他不再压抑,接受了这种爱,他的肺结核竟也不药而愈了,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除了“自虐”外,更有很浓厚的压抑色彩,如果她能更自然地让热情流露,也许就能减少或者不需要那么多症状。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基本上,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是最前面所说的“古典浪漫爱”,欲望是不能消耗的。
斯人而有斯疾也
红学专家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写,而是高鹗的续作,本文所谈林黛玉的爱情、疾病与死亡,从第二回到第九十八回,贯穿这两者,笔者觉得,曹雪芹和高鹗对林黛玉爱情、疾病与死亡的铺陈,倒是首尾相扣,有着相当的—贯性。
如果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将“真事隐”,那么书中的林黛玉可能有个来自现实生活的“蓝本”。而高鹗的续作则全凭“文学家的想象”,他在第八十三回就让林黛玉“惊恶梦”,然后“吐血”,然后“死亡”。我们无法揣测这种演变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胡适说得好:“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致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为什么“作一个悲剧的大结束”就是续得好、续得妙,胡适并没有说,但它的答案似乎就在笔者前面所说“古典浪漫爱”的基本结构里。其实中国旧小说及民间故事里,多的是以悲剧收场的,只是它们素来受到文评家的漠视与鄙薄而已!
生老病死虽是人生必经之路,但一个文学家和一个医学家对疾病与死亡显然是抱持着不一样的态度,并会给予不同诠释的。医学家尝试使人免于疾病和死亡,而文学家则试图赋予疾病和死亡以意义。笔者不揣浅陋,从医学的观点出发,但却想赋予林黛玉的疾病和死亡特殊的意义,期使我们对这位病美人的才情与爱情本质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基本上,我是把林黛玉当做“病人”而非“美人”来看待的,但分析到最后,也不禁像孔老夫子一样叹息:“斯人而有斯疾也!”
………………………………………
《封神榜》中的魔法与命运(1)
………………………………………
《封神榜》的历史位阶与心灵位阶
在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里,《封神榜》是相当突出的一部,也是笔者少年时代最早接触、最沉迷于其中的“野史”之一。当时年幼无知兼且慧根短浅,觉得《封神榜》比《三国演义》有趣多了。以传统的文学品味来衡量,《三国演义》与《封神榜》当然有着天壤之别,《封神榜》不仅文字拙劣、漏洞百出(譬如在第一回里,纣王就用“毛笔”在女娲庙“题诗”),更涉神怪,令鸿儒摇头,硕彦皱眉,有识之士不忍卒读。但《封神榜》与《三国演义》同为野史小说,这种根据正史来演义、终至偏离正史的说部,其文句的是否典雅、结构与内在逻辑的是否严谨,恐怕都是次要的问题。它更重要的目的,似乎是在揭示庶民阶级对朝代兴亡及人世沧桑的一些看法。本文即尝试从这个角度来剖析《封神榜》。
庶民阶级对朝代兴亡及人世沧桑的看法,有其不变的本质,也有进化的形貌。《封神榜》像《三国演义》及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演义小说一样,都是成书于元末及明代的两三百年间,但它们诉说的却是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同一时代的作者走进不同阶段的历史中,尝试捕捉不同时空下的人事与观念,历史的结构是大家所共认的唯一参考座标,但他们所用的除了故事中人物应有的“历史位阶”外,还有作者个人的“心灵位阶”。
在依“历史位阶”而重新排列的历史演义小说中,《封神榜》的排名即使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的。作为“民间中国历史”的龙头,它所描述的不仅是“人间的兴亡与干戈”,还包括“诸神的争吵与倾轧”,两者杂然并陈,也因此而常被视为是“神怪小说”。
但神话乃是最早的历史。描述希腊早期历史的《伊里亚特》(Iliad)史诗,里面同样充满“诸神的声音”。当然,《伊里亚特》的成书最早部分可溯自公元前11世纪;《封神榜》说的虽是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历史,但却成书于公元15、16世纪。我们很难说它是作者刻意对历史的回归,真要回归历史,书中就不应出现文房四宝这类东西。因此,除了客观的“历史位阶”外,还需考虑作者“心灵位阶”的问题。
同一时代中的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心灵位阶”。在16世纪,当欧洲人进入“理性意识”时期时,澳洲的土人仍处于“无意识”状态,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似乎还在“梦游”状态中。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