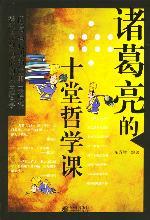从诸葛亮到潘金莲-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真是天从人愿”……这些让人联想到性的情节都被删略了,它旨在强化梁山伯对祝英台的爱乃是清纯的“非性之爱”。
二、撤消天庭势力的介入。在长亭相送中,山伯无法领会英台吐露的真情,原本是因为太白星君的介入,摄去山伯真魂而换上个呆魂所致,所谓“天上掉下无情剑,斩断人间恩义情”;但在电影里,却是缘于梁山伯自身清纯无邪的心灵,强调了浪漫爱的“人间性”。
三、凸显阶级意识与人品风格,在原故事里,梁家乃是“家财万贯,骡马成群”的富豪,但在后来的戏曲及电影中,则成为茅屋两三间的“贫户”;而马文才原本也是个“人品出众,满腹文章”的浊世佳公子,但却被贬抑成尖嘴猴腮、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在家世与人品方面,和梁山伯恰成一鲜明的对比,借以衬托出梁祝之爱的悲壮与凄美。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修饰先人所流传下来的神话或传奇,使它能更符合自己的认知架构与时代意识,但其中仍有一些不想或不容更改的特质,它亘古弥新,可以说是分析心理学里的“原型”,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里的“普同结构”,梁祝故事在蜕变中的不变本质,依然是在前面所说的“情欲的不得消耗”与“死亡”。
殉情——悲壮的抗议
很少人知道《七世夫妻》中李奎元与刘瑞莲的那一段“美满姻缘”,因为它一点也不“感人”。令人传诵不已的反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万杞良与孟姜女、商琳与秦雪梅的爱情悲剧,而这些悲剧乃是玉帝刻意安排金童玉女到人间所受的折磨。为什么“上天的折磨”会成为“人间的至情”呢?这多少反映了人间和天上具有不同的律则。
情爱是凡念,天上不朽的神仙是没有情爱、也不应该有情爱的(希腊诸神虽也谈恋爱,但因为他们不会死,结果使诸神间的恋爱变得哩吧唆,相当“烦人”),金童玉女因为动了凡念,彼此有了情意,所以玉帝罚他们到人间受些折磨。对天上与人间这两个世界,我们可以理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天上∶人间
无情∶有情
不朽∶短暂
秩序∶骚乱
安适∶悲苦
人间是个有情世界,但相对于理想中的不朽仙界,它是短暂的、骚乱的、悲苦的,而这也正是人间浪漫爱的属性。“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历来即有不少骚人墨客发出此种疑问与浩叹,死亡看似上天对人间痴情者的惩罚,但同时更是人间痴情者的一种抉择、一种模拟与一种抗议。在《七世夫妻》的前五世中,太白星君从中作梗,目的只是要拆散人间的恩爱男女,并非要置之于死地,后来这些男女虽各因此一横阻而劳役死、相思死、悲痛死等,但多少予人“身不由己”的消极感觉。直到第六世的韦燕春与贾玉珍,韦燕春在蓝桥痴候,太白星君兴风作浪,弄出一场倾盆大雨,原意也只是在于阻扰,但韦燕春却宁可“抱柱而死”也不作丝毫的退让,透过此一“死亡的抉择”,他回绝上天的眷顾,抗议命运的作弄,同时见证人间爱情的不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痴情者为我们塑造了有别于上天意旨的人间典范。
也许是因为韦燕春“悲壮的抗议”,而使天庭或编故事者在第七世为他们安排了一段“美满姻缘”,就像西洋的浪漫爱,经过几世纪的“反婚姻”(anti…marriage),到17世纪也开始出现了以结婚为结局的美满故事。但令人感动、令人传诵不已的依然是以死亡为结局的爱情悲剧,人间最甜美的歌诉说的总是人类最悲壮的处境。
理想异性与电影中的角色反串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之所以造成轰动,令人着迷,除了我们观赏悲剧时所产生的道德同情与审美同情外,还有性别角色的错置问题(电影的技巧此处不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剧中,令梁山伯着迷的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但在剧外,令观众(特别是女观众)着迷的反而是女扮男装反串梁山伯的凌波。这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讨论:
………………………………………
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4)
………………………………………
第一,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异性形象”,称为“内我”;男人的“内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叫做anima,女人的“内我”(心目中的理想男人)叫做animus。凌波是个女人,她所反串的梁山伯是个痴情男子,当她尝试以自己心中的“内我”来呈现一个痴情男子的形貌时,她同时也呈现了大多数女性心中的“内我”,也就是她们心中的理想男人,只有女人才晓得女性心中的理想男人是副什么模样!这种情形就好像梅兰芳男扮女装演杨贵妃,而令张季直、蔡元培、梁启超等男人击节叹赏一样,因为梅兰芳演活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人。
第二,女观众着迷凌波,不只是因为凌波演活了她们心目中的理想男人所产生的“移情作用”,同时因为凌波是个女人,在现实社会里,“女人捧女人”并无道德上的禁忌,她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大捧特捧,但在这种“捧”中,女观众所宣泄的主要仍是对那虚无缥渺的理想男人的爱意。
性别角色的混淆,现实与虚幻的混淆,俗世男女所需要的大概只是一场梦幻式的浪漫爱吧?“此情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天上是没有这种浪漫爱的,而人间有的是什么?我竟一时糊涂了!
***************
*古典今看第四部分
***************
潘金莲的“药死”武大郎与“淘死”西门庆,都在彰显淫妇的可怕:淫妇不仅是“丈夫孝服未满,就嚷着要嫁人”而已,更会把丈夫的灵堂当做阳台——在武大郎的丧礼仪式中,潘金莲竟在房间里与西门庆幽会;而在西门庆的丧礼仪式中,她又和陈经济云雨不歇。“性”与“死”的诡秘结合,让人不由得想起“黑寡妇蜘蛛”“血腥玛丽”等令男人颤栗的、阴森而诡异的雌性本质。
………………………………………
《子不语》中的灵魂物语(1)
………………………………………
对儒家思想的补偿与反动
袁枚(子才),清乾隆年间进士,多才多艺,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才子,他和同年代的纪昀(晓岚)齐名,时人称为“南袁北纪”。无独有偶,纪昀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一书,“诡奇谲,无所不载”;而袁枚亦著有《子不语》一书,“怪力乱神,游心骇耳”。
袁、纪这两位才子,虽非儒学大师,亦饱读四书五经,乃杰出的“孔门弟子”,《论语》里明明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们为什么要违背圣人的教诲呢?传统的说法是“其大旨悉系于正人心、寓劝惩”,但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看法。笔者以为,《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乃至五百年间的明清笔记小说,之所以充斥怪力乱神,更可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偿”、甚至“反动”。
作为一种入世哲学,儒家重视的是在此尘世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本是好事,但当它上下两千年,成为一个民族读书人的基本信仰时,“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的立场,却使它严重缺乏了宗教信仰中的某些基本要素,以及对奇异现象的探索精神。袁枚说:“昔颜鲁公、李邺侯,功在社稷,而好谈神怪,韩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驳杂无稽之谈,徐骑省排斥佛老,而好采异闻”,可见儒者私底下喜欢搜神探秘,是有其历史传统的。在儒家“忧患意识”的笼罩下,豪迈不拘之士进德修业之余,心仍有所未盈,意犹有所不尽,于是另辟蹊径,“采掇异闻,时作笔记”,正所以借此宣泄郁积于他们心中的“宗教感情”和“幽暗意识”也!
袁枚的《子不语》,当视为此类作品。但像大多数的明清笔记小说,他只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并未尝试赋予这些怪力乱神某种理论架构,甚至亦未加以分门别类。《子不语》中近千则游心骇耳之事可谓包罗万象、芜杂异常,笔者这篇短文自是难以面面俱到,而只能就中择取某一类题材来伸述之。笔者所选者名曰“灵魂”,它正是最困惑人心,也最为儒家学者所忽略的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民间信仰及佛、道思想里,是有“灵魂”的理论架构的,袁枚不可能不知,也许为了避免和儒家抗礼的嫌疑,他舍而不用,但笔者在下面的论述中,却不得不使用这些架构,来钩沉、排比《子不语》中涉及“灵魂”的故事,然后赋予他们一些意义。笔者将这些故事分为“魂离”“僵尸”“鬼”“附身”“前世”几大类,分述如下:
灵魂出走——魂离
《庄生》是一则“魂不附体”的故事。话说庄生为陈姓家西席,某日课毕归家,路过一桥,失足跌倒,起而复行,到家扣门不应,乃返陈氏宅。见陈家兄弟弈局,乃闲步轩后,睹园亭中一临盆孕妇,色颇美。庄生自觉非礼而退,返观陈氏兄弟弈局中,并代为指点,主人张皇似惊而不采,忽而灯熄,庄生复归家,至桥,又一跌,再起而复家扣门,入则罪其家人前次扣门不应之事,家人曰:“前未闻也。”次日赴陈家言昨日观棋、见孕妇、灯熄之事,主人骇言并未见其复至,亦无孕妇;同至轩后,则见菜园半亩,西角一猪圈,母猪适生小猪六口耳。
故事中的庄生“悚然大悟”,他认为自己过桥一跌,“灵魂出窍”,返家扣门与至陈家观棋、见孕妇都只是灵魂的经验,是别人无法感知的;当脱窍的灵魂过桥再一跌时,魂才又附体,恢复能思考又有血肉的自我。
在西方,也有很多“灵魂出窍”的故事。譬如德国大文豪歌德有一次和友人结伴回威玛,在途中忽见另一友佛瑞利德克,居然身穿歌德睡袍、头戴歌德睡帽、脚拖歌德拖鞋出现在马路上。歌德大惊,但因身旁友伴“什么也没看见”,歌德很快认为这只是“幻觉”,并担心佛瑞利德克是不是“死了”。回到家后,歌德一进门就看到佛瑞利德克居然就坐在客厅里,他还以为又看到了幻影。佛瑞利德克向歌德解释说,他因在路上成了落汤鸡,而狼狈地来到歌德家中,脱下湿衣服,换上歌德的睡袍、睡帽、拖鞋,刚刚在摇椅上假寐时,居然梦见自己走出去,在路上看到歌德和其友伴,还听到歌德和友伴的对话!
歌德和佛瑞利德克都为此而大惊失色!佛瑞利德克认为自己在梦中“灵魂出窍”,而歌德则认为自己在路上看到了他出窍的“灵魂”。歌德此一离奇经验,其实较类似《唐人小说》中的《三梦记》,但它同《庄生》一样,都需以“灵魂存在说”为前提,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民族、很多文化所共有的信仰。这个信仰反映了人类的不朽渴望,肉体会死亡,而灵魂则是不朽的。儒家也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说法,但这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希望大家做圣人的想法一样,是让一般老百姓感到为难的,民间百姓宁可相信自己生来就具有某种不朽的本质,那就是“灵魂”。
灵魂是附身在肉体上的,人死时,灵魂脱离肉体;这种观念很自然地导致如下想法:生时若遇到类似死亡的情境,灵魂也可能脱离肉体。这些情境包括睡梦时、暂时丧失意识(如跌倒、车祸、手术麻醉等)时,庄生与佛瑞利德克的“魂离”都符合这个模式。
魂飞魄不散——僵尸
………………………………………
《子不语》中的灵魂物语(2)
………………………………………
《南昌士人》一文,则是一个讲述人死亡时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故事。话说南昌士人某,寺中读书,与一学长甚相友善,学长归家暴卒,死者夜来,登床抚士人背,与之诀别。士人怖,死者慰之,以老母寡妻及未付梓文稿相托,言毕欲走,士人见其言语近人情,貌如平昔,乃泣留之,死者亦泣,重叙平生。俄而士人见死者貌渐丑败,惧而促之去,尸竟不去,屹立如故。士人愈骇,起而奔,尸随之奔,追逐数里,士人逾墙仆地,尸则垂首墙外,口中涎沫涔涔滴到士人面上。天明,路人饮以姜汁,士人始苏,而僵立之尸亦舁归尸主家成殓。
故事里的“识者”说:“人之魂散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其(故事中的死者)始来也,一灵不泯,魂附魄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毕,魂一散而魄滞。魂在,则其人也;魂去,则其非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此一见解更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国人认为,灵魂有两大类,精神性的灵魂称为“魂”,物质性的灵魂称为“魄”。活人是魂、魄、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