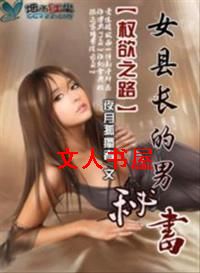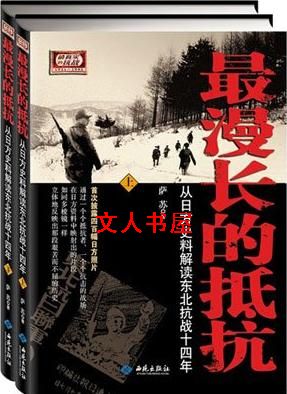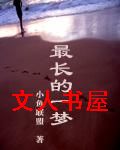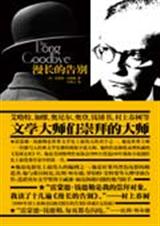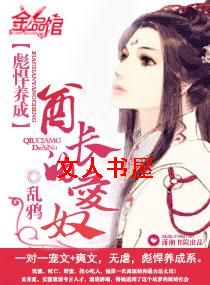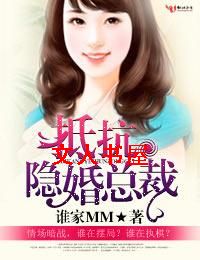最漫长的抵抗-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者说咱哪儿敢寒碜王司令呢,咱就是问抗联当年多艰苦,多顽强……
老爷子说了,你干吗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有多惨呢?
实话告诉你——
那时候鬼子吃啥老子吃啥,他仓库里有的,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
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啥山珍野味老子没吃过?
你也是当兵的,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仗,谁愿意给你当兵?我能扩军吗?
还有,你干吗老缠着我问库楚河那一仗?
老子那一次西征兴安岭,大小十六仗,除了这一仗,哪一仗让狗操的占过便宜?
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你什么意思?!
记者傻眼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上头让他采访抗联,就俩主题:一个牺牲,就是要多惨有多惨;一个艰难,就是要多苦有多苦。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不能跟上级对着干不是?
最后那次采访不了了之,好像连发稿都没发成。
按照萨的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虽然艰苦卓绝,但这些刚强的中国人并不是整天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们的坚韧同样体现在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上。
在发现的一路军陈翰章将军日记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记录——1939年4月6日,陈翰章既听取返回的侯国忠副师长的汇报,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讨论和日军作战的问题,制订了发动奇袭以阻止日军向西方增援(似乎那边有友军在活动)的作战计划,下午还讲了两个小时“群众常识”的课,又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本来疲劳已极,但是,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前后才能够就寝,自述“原因是他们放留声机放得太吵了”。
1939年,抗联的部队居然在听留声机,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这并不是孤证,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他们在撤退到苏联的时候,还曾在出境前埋了一台留声机,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再去找,却没有找到。这台留声机还颇有来历,是著名的“十三省”中的“三省”、六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君从缴获敌人物资中发现的“破烂”。
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始终带着一只口琴。
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一条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没有对生活子孙的热爱,焉有誓死决绝的刚毅?
那段采访的片段,很容易让人对王司令的形象产生误解,其实连日本人都知道,王明贵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多年在苏联的生活,又让他精通俄语。这熟悉三国语言的优势,就是王司令员不想当兵了,进外交部跟陈毅元帅搭伙去也会是一把好手。
只有在战场上,王明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云龙”。他唯一那次不大光彩的仗,也打得可圈可点。这一战三支队被打散,王明贵带着身边的人员且战且退,打到黑龙江边只剩二十几骑,却陷入了敌军伏击,带队伏击王明贵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锹田讨伐队。
然而,被日军称为“袋中之鼠”的王明贵却乘锹田分兵试图合围之际,果断率部直扑敌讨伐队指挥部,发起了主动的决死进攻。猝不及防的日伪步兵才发现机动中在雪地上和骑兵交手近乎自杀,打打不过,追追不上,逃逃不了。激战中七八倍于王明贵部的锹田讨伐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包括讨伐队队长锹田德次郎(警正,相当于日军中队长)、副队长井泽寿一(警佐)、伪警察队长刘霖(警尉)在内的三名指挥官一个也没能跑掉,全部被击毙在战场上。
王明贵率部过江而去。
那一仗,中国将军王明贵让日本人明白了什么叫“十三检点回马枪”。
那一仗,王明贵身边的24骑,战死13骑,撤回苏联境内基地的仅余11人,半数带伤。壮哉!
可以看到当时抗联部队已经换穿苏式军装并佩带苏军军衔。他们同时拥有三个番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和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多重的番号反映着这支部队在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上独特的地位。
王明贵当时担任该旅教导第三营营长。
这段经历还引出后来一段“王明贵被周总理批评”的趣事。有人这样描写这段事情——“那一年,周总理陪同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来访问,王明贵组织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敬礼,报告,欢迎,一切组织的井然有序,完毕,上去搂住这位领导人的脖子,说,老金,可想死我了。在东北抗联过境部队改编的抗联教导旅,这位领导人是一营营长,王明贵是三营营长。后来,周总理批评了王明贵,因为这位领导人不再是当年的营长,而是国家元首。这位领导人回国后,给王明贵发来两车皮苹果,王明贵都分给部队了。”
入苏这段经历对王明贵影响应该不小,对苏联正规部队环境的熟悉,使王明贵一度担任解放军最早的步兵学校副校长,不过后来因为这个挨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一度作了校长,王明贵应该也可以算是“儒将”了,但是,这位将军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没有那样温文尔雅,他们对他的评价竟然是——“狞猛”。
在今天的日语里,这是个通常用来形容史前怪兽的词儿啊。
在《啊,满洲》一书542到543页,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留写有一篇《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这里面的“匪贼”,指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抵抗力量。北原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曾带营林署的采伐队到汤旺河负责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们这些日伪林业官员的生活是“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在战地一样”。“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三千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样的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举手之间都可能发生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
之所以造成他们这样紧张,原因是“在诺敏河和汤旺河之间,是狞猛的‘匪贼’的巢窟,尽管在森林警察队警戒之外,在(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作业期间也要求日军前来驻屯,但是‘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仍不时发动夜袭,惨杀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这条生命随时可能像汤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
结果,在王明贵等抗联部队的不断袭击下,最终北里虽然十分努力,“血枯,肉削,几度昏倒”,但是任务“到底完遂不可能”,“如此苦心生产的木材,在还没能供军队使用上的时候,就战败了”。在哈尔滨国立饭店听到天皇宣布战败的“玉音放送”,百感交集的北里等人忍不住趴在地上“号泣”起来。
其实,王明贵将军要是活着,听到这个日本人的话恐怕要大呼冤枉。
因为1942年抗联的作战方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赵尚志的牺牲和对最新敌情的了解,抗联逐渐意识到在日军将数十万关东军主力调集北满,又大搞开拓团和集团部落的情况下,重建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已经不现实。因此,抗联教导旅主力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入以小部队入境袭扰和谍报活动,特别是实施对苏满边境日军阵地配置情况、兵力部署等的侦察,加强地下组织,以便配合盟军未来对关东军的作战。
在这些小规模的入境作战中,王明贵、刘雁来、徐泽民等都十分活跃,但其具体行动至今尚无完整记述。汤旺河地区是王明贵将军早年战斗的地方,他率领小部队入境的时候,在这里建立秘密基地并活动不奇怪,但要对付的主要目标肯定不是日本人这个林业工作队,搂草打兔子地打几仗,干扰一下敌人的开发活动,顺便弄点儿给养恐怕是有的,把北里等人逼到这种地步大概王明贵自己也没想到。
对王明贵部队这一阶段活动地描述,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啊,满洲》第549页)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北里1938年开始在诺敏河林区任职,当时周围还有马占山余部在活动。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当地就只有抗联在抵抗了。以少数兵力就牵制住三千森林警察队,对于这位“狞猛”的中国将军,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北里仍然表现出了由衷的钦佩。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很多人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在1940年杨靖宇将军殉国后便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他们始终在敌后孤独而顽强地战斗着。说他们孤独,是因为抗联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说他们顽强,是因为抗联在东北境内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实际上从未停息。例如,在《啊,满洲》的第691页,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的回忆文章《通河县副县长尾原势一君的最后时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当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我方资料,这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便是赵尚志将军亲自部署潜伏,由杨春、杨振瀛父子两代经营的抗联北满(通凤)交通总站。起义部队一度占领通河县城,并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敌军镇压最终失败,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战败之后,中村贞成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贵。
王明贵将军所在的抗联教导旅在盟国对日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之战中,共有三支部队参战:第一部,分成57个小组,以空降等方式携带电台于苏军之前率先攻入东北境内,作为突击队对敌后方发起大纵深袭扰(因为人员不足,连李敏这样的女战士都参加了这支部队);第二部预先渗透入境,潜伏在日军阵地后方,在苏军对日军各要塞和部队布防情况进行侦察,攻击发起时实施炮兵引导,甚至直接渗透攻击日军要塞阵地;第三部担任向导和翻译,随苏军先头部队行动。王明贵将军在战斗打响时在海拉尔方面,攻占齐齐哈尔后,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
很感谢一位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朋友提供了当时目击的情况——“1945年9月前后,抗联战士协助苏联红军痛歼日寇关东军后,进驻齐齐哈尔市,全副苏式装备,一看就是中国人,在苏联军队中十分显眼。他们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举行了简单入城仪式,旋即开拔,向南进发,收复祖国失地。”
与中国人的光复之喜相对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这时候见到的王明贵将军。
中村回忆:“八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到。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注:王明贵实为卫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林管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洪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啊,满洲》第888页)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然而,也许中村的百感交集还有另一个原因。萨在采访居住于大阪的日本“归国者”(即战后滞留中国,后经两国政府协调返回日本的原开拓团成员)古川修时,听他讲起,1945年冬天,因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后还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引起苏军愤怒,切断了从哈尔滨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难中的北满日本开拓团成员大批徘徊于延寿、方正等地,由于无衣无食,那年冬天仅仅方正周围,因为冻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