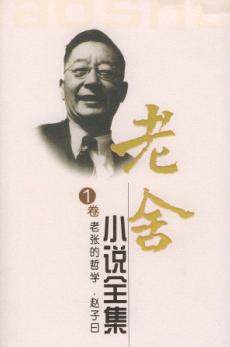长安古意 作者:掠水惊鸿-第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李成器听父亲说到这里,连忙起身道:“此事陛下当决与宰相。”李旦淡笑着拍拍他的手臂道:“这是咱们父子之间聊聊,你不必如此小心。凤奴,爹爹明白你的意思,你一直在竭尽所能避嫌,维护三郎的储位。可是京中的诸多谣言,仍是将你卷入其中,这才是爹爹最担心之处。”
李成器点头道:“臣有一言,一直惶惶不安,未敢轻吐。臣与几位弟弟,于平乱并无尺寸之功,仅仅以皇子身份,骤加高位领兵权,自古大都偶国乃祸之本源,还望爹爹早日下诏,将我们所领的军中职衔罢去。另外臣身领五千户封邑,与当日太宗所定的皇子实封不可过千户,实在逾制甚多。三郎仁明孝友,天下所知,立他为储乃上应天意下顺民情,陛下便不该因为臣辞位一事,对臣厚加封赏。”
李旦叹息道:“凤奴,你在这世上,有没有人,让你愿意竭尽自己所有,要保护他,为他带来平安、富足与快乐?”李成器一愣,他默默垂首,点头道:“有的。是陛下、姑母、几位弟弟,还有——花奴。”李旦目光柔和地望着儿子,道:“你的母亲不在了,对爹爹来说,这样的人便是你的姑母与你们兄弟。爹爹不是一个好皇帝,天子家天下,可是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仍只有这几个亲人。爹爹错过了抚育你的时候,现在只能用这些无用的田地、财富来补偿。你的姑母于我有大恩,她提出任何要求,我也无力拒绝。”他说到此处黯然顿了顿道:“现在想来,其实我与你三伯,也并无多大差别。”
李成器又是心酸又是惶恐,忙道:“爹爹,不是这样……”
李旦道:“我明白我的失职处,我的精神也不济,无力处置这许多朝政。我想过几日,就下诏让三郎监国,你看可好?”李成器道:“本朝素来有太子监国的先例,如此一来,太子名分既定,也可安三郎与宰臣之心。”李旦沉吟片刻道:“今早宋璟入宫,向我说了三件事。第三件与你方才所说不谋而合,他请我罢去你们的大将军之职,令隆范与隆业分别为东宫左、右卫率,既可辅佐三郎,也可免他们手中兵权惹人嫌猜。”李成器道:“宋大人此乃老成谋国之见,比臣所想的更为周全。不知另两件事是什么?”李旦望了李成器一眼,神情略含悲意,缓缓道:“他请我将你和守礼都外任刺史,将太平安置东都。”
李成器脑中如被一阵闷雷打过,一时嗡嗡作响,竟忘了换却神情,只呆呆与皇帝对视。皇帝心中一痛,道:“你不必怕,这两件事我并未答应他。”
就这一句话的功夫,李成器忽然将种种前因后果都想得清楚,对三郎威胁最大的是自己和身为太宗长孙的守礼,将他们遣出京城,便防止了姑母以他们为口实交构东宫。这同他留在东都不肯回来是同一个法子,为何他竟从未想到?只因他心中还有不舍,他刚才还在对父亲说自己别无所求,那是骗人的话,他唯一的要求,便是与那个人不离不弃。可是没想到,到了这一步,这要求也终于不为情势所容。
李成器深深吸了口气,清寒之气如一段寒冰慢慢插入他的肺腑,他只是诧异,为何这长安宫中早春,比洛阳的隆冬还要寒冷。他慢慢站起身,离座坐到阶下跪倒,向皇帝叩首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宋大人此三策甚是妥当,请陛下恩准。”
皇帝愣了愣道:“凤奴,这不是爹爹意思。”
李成器黯然一笑道:“臣知道,若是臣稍稍表露一丝留恋之意,陛下一定会庇护臣,将臣留在京师。可是在爹爹心中,定然也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自汉朝起,就令不曾立储的皇子就藩,以避免兄弟相争的惨剧。太宗皇帝曾因为私爱,将魏王留于身边,其结果也只是令其势欲熏心,做出无父无君的事来。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臣不愿因为……”他说到这里,仍是忍不住万箭攒心,颤抖着声音道:“仅仅因为臣的一己私爱,滞留京师,令爹爹为难,令三郎惶恐不自安,令朝臣无心理政,因陛下的游移不定,而陷入朋党之争。”他含泪抬头,强作微笑道:“爹爹,儿子并不用去很久的,过得几年,待朝上局势平静,臣还可以回来,陪爹爹焚香抚琴。”
李成器与父亲约好,这几日不可惊动太平公主。四日后朔日大朝,内侍宣诏:迁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改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安置太平公主与其夫定王武攸暨于东都。诏书尚未念完,便闻得朝班中一片窃窃私语。李成器当先出班拜谢如仪,李守礼忙也跟着出班谢恩,李隆范和李隆业尚在少年,骤然听得父亲如此重大的变动,都有些愣神,待李成器叩首已毕,才有些怏怏地出班跪倒。
朝臣们虽然各垂首站着,但都忍不住拿眼角去瞥御座旁的太平公主。孰料最先说话的倒是薛崇简,他又惊又怒之下高声道:“陛下,表哥从东都归来尚未满一月,您又要将他外迁,难道这京师,就无他一寸立足之地吗?”李成器心中剧痛,跪在地上,回首低声道:“亲王就藩,乃本朝成例,此番是我自请外迁,陛下恩准,是对我拳拳顾惜之情,立节王勿妄言。”
薛崇简胸中热血乱滚,他望着李成器匍匐于地的姿势,只觉心中痛楚到极处,屈辱到极处,他已经退到了无可再退处,还是有人容不得他。他交出了太子位,一次次卑躬屈膝,只为建筑一围小小的城垣,守卫着他们二人的胶漆不离,这城垣竟也不可倚靠上去。自己对他的眷恋,比起他心中君臣父子的大义,当真轻若飞烟,只待他人来吹一口气,便散入了茫茫天地中。薛崇简冷冷道:“天下岂有驱逐亲子的顾惜之情!陛下,请勿听人离间骨肉!”
宋璟见皇帝面上浮起悲怆之色,深怕他一时优柔寡断复又反悔,忙迈出一步道:“诗曰,大邦为屏,大宗为翰。以皇子出任刺史,既可拱卫京师,复可安定东宫。昔日魏武帝偏爱陈思王,几倾文帝,而魏武之后,陈思受祸,是爱之所以害之也。陛下以宗社为上,戒宋王蹈陈思覆辙,实乃大慈大爱之心。”
薛崇简本就在盛怒中,有人跳出来说话,立时反唇相讥道:“你以陛下比拟魏武,是讽刺东宫将为篡逆之君了?”他迈出一步道:“陛下,臣弹劾中书令宋璟毁谤东宫,请陛下严处!”宋璟情急下只想对皇帝动之以情,被薛崇简抓住这细微之处发难,也只得按照官员被弹劾的惯例,躬身上前跪倒,口称:“臣死罪!”
太平公主此时方缓缓起身道:“陛下,我想知道,是谁为您草拟的诏书。”皇帝见太平眼中隐有泪光闪烁,不禁面有难色,低声道:“太平,是我草率了,此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太平忽然提高了声音道:“臣妹只问,这诏书是谁写的!”
姚崇看不下去,扬声道:“公主逼迫至尊,礼仪何在!”太平冷笑一声,熠熠生辉的凤目缓缓扫过朝班,道:“是谁逼迫至尊,谁心里明白。”她望着皇帝,两行泪水倏然淌下,低声哽咽道:“四哥,我记得当年,二哥被母亲送往巴州,三哥被送往房州,都是你我送行……”皇帝听到这里,身子轻微颤抖,声音中含着求恳,道:“太平,你误会了,四哥不是要贬斥你……”太平静静望着皇帝,继续道:“现在只剩下你我了,四哥会为我送行么?”皇帝艰难道:“太平,你若不愿,四哥不会勉强你。”太平厉声道:“可是有人会勉强四哥!”她一指姚崇宋暻道:“是不是这两个人!”皇帝为妹妹的气势所迫,一时竟讷讷说不出话来。
太平望向李隆基冷笑一声道:“三郎,这诏书你事先也看过吧?”
李隆基苍白着脸色,望了望父亲泫然欲泣的脸,又瞥见两位弟弟愤愤不平的脸,知道此番已全军覆没。他用力一咬下唇,缓缓踏出班首,沉声道:“陛下,姚崇宋璟离间臣之姑兄,请从极法。”
作者有话要说:【1】继我毁了花奴写诗的水平后,这位“文质兼半”的皇子又被我糟蹋了。万幸是初唐时律诗还没兴起,格律不那么流行,我这处处唱破如马蜂窝的四句话,勉强算作诗(吧?吧……)。关于桥上看月的诗,我一直很喜欢两句,一句是元稹的“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一句是清代黄景仁“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都有种对整个时代的寂寞与忧虑。如是我就不要脸地化用了,化用的结果就如乾隆仿造的汝窑釉色,神行皆散。
75
75、七十四、楼前相望不相知(上) 。。。
皇帝终究没有做出任何决断便宣布退朝,李隆基只觉两耳被那退朝的鼓声震得一片片嗡嗡作响,朝臣们在身后窸窸窣窣地交谈,他却一个字也听不清楚。太平公主被皇帝扶着,似乎犹在低声啜泣,皇帝望着妹妹的神情是那般的和善。李隆基的身子有些发僵,他知道父亲身边的那些人,此时不会让自己与父亲相见,他却又实在无力转身,与姚崇宋暻相对,在群臣的众目睽睽下回到东宫去。
李成器走到李隆基面前,神情中带着歉意,柔声道:“三郎。”李隆基这才醒过神来,他苍白的脸色尚算平静,向李成器淡淡一笑道:“我心里明白,是我辜负大哥的好意了。”他深吸口气,转身快步略出朝堂,也不知是经过谁的身边,隐隐听到了一声冷笑,他咬着牙不曾回头去看。
李隆基被高力士扶着,踉踉跄跄回到东宫寝殿,元沅正和太子妃王氏坐在榻上下期,元沅的弈术还是被幽禁在东都那几年,跟着李隆基学的,太子妃是新手,还要向她讨教。李隆基不知为何,看到元沅头上金光闪烁的步摇,便猛然想起了姑母,上前呼啦一声将那桌案掀翻,数百颗美玉磨成的棋子滚了满地,如骤雨打浮萍般敲出一片悦耳之音。
太子妃吓了一跳,道:“这是怎么了?” 元沅一言不发起身,跪在地上将那些棋子一粒粒捡回盒内。李隆基随手将身上玉带摘下,狠狠掷在地上,回身坐在一张高椅上,沉着脸不语。太子妃也不敢多言,尴尬地立在他身旁,李隆基怒道:“还要我自己倒水来?”太子妃忙给他斟了一盏热酪。
不一时元沅将地上棋子捡尽,捧着木盒上前跪在李隆基面前,李隆基皱眉道:“你捡它作甚!”元沅低声道:“请郎君再砸。”李隆基道:“我为甚要再砸?”元沅垂首道:“郎君余怒未消,于其郁郁伤身,不如拿它出气。”李隆基向太子妃冷笑道:“到底是姑母教导出来的人,这份泰山崩于侧而目不瞬的本事,你还差得远。”元沅捧着盒子的手微微一颤,仍是不曾抬头,低声道:“郎君拿奴婢出气也可。”
到了这份上,李隆基倒不好发作了,他厌烦地挥挥手道:“都下去。”却随手将那玉盏递给元沅道:“再添。”太子妃怏怏地向他行了礼,带着几个内侍婢女退出,元沅回身将那盏酪浆递给李隆基。李隆基有些黯然地抚了一下那只手,低声道:“朝中出了些事——我没有疑你的意思。”元沅微微抿嘴,道:“我知道。”
太平公主来到后殿,虽在皇帝的劝慰下,兀自流泪不止。皇帝亲自在金盆中摆了手巾递给她,太平只是不接,皇帝无奈下只得将自己袖子递上去,道:“那用这个。”太平愣了一下,破涕一笑,两行泪珠却又滚了下来。皇帝叹了口气,道:“今日之事,来找我的是姚崇宋暻,既然三郎也请求处置他们,我将他们贬出京师,再将刘幽求迁为中书省,他们空出来的宰相之职,让萧至忠与崔湜、李日知来补,可好么?”
太平默然不语,过了片刻道:“我并未说要将萧至忠和崔湜擢为宰相。”皇帝摇头道:“萧至忠当年为你我鸣冤,我早有提拔他的心意。崔湜这人虽然有些好货的毛病,但他文字上强过姚崇,当文学之士用还是可以的。只是,你和定王……” 他说到这里,似有些难以出口,又顿了一顿,方道:“能先到蒲州去一阵么?那里距离长安比洛阳近许多,快马一日可至,传递消息也方便。”
太平颤声道:“原来四哥先礼后兵,还是要将我驱除出京。”皇帝扶着她的双肩道:“阿月,你不要误会。这不是贬斥,只是眼下我贬了姚崇宋暻,是对东宫极大的打压,也许现在动摇东宫的谣言已经传遍整个长安了。张说有句话是对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储君安方能天下安,我也不能令三郎惊惧过甚。你去蒲州,只是避一避风头,你的几个年幼儿女,可以和你同行,大郎和花奴,在朝中都身居要职,他们就不必动了。四哥向你保证,你不在的日子里,朕凡事皆与萧至忠崔湜商议,军国大事也派人去蒲州垂询你,三月之内必然招你回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