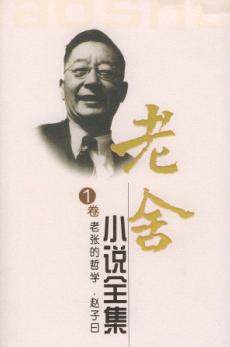长安古意 作者:掠水惊鸿-第9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开来。有时李成器抄完一段,提笔濡墨,就不经意地侧首与薛崇简对望一眼,他们心中都觉得眼前这灯光,这书墨的清香,都如这纸上佛家的般若之音一般,慈悲美好到了极处。所谓西方极乐,并不在霞光遍布的天边,这再普通不过的读书写字,却又脱却了尘世一切愁烦,足以造出一室之内的极乐来。
李成器低头抄了许久,终于听到清晰而遥远的咚咚的鼓声,如连绵的波涛一般涌来,便是每日昼漏尽时六街上擂起的宵禁鼓。不急不躁的一千声街鼓响毕,所有的市坊大门将要关闭,商贩行人必须归家,他们这样温情的灯光,也将在千家万户的窗内亮起。李成器转动酸痛的腕子,回头一望,薛崇简还未睡着,仍拖着腮,眼睛盯着一页书久久未动。李成器微笑着揉了下他的头发道:“看什么呢?”薛崇简指着书上一处道:“这里真像在说你。”李成器这才低头看去,原来他随手拿的是一本《四十二章经》,手指处那句话恰是:“人随情欲求华名,譬如烧香,众人闻其香,然香以熏自烧。”
李成器沉思一下,却不料这句话自己幼年便读,今日被他骤然找出,竟是从未想过的贴切。他也不答话,拿着薛崇简的手,又向后翻了两页,指着另一处给他看,却是一句:“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
薛崇简呆了呆,随后将那经书向一旁丢过道:“那还看它作甚。”李成器笑得一笑,道:“你能起身么?”薛崇简道:“你要做什么?”李成器道:“不知为何,方才听着那漏鼓之声,忽然极想看看,这时候天津桥上月色是怎样。”薛崇简道:“你怎不早说?这会儿宵禁了,没有军国之事不能开坊门的,万一被哪个愣头青巡夜抓住打一顿板子,你这亲王就没脸做了。”李成器被他说得一笑道:“罢了,我也是随口一说。”
薛崇简忽然翻身起来,道:“走。”李成器怔了怔,道:“不必了。”薛崇简笑道:“自从舅舅赏了这个郡王封号,还没狐假虎威过,索性放肆一回,我也想看月色,且看看有谁敢拿咱们。”李成器望着薛崇简灿若明星的双眸,渐渐也露出一个舒缓的笑容,道:“晚上风凉,你加件半臂。”
作者有话要说:【1】中宗将洛阳的河南县改名为合宫县,应天门与明堂皆属于合宫县。
74
74、七十三、专权判不容萧相(下) 。。。
李成器与薛崇简出了府门,薛崇简不便骑马,他们所居的积善坊距离天津桥也就是一坊之隔。两人只携手步行。薛崇简怕路上遇着歹人,还特别带了一把短剑,果然刚一到坊门前,便被巡夜的守卫拦住,两人并未隐瞒身份,守卫深更半夜碰上现今洛阳城里最大的两位殿下,且是一个侍从不带,白龙鱼服便跑到了街上了,颇有些疑惑。好在此处距离洛阳宫牛千卫的官署极近,立刻有守卫飞骑请来千卫将军,那将军识得李成器与薛崇简,连忙开门放行。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安静的洛阳城。
他们从积善坊一路向西行,隔着一条洛水,可遥遥望见对面的洛阳宫,巨大沉默的宫殿,轮廓均被夜色模糊,唯有宫城上悬挂的绛色灯笼甚是醒目。便如只用朱砂与浓重墨色泼出的巨幅图画,遒劲峻峭,并不因隐去了雕梁画栋,而丧失了威严。
这座晨钟暮鼓、井然有序的古城陷入了沉睡之中。河道中的流水宛若有人拨动轻柔的箜篌,并不觉得嘈杂,只絮絮地在耳旁反复叮咛。偶尔传来几声隐约的马蹄和梆子声,他们不曾看到,但可以想象巡夜的差役纵马在空旷无人的街市上奔驰而过,年老的更夫沿着墙根,敲打出枯燥却又绵长的调子。这些声音交融在一起,便显出某种奇特的韵律来,这乐曲无人去认真欣赏,却又一日不可缺少地飘入这座古城每户人家的梦境,告诉他们一切平安,无水火之患,无盗贼之恐,他们翻身安然睡去。
天气已入秋,夜风虽然清冽,却并不冷硬,似乎还带着从洛河上飘来的濛濛水气,吹拂面上颇觉湿润。空中的一轮明月尚缺着一牙儿边,好在天清似水,月明星稀,清光投射在青石板路上,恰可在朦胧光芒中辨认出路径。李成器与薛崇简所着的缭绫长袍上的暗纹,竟也被这清辉照耀得闪烁出一点点的光泽,那月光便似也化作了实质,顺着他们的衣袖袍角流淌而下。
李成器与薛崇简半生都居住在东都,一年中却也只有上元时能有三日不宵禁,深夜得以走上街头看灯,但那几日家家户户也都聚于街头,游人摩肩接踵,火树银花宛若白昼,从未见过如此安静的月夜。两人被这份巨大空旷与静默震动,如佛前顶礼,竟无人敢出声,只携着手默默前行。待走到天津桥上,看到那一轮明月在桥两边各投一影,上下左右相互映衬,夜光如水,水亦如天,偏偏又都有月,他们便是被如此清澈的天河环绕。
薛崇简靠着白石阑干,极目远处那朦胧起伏的北邙山,忽然想起那句“清光到死也相随”的歌谣,他望着李成器,听着潺潺流水,望着桥下月影,心中竟也升起年华随水而去的感慨来。薛崇简伏在石栏上,低低一笑道:“还是那一年上元,我把你从推事院接出来,在城外看的邙山。那时候就想,若是你死了,我就带你上邙山去,再也不下来。”李成器从后边拥住他,低低吟道:“九衢茫茫漏迟迟,年光潜从流水知。天津桥上无人识,唯有星月似旧时。”【1】
薛崇简回头一笑道:“是你自己舍了这河山,又发什么‘无人识’的牢骚?”李成器微微一笑,道:“你是不是觉得表哥太没用了些?”薛崇简摇头道:“我其实并不盼着你做太子,小时那个宋老头讲的道理,让人听着又害怕又心疼,若是都要按着他说的去做太子,这辈子也就没什么活头了。可我怕的是,你让出了这江山,到头来反弄得自己连容身之处都没有。”
李成器淡笑道:“我在自己的弟弟面前行个礼,将他的名字置于我之前,你便觉得这很委屈?”薛崇简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李成器道:“花奴,你大概觉得我此生经历诸多磨难:半生闭于宫中,失去了母亲,与父亲相隔,身为帝胄而遭际若此,实在算是凄惶到了极处,对么?”
薛崇简黯然道:“我们一大家子,谁也好不到哪里去。”李成器点点头:“五十年来帝室变迁,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万幸我们两脉尚得以保全,这要仰赖姑母的智慧,和我爹爹的隐忍。其实当年我也一度诧异,为何一个匡复李唐的机会摆在面前,爹爹却不肯离去。后来我被幽禁的日子,看了些北魏朝的事,才忽然完全懂得了,爹爹为何肯将所有的苦楚都忍耐下来。”
薛崇简道:“你说北朝那些乱七八糟打来打去的事么?”李成器道:“他们虽是胡人,但心性与我们并无两样。孝文帝迁都洛阳,不过一甲子间,洛阳城竟被兵灾屠了三次。起因是胡太后的专权,是帝室内叔侄兄弟相争,君臣相残,这座繁华城市匍匐于刀兵之下,每一次战争过后,人民都会折损十之八九,再经隋末一场洗劫,到了贞观初年,魏征说,洛阳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花奴,你想想,十之八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十口之家,只能有一人存活,是可能在一夜之间,夫丧其妻,母失其子。我们的阿翁用了二十年,才重新建起这座城市,可是那些活下来的人,却一生都无法忘记丧亲之痛了。那才是真的苦难,真的地狱,比起他们,我受的那些苦楚与委屈,又算什么。”
薛崇简没有答话,李成器顿了一顿,接着道:“即便是当今太平年间,这普天下还有许多人,丰年仅仅可得温饱,凶年不免于死亡。我这二十余年,除了几次波折,也算是衣食无忧了。我能做的,仅仅是端正自己的言行,让百姓们相信,天子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欲而驱使百姓去征战,不会打破万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花奴,三郎或许略有倨傲,但那只是对我一个人,并不妨碍他成为怀保小民的明君。这世上没有比战乱和苛政更可怕的灾难了,这种灾难不是落在某个人身上,它会毁灭一整代人的希望。我受了天下万民二十余年的供养,至少要让我自己,不能成为这灾难的缘由。”
薛崇简靠在李成器怀中,只觉他说到激动处,身子都微微颤抖。薛崇简不知为何,望着那天水之中的明月,视线中竟也微微起了涟漪,他点点头道:“我懂得,你的心愿,我都懂得。”
————————————————我是还想打花奴的分割线……
李成器与薛崇简在洛阳一住半年,待肃明皇后与昭成皇后的惠陵与靖陵竣工,他们返回长安,已经是一年将尽时。返京之后便是忙忙碌碌的除夕与上元大节,今年是皇帝登基后第一个上元节,虽然皇帝天性不喜喧闹,却依旧要做足除旧布新的架势来,上元休沐三日,由太平公主和皇帝的两位妃子捐助脂粉钱,在长安城内设三日花灯会,天子一家人坐于承天门上观灯,与民同乐。李成器第一次过如此忙碌的节日,身边总是被人群环绕,耳畔永远有人说话,疲惫中带着恍惚,全无一点欢喜之意。
到了十六日,因还在休沐假内,并不上朝,各位皇子皆回归府邸睡觉。因整个大节都不曾好睡,昨晚又熬了通宵,李成器睡到午饭时候方醒来,头脑中犹有些昏沉,连骨头里都生出一股酸意来。他望着帘帷出神,想起回京后所听闻的一切,心中便不觉复又沉闷。
虽然归来的日子短,但也够他了解许多事,成义告诉他,如今父亲聆听宰相奏事,总是先问:“与太平议否?”再问“与三郎议否?”而姑母所奏,父亲无有不听,半年来由姑母举荐而骤登高位的官员已不可计数。数日前听说姑母在光范门邀见中书省几位宰相,暗示陛下将易置东宫,宋璟抗言道:“东宫有大功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最后诸人不欢而散。前几日,更是有天宫寺中僧人进言,说五日内将有急兵入宫。诸般传闻令李成器心惊不已,以至于太平屡屡招他过府,他竟不敢前往,只得以诸般杂冗事推脱,花奴还抱怨一回家,两人倒连见面的功夫都没了。
李成器出了会儿神,听见外头王妃元氏轻叩屏风,柔声道:“殿下醒了么?宫中来了中使,说陛下传请殿下。”李成器慌忙起身更衣,王妃亲自端来银盆为他盥洗,见他穿上公服就要出门,忙道:“天寒,妾备了些酒馔,殿下用一口再去吧。”李成器略带歉意地一笑道:“不敢让陛下久候,你们吃吧,莫等我了。”元妃送他到门口,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怔忡了一阵,才缓缓返回室内,坐在妆台前将头上步摇一支支拔下。阿萝诧异道:“娘子大早上起来,为梳这髻子费了一个时辰,怎么就不戴了?”元妃淡笑道:“怪沉的,在家又无人看,戴这些做什么。”
她尽量使得自己的语气从容些,像说一些全不萦怀的事,可是她仍是禁不住呼吸有些急促,镜中的女子身披金线织锦帛帔,面上的脂粉花钿绮丽华美,却将少女的清秀容颜尽皆遮掩。她心下有些恍惚,她做女儿时是什么模样,她自己都不甚记得了,她只知道,无论是素颜还是艳妆,她的任何模样,那个人都看不见,也不欢喜。从大婚之日起,她看到的就是他的背影,那背影从未为她回首。
李成器一路骑马,见满地散落的都是昨晚的花灯残骸,天街上有年老的兵丁在将这些残骸扫去,除此外便空旷寂静,只剩自己的马蹄踏碎这一地冰霜。他心中有莫名的空虚,他并不艳羡昨晚的繁华,可是这繁华过去,仍是让人生出盛景难再的凄凉与孤寂。
他来到武德殿皇帝寝宫,想来皇帝也是起身未久,只着了一身家常穿的圆领长袍,见到他温言道:“你从洛阳归来,我们父子还没有功夫坐在一处说说话。想来你也未用午饭,便传了几个清淡菜肴,你陪我用些吧。”李成器拜谢了皇帝的恩典,便上前坐在皇帝下首,两人闲话了几句今年的灯节,皇帝便叹了口气道:“你姑姑和三郎的事,你有耳闻吧?”李成器不妨父亲开门见山便说到这里,心下骤然一紧,含糊道:“约略听说了些,并不详尽。三郎与姑母都是心性倨傲之人,或者一时误会,还望陛下兼顾调和。”
李旦怅然一笑,叹道:“你姑姑与社稷有大功,可是我除了将她的封邑加到万户,并无别的方法报偿她。她想要将自己的几名亲信置与朝堂,我不能拒绝。三郎经过则天一朝,对女子擅权一事深恶痛绝,也无可厚非。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李成器听父亲说到这里,连忙起身道:“此事陛下当决与宰相。”李旦淡笑着拍拍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