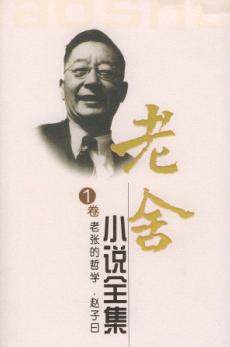长安古意 作者:掠水惊鸿-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报复了他的子孙,却依然无法战胜他一手缔造的李唐盛世。
贞观之治给长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尊严与骄傲是如此强烈,五十年光阴洗去了当年为了开疆拓土洒下的征夫血,思妇泪,剩下的只是那份传说中光耀万丈的繁荣昌盛,成为民众在苦难中最易触动的梦想与期盼。即便李世民的两个孙儿一个无能一个懦弱,在天下臣民乃至域外蛮夷的心中,亦是龙章凤姿的天之骄子。而她一手创建的帝国根基,终于被武懿宗之流的浅薄骄横、残忍无知挥霍殆尽。
女皇默默放下了珠帘,原来一世努力,一世决绝,到头来亦不过是落叶归根,仍旧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自永宸元年大帝与天后迁都洛阳,一众王公与大臣们皆是举家定居神都,这次贸然伴驾西归,自有一阵忙乱。待收拾好了太极宫与大明宫,安顿好了诸王府与诸大臣居所,已到了长安元年的三月。
女皇任命相王李旦知左右羽林军事,同时出任雍州牧,护卫京畿之地。李旦二十年来从未染指军政,此番却知道母亲将如此大权交给自己,是为了防止他日太子继位时诸武造乱。他感激之下亦知事关重大,平生头一次为朝政奔忙,他忙不过来时便只能借助儿子们,除李隆基镇日穿梭与军营外,连李成器都由薛崇简陪着,时时入羽林军查看京畿防御。
四月初八浴佛节,今年女皇似是比往年疲惫许多,并未安排盛大佛事,只是点了太子李显、皇太孙李重润、相王李旦、寿春郡王李成器四人陪她入寺礼佛一日。
因着朝休,临淄王李隆基终于得了一日清闲,他回到长安已经两三月,日日忙得睡不到三个时辰,做事时倒也不觉得,一旦歇下来,才发觉浑身骨头乏得发酸。早上去了一趟军营,回来略用了些点心倒头就睡,醒时已到午后。他睁开眼来,屋内只元沅一人,坐在榻桌边低头缝补着什么。此时天气渐渐变热,元沅只着了一件窄袖罗襦,李隆基歪在枕上看着她细细腰肢,笑道:“做什么呢?”
元沅见他醒来,回头抿嘴一笑,道:“殿下这几日总是骑马,这条裤子昨日才穿的,腿上就磨出个洞来。”李隆基笑道:“破了换条新的就是,这样的事还轮到你做?”元沅怔了怔,当日洛阳宫幽禁中,一应供奉用度捉襟见肘,李隆基的衣衫开线或破洞,皆由她来缝补,做得惯了,却忘了现下李隆基已是显贵郡王,并不在乎几件绫罗衣裳。她望着那补了一半的破洞,本该是为他欢喜的,却不知为何总是有些怅惘失落,低头咬断那根线,将一团绒线轻轻唾在一旁,淡淡应道:“我闲着也是闲着。”
李隆基翻身起来,揽住她腰身,笑道:“你这些日子也闷了,去换身衣裳,我带你进宫打球去。”元沅笑道:“奴婢哪里会打球。”李隆基笑道:“你已经会骑马了,打球不难学,今日难得有空,正好教你。听说含元殿后头的球场已经修好了,我还没工夫去看看呢。”元沅心中虽然十分欢喜,却道:“殿下累了这么数日,还不歇歇么。”李隆基笑道:“刚才睡了一觉,已经轻健了许多。放心,我身子骨儿好着呢,若是这点小事就累趴下了,怎么应付来日的大事?”元沅嘴唇微微一动,她凝望着李隆基踌躇满志的俊朗面容,心中隐约的忧虑,也只得压下了。
李隆基让元沅换了一身小宦官服色,自己亦着了打球的短衣,也并未带随从,就从弘文馆左侧的偏门入大明宫。今非昔比,他在羽林军中身居要职,自有权力出入宫禁。元沅却是第一次进宫,一路上见亭台掩映,殿阁高耸,杨柳飞棉作雪,秾花落红成霰,虽是极力压制,仍是禁不住满脸兴奋,一双眼睛已不够用,时刻东张西望。李隆基望着明媚日光映在元沅娇嫩脸上,将少女肌肤照耀得如同透明,自己一颗心似也要随着那杨花直上青云,他牵着元沅的手慢慢行走,为她讲解宫殿名字及宫中趣事。
绕过了含元殿,便来到殿后的一大片空场,元沅深吸了口气,惊道:“这么大?”李隆基含笑道:“陛下设立了北庭都护府,下个月吐蕃的使者就要来朝了,那些人皆是马背上长大,善于击球,已放出话来,要和我朝儿郎们比试一场。要不太极宫还没修好,陛下便赶着让定王亲自督工,修好了这个球场。你看见那地面了么,一般的土地哪有这般平整光亮?那是给土里掺了油,再用千钧巨碾碾成的。”元沅咂舌道:“给土里掺油?修这一大片地方,得花多少钱啊!”
一个守卫球场的内侍看见他们过来,连忙迎上来道:“这位大人,此处是皇家禁园,还请止步。”李隆基身上未服王服,又是头一次来这里,这内侍不认得他,倒也不甚奇怪,笑道:“我是临淄王,你们这里的马可驯好了?牵两匹出来,我试试。”
那内侍忙跪下行礼,起身后却道:“殿下巡查球场,可有宅家旨意?”李隆基一愣,道:“我来打两杆球,还需请旨么?”那内侍赔笑道:“殿下见谅,马倒是驯好了,只是厩中皆是御马,没有宅家旨意和定王手书,奴婢们不敢私自供殿下使用。”
李隆基本不过是想带元沅玩耍一场,却不料打个球还要请旨,眼中掠过几分愠怒,冷冷道:“这场子是定王家的?他能来,孤王不能来?”见他动怒,那内侍腰身又低几分,语气中无甚惧意,解释道:“殿下息怒,是宅家命定王总管这场子,定王交代,这场子临近正殿,需防有闲杂人等惊扰圣驾,奴婢们不敢抗旨。”
李隆基脸色一变,胸口微微起伏,他这两月在军中奔忙,所到之处皆受礼敬,再想不到这宫中一个低贱宦寺竟敢慢待他。他在元沅面前,越发难忍下这口气,正待发作,忽然听得身后一阵杂乱笑语,回过头去,正看见薛崇简带着羽林中一票少年谈笑着过来,他们皆是深蓝劲装,纯黑短靴,手上带了护腕护掌,各执着球杆,一望而知是打球的装束。李隆基难得不见薛崇简和李成器在一处,想来也是李成器今日侍奉皇帝礼佛,薛崇简才来此处玩耍。
薛崇简见到李隆基一怔,随即笑道:“三郎也在,早听说你球技好,今日正好比试一场。”方才那内侍脸上如开出了花儿来,两三步趋迎上去,先恭恭敬敬向薛崇简扣了头,笑道:“郎君可算来了,您交代了给您驯马,奴婢们日日拿精燕麦喂着,那马跟奴婢们一般,都望眼欲穿了。”薛崇简笑道:“我近日太忙,好容易今日才得闲。我让你驯马,又不是让你养猪,你要是糟蹋了我的汗血马,当心我宰了你。”那内侍笑道:“糟蹋不了,糟蹋不了,那马雄健着呢,截了马尾后更精神了,别的马见了它都不禁得矮三分,也只有郎君您才配骑这样的神驹!”
薛崇简一笑,他身后少年杨慎交亦是勋贵子弟,随手丢两粒金珠给那内侍,笑骂道:“赶紧牵马去,少在这里胡白!”那内侍忙笑道:“是是。”回头对跟来的几个内侍吩咐:“还不快牵马去,找最好的牵!”
李隆基在旁默默听了一刻,忽然转身就走。薛崇简好不诧异,在后喊道:“你不玩么?”李隆基冷冷道:“我还有事。”
元沅早看出李隆基脸色不对,明白他的心事,暗暗叹了口气,连忙小跑着追上去。李隆基虽听见元沅在后边微微喘息,却无法慢得一刻,方才薛崇简脸上那春风得意又漫不经心的笑容,如一记警钟般砸在他心上。他终是将人心想得太过简单,他以为回到长安,这皇宫、这天地便重新归于李氏。那个内侍卑贱的笑容让他刹那间看得如此清楚,虽然武氏式微,但女皇仍是女皇,太平公主仍是太平公主,这皇宫仍是掌握在他人手中。
他们走至昭庆门的石桥上,忽听得身后有人喊道:“殿下!临淄王殿下!”李隆基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见是个内侍气喘吁吁奔来,他略一蹙眉,待那内侍连滚带爬扑倒在自己足下叩首,才淡淡道:“你是哪个宫门的?”
那内侍喘了几口气,才磕了三个头抬头道:“回殿下,奴婢是在含元殿球场当差的,叫高力士。”那内侍不过十七八岁,跟李隆基年岁仿佛,一张脸生得白净机灵。
李隆基听他提到球场二字,心头怒火又起,哼道:“你唤我何事?”高力士道:“殿下息怒,方才那人是太平公主府上出来的,眼睛长在屁股上了,只认得太平公主家里的人。奴婢唤您,是想请您移驾麟德殿的球场,那里是奴婢的干爹管着,马不比含元殿的差,还比含元殿清静,您同这位……”他看了元沅一眼,道:“……这位贵人,正好玩耍。”
元沅脸上一红,高力士显是看出了自己是女儿身,才将中贵人改称“贵人”。李隆基嘲讽一笑,道:“麟德殿亦是宫内禁园,我没有请旨,你敢开场?”高力士笑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天下一尺一寸,一草一木,皆是殿下家的,还有殿下不能到的地方吗?”李隆基抚着桥上汉玉栏杆,用力攥住栏杆上的麒麟首,冷笑道:“这天下是宅家的天下,你口出大逆之言,不想活了?”高力士倒不慌乱,一笑,轻声道:“试看今日城中,竟是谁家天下。今日这今日,与昨日那‘今日’不同了。”
李隆基神情微微一凛,不料这个小小宦寺,竟能诵出当年骆宾王檄文中的句子。他抬头向含元殿望去,恢宏宫殿高峙半空,殿顶琉璃瓦被春末夏初的浓郁阳光照耀,反射出的竟是粼粼金光,整座宫殿便似是用黄金铸就。他知道这彩栋画梁每一寸都贵比黄金,皆是用民之膏血支撑,唯独如此,身处其中,才有睥睨天下的骄傲;他亦知道这脚下每一寸土地,皆是开创江山的祖辈英雄们用鲜血浸润,他们的血和敌人的血融于一处,滋养了这宫中繁花绿柳,唯独如此,才会让人不惜用性命去守护这片土地。
李隆基复又低下头侧目昵了跪着的高力士一阵,淡淡一笑道:“好,孤王随你去。”
到了五月中,送走了吐蕃倭国的使者,朝中诸事才渐渐安稳下来。李成器和薛崇简终于得了些闲暇,那日一早,两人便骑着马出城,逆着渭水一路西去,游览长安郊外风光,到了午后马至渭城。渭城亦称咸阳,原是秦朝都城,千载而下,当年阿房宫的胜景早付之一炬,李成器与薛崇简寻访了半日,也未曾寻到半片残砖败瓦。
李成器颇为遗憾,便又策马转到渭桥。此处是西出长安的必经之路,多聚集着送行之人,虽已到夕阳西下时也未全散去。远远望去桥头茵茵碧草上铺设了许多毡垫,众人或饮酒赋诗,或折柳相赠,亦有人负剑牵马,却在桥头逡巡不前。夏初之际,桥边数百株杨柳生长得精神挺拔,长条拂堤,与岸边蒹葭缠绵相攀。此时日光已略西斜,照耀得桥下渭河水波光粼粼,如整条天河的繁星洒落人间。这金缎般的长河延伸出去,是大片苍茫原野,消失于云中的巍巍高山下。
李成器凝望着西北方,轻叹道:“原来汉家陵阙,只剩下这一座渡桥了。”薛崇简笑道:“若是将来我要带兵出征了,你也来这里陪我喝一杯。”李成器望了他一眼,笑道:“你何时也染上这等边塞癖?”薛崇简笑道:“我在军中挂着衔儿的,将来国家有事,总该出去看看,也不能就在深宫皇都吃一辈子闲饭。”李成器笑得一笑,薛崇简少年意气,走马游猎之余,自然对塞外怀着向往,战场凶险人命惟危原不在他思虑中。李成器微微一顿道:“若将来你真有西出长安的一日,我不会在桥下替你践行。”薛崇简倒是一怔:“嗯?”李成器接着轻声道:“万里关山,我自是随了你去。”
薛崇简胸中一热,自去岁两人去了那层隔膜,李成器虽仍是一贯矜持,偶尔背人处,亦会吐出这等深情言语。他策马凑近李成器,离得近了,才看清他唇上微微渗出细密的汗珠,愈发衬得双唇若点朱般红润。他心跳忽然加快不少,强自按捺住,笑道:“人家都是来送行,满腹的断肠悲怆,咱俩太碍眼了些。跑了这半日马也渴了,寻个清静所在饮马去。”
李成器便也随着他调转马头,顺着渭水向东,渐渐行至一处偏僻的分叉水路,虽比渭河狭窄,水流却清澈如镜。更喜的是两岸皆有杨柳掩映,便如拉起两扇绿色帷帐,李成器下了马,将马匹交给施淳去下游饮水,便随意依着一颗柳树坐下。四下里青草微涩的香气被流水氤氲开来,不知从何处传来莺声鹊语,除此外便只剩流水如弦。李成器适宜地闭上双目,忽觉得面上一热,口唇已被薛崇简吻上,他吓了一跳,慌忙推开他,倒:“有人看见的!”薛崇简笑着张望一圈道:“哪里有人?”李成器面上甚热,低声道:“施淳就在。”薛崇简笑道:“他看不到。”李成器却不敢如此大胆,硬是推开他道:“这里时常有人经过,你不许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