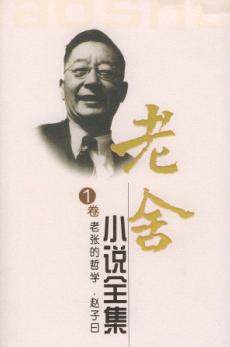长安古意 作者:掠水惊鸿-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人抬起头,虽是内侍打扮,却身形魁梧,鼻高目深,与中原人破不相同。李成器本来只觉得这人声音略有些耳熟,此时借着微弱灯光,觉得此人容貌和绥子有二三分相同,心下一震,压低声音道:“你……你是阿史那可汗!”
阿史那元庆淡淡一笑,牵起李成器的袖子道:“殿下好眼力,臣来护送殿下进东宫。”李成器将自己袖子从他手中夺过,他已看出事情远不似绥子说得那般简单,范云仙本就是内侍,让他探视父亲还说得过去,派一个外府将军进宫已属蹊跷,此时又忽然多了一名左威卫大将军兴昔亡可汗,他声音略有些颤抖:“我不过拜见父亲,有范将军二位足矣,何以竟劳动可汗大人?可汗是否可以告我以实情,你们要见我爹,究竟是所为何事?”
元庆道:“东宫周围遍布眼线,此地不宜说话,进去了臣自会对殿下与皇嗣说明。”李成器急道:“不!你不说清楚,我不能带你进去!我不能遗危君父!”元庆深深望了他一眼道:“臣对高皇帝之心,可鉴日月。臣此来正是为了救皇嗣与殿下,殿下若不信臣,现在便可回头。”他又一躬身,竟是径直往东宫走去。
李成器将李昭德、绥子、阿史那元庆、白涧府、北风其凉在心中一碰,脑中嗡一声响,一个念头模模糊糊爬上来,却是不敢相信。眼见元庆的背影如山如岳,心中一阵急痛,此时箭已离弦,他无法回头了,只得咬咬牙跟了上去。
李旦静静趺坐在蒲团上,室内并未点灯,只佛前的香炉从镂空的银罩中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光亮,照在他清俊的面容上。他早就以为这一点冥香当尽,静静地等,静静地,等了这许久,等他的世界沉入纯粹的黑暗中去,那一点微光却仍是固执地闪动。便如一颗不死的人心,无论如何拼命压制,如何风欺雪压,总是断不了牵绊、思念、执着。这便是佛家所说的贪嗔痴恋恨,爱别离与求不得。
豆卢妃提着裙裾,轻轻地走进来,叹息一声,走到佛像前,拿净瓶往手心里倾了些水,这才揭开香盒的盖子,又取出两撮香添入,用铜箸将火光拨得亮了些。瑞烟袅袅上升中,是佛祖慈悲的眉目静望人间,豆卢妃顶礼合十,望了一阵,忽然鼻尖发酸,悄悄用指尖弹落泪珠,回身在李旦身边跪下道:“殿下,安歇吧。”
李旦道:“你礼佛也有数年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句怎么解?”豆卢妃道:“过去事瞥然已过,若追寻之,无有处所,了不可得;未来心妄有畅想,全然无法定夺,了不可得;现在心一刹那百念丛生,刹那不可住,刹那不可得。”李旦指着佛案下铺着的帷帐上所绣的一只凤鸟道:“你说,那是过去心,现在心,还是未来心?”豆卢妃心中一颤,这才想起,那帷帐还是当日刘妃所绣,因已用得数年,眼中见得惯了,倒忘了它的来处。她知李旦思念妻儿,心中酸痛,靠在李旦肩头哽咽流泪。李旦反是轻轻笑了出来:“才教导过我,你自己倒看不透?莫要哭了。”
忽然一名内侍匆匆进来,面带惊惶神色道:“殿下,寿春郡王……来了!”李旦脸色一变,手在地上一按霍然站起,大步向外冲去,正赶上李成器向内走,两下里目光一碰,李成器但觉自己一身都软了,不知是悲是喜,向前踉跄两步跪倒在地,膝行上前抱住李旦双腿泣道:“爹爹,爹爹,儿终是见到你了!”
李旦顾不得其他,用力扳开他肩头,急急呵斥道:“你来做什么?可有至尊旨意?”李成器满面泪痕,不及回答,只问道:“爹爹,我娘在何处?”李旦脸色更沉,声音有些哆嗦:“你……你是擅自入宫的?你快出去,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李成器望着父亲脸色,只觉心底那一点点漂浮的希望也被一个浪头打入海底,肺腑之间痛得浑身痉挛,颤声道:“难道……真的如他们所说一般,娘和窦娘子都已经……”他只盼望父亲说些什么,或是安慰他一句,或是斥责他也好,李旦却只是呆了呆,低声道:“我不知道。”
李成器心中痛得两眼发黑,忽而一股腥甜从口中冒出,身子也瘫了下去,惊得范云仙和豆卢妃一起来扶。李旦这才看见儿子身后跟着三个人,指着他们道:“你们……是谁?”范云仙望了李旦一眼,轻声道:“奴婢是服侍过大帝的内侍范云仙,殿下,里边说话是否清净些?”李旦心乱如麻,点了点头。元庆扶起李成器,跟着李旦进了佛堂,豆卢妃就留在外间守望。
进屋后李旦让他们将李成器放在蒲团上,亲自点起一盏灯,元庆三人才正了正衣裳行大礼跪倒,叩首道:“臣阿史那元庆、臣白涧府薛大信、奴婢范云仙叩见皇嗣殿下千岁。”李旦并不转身,一拂袖子道:“我不知你们来做什么,你们若还念在先帝待你们的恩义不薄,就快带我儿子出去。”
元庆与范云仙对视一眼,范云仙膝行两步道:“殿下,武氏诸王无一日不谋算戕害殿下,两位皇妃被人所害,殿下已成危若累卵之势。我等正是不敢辜负先帝恩义,这才冒死入觐,若是能救殿下脱困,我等死不足惜!奴婢已与元庆可汗安排好一切,这就请殿下与寿春郡王火速出宫,西突厥的诸位英雄儿郎当护送殿下先到白涧府,就在冀北举起兴唐旗帜。天下士庶思唐久矣,殿下登高一呼必然从者云集。到时外有西突厥数万雄兵,内有李昭德等故旧大臣,殿下何愁宗庙不复!”
原来如此,李成器终于明白,李昭德那首北风,不仅仅是告诉他事已危急,而绥子要他入宫,也不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
李旦的手微微颤抖不住,回身厉声喝道:“住口!”他深深吸了口气,走到李成器面前,喝问道:“是你带他们进宫的?”
元庆膝行上前,从容道:“殿下,此事寿春郡王亦不知情。”李旦这才举目望着元庆正色道:“阿史那元庆,你的镇国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皆是至尊所封吧?大周也罢,大唐也罢,皆是我汉家事,你为何要参与其中?”元庆静静望着李旦道:“臣虽是胡人,却懂得‘忠者一也’。我西突厥当日降的是大唐太宗天可汗,不是大周武皇。殿下所说的私心,臣不是没有,臣助殿下成事,他日殿下当放臣归故土。”
李旦心知阿史那元庆之父阿史那弥射对太宗皇帝忠贞不二,叹了口气道:“我是幽闭百废之身,做不了你们的大事,你们不要再说了,快带着我儿子去吧。”
范云仙叩首泣道:“殿下!殿下,现在庐陵王被废,生死未明,大帝只剩殿下一脉遗息,宗庙社稷,尽系于殿下一身。殿下若走,成与不成,总能保全李唐血胤;殿下若留,则诸位郡王皆为覆巢之卵,殿下难道忍心看他们重蹈两位娘子覆辙吗?”
李旦慢慢走到李成器身边,揽住儿子肩头道:“纵然武氏诸王不肯罢手,也不过我一家之不幸。我若随了你们去,则是千万黎民破家亡身,中原大地流血盈野。何况子反其母,天理不容,我做不来。”
元庆万万想不到,他们拼了性命来救李旦,李旦却不肯走,急道:“殿下,臣听说过一句话,小慈乃大慈之贼。李唐中兴之望系于你一身,你便不能囿于区区母子之情!当今皇帝鸩杀你两位兄长,贬斥庐陵王时,可曾念过母子之情么?”
李旦沉默片刻,一字一顿道:“吾不敏,却有三德,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他淡淡一笑,道:“我今日亦或是对列祖列宗犯下大罪,却也别无他法。”
李成器不知为何,听到父亲做出这样决定,反是有种放下重负的释然,他挣扎着跪起身子,道:“吾从君父。”李旦爱怜地拭去他嘴角血迹,道:“傻孩子,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
作者有话要说:也许有人觉得李旦傻,但在我看来,在那个无法两全的时代,他是对的。
25
25、二十四、廷尉门前雀欲栖(上) 。。。
李成器从宫中出来,李隆基便也得知母亲罹难,五王宅中一片哭声。许是李成器在父亲那里已经历了最痛之时,又两夜未眠,身心疲乏到了极处,心中反有些混沌。他回到房中将向皇帝请罪的表文写好,又将从父亲那里带出来的一块白绢叠好放入怀中,便躺到床上闭目静候。他并不指望昨夜之事能瞒过皇帝,该来的总归会来,薛崇简说得对,担忧有什么用?上天也从不会因人的将恐将惧而多一分的慈悲。
他未睡到一个时辰,就听见二弟李成义在门外颤声道:“大哥,宫中来人了,至尊传大哥即刻进宫。”李成器原本睡得不沉,立刻惊醒过来,愣了一愣,对婢女吩咐:“更衣。”那婢女从熏笼上拿起一件素色袍服,替他着上,这婢女是刘妃使出来的,总记得这条。熏热的衣裳贴上身子,一股带着香气的燥热透入胸怀,便如同被人轻轻拥抱。李成器按了按胸口,凄然一笑,点头道:“开门吧。”又拿过那封罪疏放进怀中。
李成义和李隆基双目红肿进来,李隆基在李成器足边跪下道:“大哥,我同你一起去。若是能面见至尊,说不定还能探知母亲下落,那时候你我请你身代,总还有一线生机。”李成器轻轻在他肩头拍了拍道:“见到宅家我自会说,你在家,弟弟们总还有依靠。”他又握住成义的手道:“遇到事情,便听三郎的。”成义哽咽着点点头。
李成器见那婢女拿来郡王远游冠,摇头道:“我是罪人,理当蔽衣科头,用木簪,选一顶小些的幞头吧。”那婢女替李成器将头发细细结成髻子,在镜中看到这少年鬓如墨染,面如玉琢,俊秀得如诗如画,一双眸子却是黯淡全无生气,心中一痛:大王才十八岁。她淌下泪来道:“娘娘与大王都是菩萨心肠,神天保佑,你们都不会有事的。”李成器淡淡一笑,握了握她的手道:“借你吉言。”
他出得门来,吩咐备马,那宫中来使却躬身道:“至尊已吩咐为殿下备了车。”李成器心中一凉,声音不由发颤:“是槛车?”那内侍倒笑起来:“殿下想岔了,是至尊怕殿下冬日里骑马受风,让预备了一辆暖和牛车。”李成器微松了口气,便又跪倒,向北面叩拜道:“臣谢陛下天恩。”
牛车踏着不疾不徐的步子,穿过一条条街巷。车中只李成器一人,他轻轻揭开垂帷向外眺望,竟惊奇地发现许多黎民百姓脸上也都带着厌烦苦恼之色。他猜度着他们的心事,那卖菜蔬的大概是厌恶着天气寒冷,耽误了生意;那提着几包药从药铺出来的少年,眉间颇有忧色,想是家中有亲人抱恙;那卖炭老翁的牛车,一只轮子滑入了沟渠,几次使力都拖不出,急得只是鞭打那老牛,那老牛发出委屈的哞哞声。原来这便是众生受苦的凡尘俗世,或苦饥寒,或悲生离,或憎死别,或怨爱不可得,或恨理不可伸,他又有什么资格自怨自艾?也许只有当死亡到来的那一刻,这苦楚才能真正解脱,想到母亲,他头一次觉得死并不如何可怖。
牛车经过尚善坊时,他远远便看见几株红梅妖娆出墙外,一股酸楚骤然涌上,还有是不舍的,不舍那少年在冰天雪地中金鞭遥指,笑道:“这是我家,你来玩儿!”李成器心中一阵难以压制的焦灼,猛得抓住车窗道:“等等!”宫使忙让车停下,俯身道:“殿下?”李成器向那片银楼玉阙凝望片刻,狠狠透了口气,压制住眼中酸意,将垂帷放下道:“没事,走吧。”
耳旁市井喧闹之声渐渐止息,只剩牛马踏着地面的嘚嘚声,当是已经临近皇宫,李成器可以望见按巍峨则天门,与耸入天际的万象神宫。在他的眺望中,车子临近一道城门,他抬起头,看见高高的青砖城阙上方的巨大石匾,凿着“丽景门”三个大字。车子进入皇城后,在一道横亘在宫城墙与皇城墙中的夹城里逶迤前行,奇的是路上竟然空无一人,连皇宫中最司空见惯的内侍也没有,墙垣边几丛白色草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几只麻雀在草丛中用爪子扒拉着什么,咕咕鸣叫声中愈显得这一带清冷落寞。李成器心中隐隐不安,即便是从洛阳宫到上阳宫,他也不曾走过这条路,忍不住问道:“至尊可是在上阳宫?”那宫使在马上回头一笑道:“奴婢是奉旨送殿下,殿下放心就是。”
牛车拐了个弯终于停下,那宫使下马替李成器打开车门道:“前面不许行车走吗,殿下请下来吧。”李成器跳下车来,整个人便已呆住,数百名金吾羽林执戟挺立,在城垣的尽头,是一扇通身漆黑的木门,门上匾额却是三个大大的金字,那飞扬的笔意可以看出是御笔,冬日阳光虽然不强,李成器仍是被那金光刺痛了双目:推事院。
那宫使见这一路都淡雅从容的少年皇孙,片刻间就吓得面上变了颜色,心下不觉好笑,道:“宅家命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