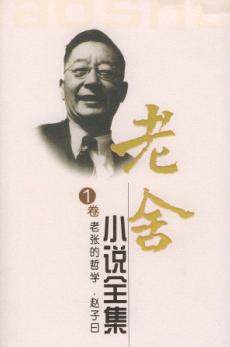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 ����:��ˮ����-��1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ϻʡ���
���������ʶ��ס������������ȥ�����꽫��ص����������������������������һ�ű���ĺڰ��С������к���һ��ʹ��˶��������ȭ���������˫��������֪�Լ����ںδ�������֪��Щ���ɵƻ���һ�����ǻ�ū���ĸ�����ڡ���Ԫ�����ͣ�£�Ҳס�������������£�ҹ������ʵ�飬�����ȼ�ȷ��̫�ϻ�ƽ��Ҫ������������������飬ֻ�õ��ͷ������������
���DZ���̫�����⣬ԶԶ�������¥�ϵƻ�ͨ������������̸���������������ǰ��������������������ף���������������������������һ����Ӱ������¥�ߣ�����Ҳ��Ϊ��������Ӧ�����������������������һ�������������������������ó�һ��·���������¥�ϱ�ȥ��̫�ϻ��Ѳ����ȴ����˲������ӭ�����������������������������һ������̱������æ���������������г��˺��£���̫�ϻ�ҡͷ������ֻ����һƬ���룬����ʡ�DZ��𣬾����Ǻ������ң����ڲ�֪��
̫�ϻʷ�ס������ӭ���Ĺ�Ԫ��������������ٴ�������������������Ԫ��������ٴ������������ұ�������Ԫ��̧ͷ����̫�ϻ�һ�ԣ���ǰ�����µ������������ʥּ����̫�ϻʣ�������б��´��ã���̫�ϻ����ڰ�������̫�ϻ�����һ�����ʵ�������˵���¡������ɣ��������������Ԫ������������ʵ۷�̫�ϻ�ھ������ɱ����ҳ�����̫�ϻ����ǡ������Ƕ��ϴ���֮��������أ���Ԫ��ļ��仰��Ȼ�����������ҵ�̫�ϻ����ĺ���һ������������ɫ�Ծ�ŭ������תΪ�������ŵı�����������̧��������ָ�Ź�Ԫ�����������˵һ�飿˭������ھ����������������ߣ�ȴ��û����Ȼ�������������У���ʵ��һ��������̫�ϻ��������������ݡ�
�������������������������������������������������������ǽ����ؾ��ķָ���
̫�ϻ���˾�ŭ����Ԫ��ԭ����Ԥ�ϣ����������������Ӱ�˿�ֻ�Ǹ����������ˣ����յ�����Ȩ�������һ�㣬����ҹư�ô��꽽����ʣ��һ�ѱ���Ļҽ����������������־��ˡ�����������˵����������������ȥ��������Ǿ����ԣ�ǰ��ҹ����ԫ����Ԫ��ߵ�״��ݵ��������·�̫�ϻ�֮�����������̫�ϻ���ǰ����һ����ŭ������˭�Ǽ����Ԫ�������Σ�����֮�ˡ���
̫�ϻ���������һ�Σ�����������ͷ�����������ˣ��������ˡ������ǣ������վ��ǵȲ����ˡ�������������ǰ����һ����������������Ҫ��̫ƽ��Ҫ�����ɣ�����Ԫ��δ����������ǰ��������������ǰ�����������������ϵ��������������ǵ��������ΰ������Ӱ���µ�������̫�ϻʵ���ǰ���γ�һ�±����Χǽ��̫�ϻʱ����Ĭ�����ƱƵ�ͣס�˽Ų����������ŵػع�ͷȥ�����������ǡ���Ҫ���ݣ�����Ԫ��վ�����������������֮��������̫�ϻ���ȫ����̫�ϻ����ڰ�Ъ�������´���һ�ˣ��Ի�ǰ����̫�ϻ���������
�����һֱδ˵������תͷ�������ȥ��ȴֻ����һƬ���û�⣬������ҹ���籱��ɽ�ϵ���һ�㣬���������ܲ��õĹ�â�����������������������������е���;ڤ�𡣶�˵�������ϻ����Ѿ�����ຣ��ԭ������������һƬ���������ν����һ˵��������ܾȻ�ū�����������Լ�������������Ѱ����������һ������ת�����ͷ����ȥ��̫�ϻʾ����ĸξ��ѣ�ʹ����������ū�����ɣ�����Ԫ�������������������Ϊ���
����������������˳�ǽ����Ҫӻ�����£���Ȼ������������ɱ���һ�����������гٻ�����������������Ю�֡�̫�ϻʳ���һ����������һ��̱����ȥ�����ߵ�����æ��ס�����������ͷ���Ź�Ԫ�ڰ������������Ԫ���������ݣ�����ȴ������������һ��������Ƿ����������־��������ҧס�촽��һ����ɬ��ζ���ڿ���ɢ����
��Ԫ����������£�̫�ϻ������Ѹߣ������������ף��Բ���������ʧ���������Ʊ�ǧ��֮�塣�������ҧ����������ң��������ң�����Ԫ���Ĭһ�̵����������ң�����ҹ���д��ң��ѱ�������Ϊ�������ˡ���
̫�ϻ����Ի��ʸ�����ת��������Ԫ��Ļ������ϲ����ʵ۾���������������ҪЮ����������뵽���������빬�еĶ�¬�����˿̶���֪�Ǻεȹ⾰������ӿ����һ�Ǻ��⣬�����������죬���ȥ�������ɣ���Ҫʲô���������վͰ����µ����������ֻҪ������̫ƽһ�ң����ȥ������Ԫ������̫�ϻ���˰����������и���һ�ᣬ�����Ե���Щ������̫�ϻʷ��ģ�����������Т���˾�ֻΪ���峯�٣������ľ���̫�ϻ���̫ƽ��������
�˿̵Ļʵ���������̫�������ŵĽ�����Ӫ���ⲽ�����治ʱ�����͵�ѥ�����ܶ���ȥ����Ⱥͳ�Ԫ����ʬ����Ѫ���������ݽǣ���ʵ۲�δ���Ҳ���˸Ҷ��ְ��ȥ��һ�ڽ�����۵Ľ�ʿ�У�Ψ�лʵ�ֻ��һ��Բ��ң���������ʱ·���ͷ����ʪ�ˣ�Ҳ��������һ�ԣ��ƹ���¶���Ǽ�����Ŀ��������˿������ͷڤ˼֮ʱ��ǽ��̻�������ϼ���������·�����Ž����ͻʵ۲������裬ͬ������������������Ҳ����ͷһ�أ�ֻ�Ǻ�Ȼ���ã���֮����Τ��ʱ�������緢�����꣬��ǰ�����Ӿ���������ʮ�ꡣ
���㽫�����ص´Ҵұ��������ʵ���Ȼ̧ͷ�������ʵ�����ץ����û�У������ص�Ĩȥһ��������ˮ�������ҵñ��°�����ȫ��̫ƽ��ȥ�ȶ��ӵ��˻�δ���ø�ۡ�ͱ����á�����Ѧ����������Ӷ����ˣ�Ѻ�ڳ���Ӫ�У�������·��䡣���ʵ�������˿�����������̫ƽ��;ĩ·֮ʱ��Ҳ�˲�����������ˡ�������ʿ������̫ƽ�ӳ���ȥ���վ��ǷŻ���ɽ������������������á����ʵ۵�Ц���������Ŀ�ɽ�ڳ����أ��ܳ�ȥ����Ѱ��·������֮�½�����˳������á���
˵������袴Ҵҽ���������Ҳ��һ��ʪ��ȴ�����洺�磬Ц���������£������Ҵޜ��Ѿ����£������϶��ӳ����ţ�������·ʪ��������������ˣ����������˳�����Ҳ���˹��������ʵ�����һЦ���������Ͱ��䣬��ˣ��������һ���˷�һ��Ѻ�����������У������շ��䡣������ͷЦ��������ѧʿ������д����ô����
�����е����F̧��ͷ������һ����£��ڲ��������忡�������������㲡����ĸ����չ�ȥ�����ã�������ڼң����ո���ʿ�Ҵҽ������빬�У������ϲ�����������������˴��¡�����ҹδ�ߣ������в���Ѫ˿�������黹��ƽ�������ʻ������£��������ӣ������ͷ������گ���Ѿ��ݾͣ�����¹�Ŀ����
�ʵ�����ǰ�������ŻƲ���һĿʮ��ɨ��һ�飬Ц�������������˵С��ѧʿ˼��Ȫӿ���⼸ƪ���ºϵ�����д������ȥ��̫�ϻʰɡ������F�����������˲���֮�����˵ȴ��£��������رܡ����ʵ���ɫһ������������ѧʿ��Т�ӣ���Ը����������������Fߵ���������ձ��´��٣������������빬��ֻ���������������Σ��֮�ʣ��Ե�ͦ�����ѡ����ձ��³�������F����ī���֮��Ҳ�������ڱ����������������棬�Ե��˹��������ơ���
�ʵ��������ٿ�����Ƭ�̣����廪�ķ�����飬�������벻���������жȹ������������ƾʲô�����Ĵ������Ǿ��������ɱ������ʵ۸��������F���Ե�����������֪��Ϊ��Ҫ����д��ƪ���£������F����̧����ʵ�һ�������ֵ���ͷȥ��ѹ������������������֪���࣬����֪�����ѡ����ʵ�̾�˿��������������F�ļ�ͷ����������Т������ȫ֮�࣬�������dz��Ӳ��С�����ֱ�������������ˣ���ȫ����Т�ӡ���
�ʵ�����������¥��ʱ������һҹ�ı����Ѿ���ס����������Ұij��ء��ʵ���������һ������ʪ��֮�������紵���������������Զ��죬�����ڿ�����֮�⡣����������¹���ij����ǣ�Զ�����ʵ�ɽ�������������ͬ��µ���Ů���壬���������Ķ��顣��������û���ĸ�Ů�����������ģ�Ψ��������ɽ�Ľ��ޣ�������˼������˵ĺ��顢־�������ԣ�����Ϊ�˷�����ǣ������ڡ���ҹ�������ʹ��ս�𣬿־壬����������µ���Ѫ�����ڳ�����Ʈ�����ơ���֪���������˶�ã����ն�������������֮����������������¡���Ĺ��ʢ����
�ʵ۽�����У���Ԫ��Ҵ�ӭ������ߵ�����������ر������������ʵ۵�����̫�ϻ�����ɺã�����Ԫ����ü������̫�ϻ����˾��ţ�Ŀ��ʥ�������������ϲ��ܣ��������������������ʵ۷������������ĸ��֣���������������ҹ������ѡ���
���ٲ����ڣ�������һ����������̶��Ǵ�������֮����̫�ϻʿ��ŵ��������ɡ�����������ô�����ʵۿ첽�����һ��̫ҽ��������Թ���̫�ϻ�齱ߣ������ǵ����ҩ�롣������̫ҽ�Ը�������ȡһ��ҩ��������齱߹��µ�������������������ܾ��ˡ���
̫�ϻʷ����������ӣ�����߬ס�ʵ۵��ֱۣ����е�����̫ƽ��̫ƽ�������
�ʵۼ�������ɢ�ң�һ���ҷ����ڼձߣ������ǻҰ�֮ɫ������������������Ϊ�������ֱ��ϱ���������������������ϣ���ƽ�����������������̬�ȽԲ���ͬ����ֵ�����������˿����������������������ǵù�����˵��ĸ�׳��µ�ʱ������ֹ�糣����ô���ǽ�������̫ƽһ��ʤ�������ĸ���Ӧ��Ҳ����ֹ�糣�ġ���ת��ȥ����������������һֱ˫Ŀ�ʹ������Լ�����������������Щ���죬��������粻���ʻ�ūô����
�������̫֮�ϻʵ���ƽ�����࣬����������Ԫ���Ǹ������ˣ�����Ī����Ϊ����������ؼ�ȥ�ɡ����ʵ�����������������������������ѳ�Ĵ��㣬����һЦ������ɩɩ�������������ôҪ�����أ����ģ�̫ƽ������ɽ�ϣ���ū�����������У���û�������Ƿֺ�����
̫�ϻ����������ӹ�һ˿ϲɫ�����ս��ʵ۵��ֵ���������֪��������֪������������Եġ���ǰ�ǵ������ˣ���������̻��̫ƽ���������գ��������յ����ͻ������㣬ֻ�������һ����·�����������ˣ���
�ʵ�һЦ�����������յ���Ҳ�����������ʺ�ô����̫�ϻ�һ������֪�����к��⣬�ʵ��Ѳ��ÿɷ��Ц�������������Ӳ�ˬ������̵���Ϊ���²��ͣ���������д���˼���گ�顣������ͷ�Ը�����ʿ�������
����ʿ�ӻ���ȡ���Ǿ��Ʋ�������ɤ����������첽ʱ�裬��ҵ���ѣ��ҳ��ɼͣ��δ���֮���ҹ�����ʥ���ڣ��ع��ͳ������Ľ�壬�������ݡ����Թ���������ا������������꾾���۾��������֮С������Ⱥ��֮���ԡ���ʹ��֪���ã��˾���������ν���DZı����ǽ���ơ������ꡢ�����ҡ���ˡ�Ѧ𢡢���ࡢ��Ԫ������������꿡���������ա����߸�����Т�ҡ�ɮ�ݷ��ȣ�����ӹ�����ж��ң�δ�����֮Ч���������֮�ġ����ٱ�����ͻ���н������������ʵۣ����д��档����ʵ������ֳ���Ӧʱ�御��Ԫ���¾���鵳�ϼߣ�����V�����������á���
̫�ϻ�������һ������ʱ��һ����ʹ����������Щѣ�����̣����������꣬����δ�ᵽ̫ƽ���������¸���һ������Ȼ�������㴦�õú��������������������ɡ�������ʿ�����Ų��������ڰ�ͷ��̫�ϻ���������������ֶ������������˿�����������ū�������һ�ѡ������������һ�ᣬ�����ס���ף���ס������д�¼����֣���������ʿȡ��̫�ϻ��������Ӹ����ϡ�
����ʿ��ȡ���ڶ������������֮���·�Ϊ��������֮�أ��������ܡ������оӴ�ͥ���廳��ˮ����Ϊ��־���������ġ�������ʿ������������������������Ͻڣ��������ǣ���ʹ��֪����
̫�ϻ��������䣬��֪�������Լ�������گ�飬Ҳ��������ϸȥ������ĬĬ��ס��������֣�����һ��ãȻ��������������̫ƽ���������Ϊ̫�ӣ����Ǻε��龰���������̫ƽ�������ֵܺ����𣿻���תһȦ�ֻأ��վ��ֻ�ص����գ��ص����£������������ϴӽ���֮���ɶ�ܵ�����ô��
����Ȼ����ȥ����Ϊ�������д�����ģ�����Ω���䣬������𡣺�Ϊ��������ڤ���š����˷��£��������ԡ�����ױƣ�������ۡ�����ʱ��������Ц���˼ң��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