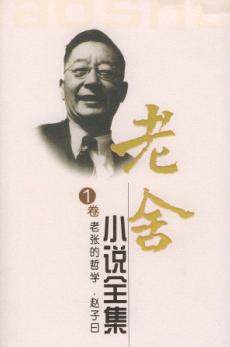长安古意 作者:掠水惊鸿-第10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些羽林望了一眼薛崇简臀上伤痕,见肌肤已肿起一层,原本紫色的细血点这阵功夫就隐隐转黑。他们平日偶尔远远观望一眼,见他轻裘肥马的王孙公子模样,知道是和他们有云泥之分的人。却料不到有一日会离他们如此近,且是天地逆转,轮到了这金为裳玉为体的公子,匍匐在地上挣扎哭泣。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令天下人艳羡的异姓郡王,剥去了锦衣华服,也不过是个被打了屁股就会哭着喊娘的孩子。这稚子般得哀告,令他们这些无关之人也心里发酸,忖度若是依着惯例责打臀腿,他定然承受不住,无奈下也就只好依旧向他臀上杖去,只盼那里皮肉厚些,不至于伤了筋骨。
薛崇简喘息了一刻,反时将方才的一点点力气也用光了,杖子重又打落在高肿的肌肤上,疼痛竟是变本加厉更增十倍,一时浑身毛孔都似要炸开,高声惨叫了一声,被死死压在地上的双手也开始盲目地乱抓,似是想抓住一点借力之物。
太平对儿子的痛哭哀嚎恍若不闻,她的视线缓缓抬起,望着门外,瓢泼一般的大雨倾泻而下,一簇从室内射出的灯光,将李成器笼罩其中。雨水将他从上到下浇了个通透,他们隔着薛崇简孤单的痛呼,隔着暗沉沉的雨幕无声相望。太平在与这少年彻底决绝之后,再看向他的目光,反倒有种不可言喻的温柔。或许她对他的期望已尘埃落地,或许她有所嘱托,她确信他们哪怕互相仇恨,却可以彼此懂得。
忽然太平听得薛崇简的一声惨叫有异,低头看时,身上不由一颤,原来那杖子宽大沉重,十杖抵得普通刑杖二十还有余,十来杖已是将高肿的肌肤拍得破裂开来。因肌肤都已成深深的红紫之色,反倒看不出究竟破在何处,只看到一股鲜血跳出,缓缓顺着莹白的髋骨滑落。
其后板子次第打落在破皮流血之处,两三杖后将那伤口渐渐撕裂,皮肉上竟是挣开几道寸许长的裂伤来。薛崇简已经痛的失去了理智,早忘记了自己是为什么受责,只是下意识地用嘶哑的喉咙叫喊着阿母。
虽无人在旁计数,但行杖的羽林心中却有计较,这杖子委实太沉,两人各打了十杖便双臂酸痛,依照惯例要换人行杖。他们迟疑一下,便停了杖,低声道:“启禀公主,是否要换手?”太平稍稍一怔,明白了他们话中含义,点头道:“换吧。”
薛崇简昏沉中仍是听到这句话,心中一股绝望登时翻涌开来,无力地哭道:“不……不要……阿母……我受不了了……”那些人却不理睬他,他听到身边脚步纷杂,知道有人换到了自己身边,知道再不说话就来不及了,不知从哪里挣处一丝力气来,努力提高声音喝道:“你们……放开我!”
太平不料他竟还有这等脾气,哼道:“我打不得你了?”薛崇简闭目微微摇头道:“阿母……你让他们松一下,我……我有话说……阿母,求求你……”太平不知他要做什么,便轻轻挥了挥手,按着薛崇简的羽林连忙退后。薛崇简长松了口气,他努力动一动被按的麻木无力的双手,忽然使力向前爬去。太平仍是不知他要做什么,只是见儿子臀上皮开肉绽鲜血横流,艰难地一点点向自己爬来,眼眶不由一酸,忍泪俯身道:“你要说什么?”
薛崇简却不吭声,他手指扒住地板缝隙,努力将身子向上蹿了一下,然后他伸出手去,带着怯意的手握住太平垂于榻下的帛帔一角。似是怕母亲会骤然抽走一样,他的手轻轻一转,让那帛帔缠绕在他被攥得乌青的手腕上,将那一缕轻纱拉过来,缓缓将自己的面颊偎了上去。做完这些,他方满足地吁了口气,闭目低声道:“打吧……别让他们按……我不动。”
他面上平和温存的神情,如同昨夜他在自己怀中睡去。太平的胸口骤然被一股悲怆击中,她亦忍不住轻轻握住缠绕在臂上的帛帔,她似是听到汩汩的血液流动的声音,沿着他们相牵的血脉,从她的身躯流向儿子。太平编贝样的细齿轻轻咬了下下唇,吩咐道:“将他送回房去。”
李成器跪在门外,看着堂内的人手忙脚乱将薛崇简负走,看着他们打水洗去地上的血迹。有人吹熄了灯,将他的世界沉入一片暗海。他起初还知道自己是在谢罪,努力跪得直些,可是过不了多久,膝头便剧痛欲碎,实在无力支撑,只得跪坐在足踝上,两腿渐渐由痛转酸,有酸转麻,这个身躯似乎不再是他的。夏日里暴雨倏忽来去,他被雨水砸得快要晕去时,那雨却渐渐收住了,湿透的衣衫帖服在肌肤上,被风一吹,冷得他阵阵哆嗦。
不知是什么时辰,有个婢女点着灯笼过来,道:“殿下,公主请殿下回去。”李成器抿抿干裂的嘴唇,努力开口问道:“你家郎君,怎样了?”那婢女摇头道:“奴婢不知。”李成器低声道:“求你让我,再留一阵。”那婢女见他冻的脸色青白,心中不忍,乍着胆子低声劝道:“大王,您便是跪到天亮,公主也不会让您见郎君的,您还是回去吧。若是走不动,奴婢去唤人来负你。”李成器虚弱地摇摇头,过了一刻,见那婢女仍是立于他身旁,便低声道:“我在这里,离他近些。”
那婢女不再说话,四下里寂静不闻人声,只有风拂动屋檐下的铁马,叮叮咚咚做响。他的神智一阵清醒,一阵迷蒙,也许他对花奴想的太多,想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心中反倒模模糊糊想起些毫不相干的事:那对燕子的巢,在风雨之后可还完好么?它们是否会依偎着取暖,并肩听雨落芭蕉,风动铁马,一起静静地等待,纤月排云而出,将清光洒遍天地。
85
85、八十四、独有南山桂花发(下) 。。。
李成器再醒来时,只见王妃元氏双目红肿坐于榻边,见到他睁眼先双手合十念一声佛,慌忙向外喊道:“供奉,宅家!殿下醒了!”李成器只是朦胧觉得头痛欲裂,口中干苦,两腿也如同不是自己的,全然不曾有知觉。
皇帝带着两名太医匆匆从外间转进来,先试试李成器的额头,长吁了口气道:“退了烧就无大碍了。”皇帝在床边坐下,握起李成器的手道:“你吓死爹爹了。”元氏见李成器轻轻舔了下烧的干裂的嘴唇,忙向婢女要来蜜水,皇帝从她手中接过,喂李成器饮了两勺,李成器稍稍一动,皇帝轻轻按住他道:“你躺着,不必多礼。”
李成器望了一眼父亲与妻子,终于确定这是在自己的府邸,低声道:“爹爹怎么出宫了。”皇帝道:“他们说你昨日一直高烧昏迷,我放心不下。”李成器心中微微一惊,却只觉一缕悲酸劈开他混沌的神智,让他疼的颤抖:花奴带着伤,独自疼了两个昼夜。
太医见他神情痛楚,忙揭开他腿上薄衾,轻轻卷起他中衣裤管,两个膝头兀自发紫高肿,元氏不由眼圈复又一红,那太医道:“殿下可是腿上疼痛?”李成器摇摇头道:“你出去,我同陛下说两句话。”皇帝神情稍稍一顿,叹了口气向儿媳道:“你带他们出去煎药吧。”
待室内人都鱼贯而出,皇帝用手巾去拭李成器的嘴角,李成器不知为何,腹内忽然犯起一阵酸苦,他从来未敢对父亲有所违拗,今日不知怎么,似是大病之后心神混乱,竟无甚顾忌,不由自主轻轻一偏首。皇帝倒是未想到他会躲避,手在他脸畔停驻了一刻,缓缓垂下道:“是我连累了你们。”李成器低声道:“那日姑母进宫,可是责怪爹爹了么?”皇帝涩然一笑道:“终究是她一说话,我就无法了,我答应她,虽然退位,但暂时摄政,军国大务及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重大刑狱,仍有我来决断。你姑母数次挽救宗社于存亡之中,我也不能一次剥掉她的权柄。”
李成器这才知道,那日太平进宫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将天地扭转。他喃喃道:“原来爹爹还是看不成南山的桂花,却险些搭上花奴的性命。”皇帝怅然道:“我总想着,他们是母子,终究你姑母会原谅他。”
李成器凝望了父亲一阵,忽然颤声道:“爹爹心中也在害怕么?”皇帝被他问的一愣,随即握紧他的手,稍稍俯下身子道:“爹爹从即位那一日起就在害怕。”李成器咬紧牙关,强行支撑起身子道:“爹爹想用这法子保全花奴,可是您用什么法子来保全姑母呢?”
皇帝道:“凤奴,你现在也长大成人,有些事,爹爹可以对你说说了。当年你阿翁要立你阿婆为皇后,固然是对她一片深情,也是他看出,你阿婆是非凡之人,只有借助你阿婆的能力,才能帮他摆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托孤重臣的摆布。除去这些禀钧之臣后,你阿翁想收回权柄,才有了上官仪草诏废后一事。我幼年跟随你阿翁时候最多,他毕生为两件事困扰,一是他的健康,二是对你阿婆的感情。他为风痛所苦,不得不让你阿婆替他料理政务,却又恨她窥伺李唐社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在这世上,最爱敬之人是他的皇后,最畏惧之人也是他的皇后。就像……”他顿了一顿道:“就像我对你姑母一样。”
他抚着李成器的肩头道:“我想让你明白,你姑母一生为则天皇后所毁,也赖则天皇后成就,根源却不在则天皇后而在我李氏。太祖太宗皆娶北周北魏女子为后,我们身上有鲜卑人的血脉,他们尚武佞佛,容许女子干政,这些我们李唐都继承了下来。 可是我们毕竟同北魏不同,我们要用儒术来治天下,妇寺不得干政,是天意人心所趋。你姑母与三郎硬拼,是赢不了的,我这次退位,乃至让她对你恼怒,也是为了断绝她心中不可想之事。过得一两年,三郎逐渐将大权收回,你姑母冰雪聪明,懂得顺应时势的道理。三郎要做明主,也不为已甚,我唯一的愿望,便是在我身后,他们能相安无事。”
李成器道:“我只求爹爹一件事。您知道姑母最在意之人是花奴,可是不要再用花奴来牵制姑母了。花奴是为情意而活的人,他现在维系性命的,只有一个母亲了。”皇帝黯然道:“是爹爹的错。我不曾想到,曾经对你们许下的诺言,一句也无法实现,却由我亲手将你们逼迫到这样的境地。”
太平公主下朝后,本是想去看看薛崇简,行至府门前时,却有内侍来禀报道:“定王请公主去他房中。”武攸暨自蒲州回来后就缠绵病榻,延医用药一直不见起色,她忙于朝务,也无暇去照顾他。她轻轻蹙了蹙眉,终究是放心不下儿子,道:“告诉他,我换身衣裳就去。”
她来到薛崇简寝阁外间,便闻到一股浓郁药气,守候在阁中的太医忙亲身行礼,太平挥挥手示意他不必多礼,轻声问:“他醒了么?”那太医道:“郎君外伤内毒夹攻,引的高烧不退,梦魇中常常会说胡话,便醒来亦不甚明白。”太平心中稍稍一紧,问道:“他说了什么?”那太医望了太平一眼,垂首道:“臣也没听清,似乎叫阿母。”太平轻轻握住自己臂上帛帔,举步道:“我进去看看。”
她来到室内,见两个婢女跪在床头,手巾裹了冰块,缓缓为薛崇简擦拭额头,薛崇简俯身而卧,脸上两片潮红,唇上却毫无血色,且尽是一条条咬痕。太平上前缓缓揭开他衾被,见臀上伤势虽已止血收口,却越发肿成深紫颜色,且是几条伤口刚刚结痂,边缘犹渗出淡淡血水来。那两个婢女虽在太医上要时见过薛崇简的伤势,但每多看一次,眼中仍不免露出惊惧之色。
太平向那伤势凝目片刻,叹了口气,缓缓将薄衾盖上,这轻微的触碰似也引得伤处作痛,薛崇简在梦中颤抖一下,忽然带着怯意唤道:“阿母……阿母别打我……”太平眼眶一酸,忍不住抬手轻轻抚了一下薛崇简的脸颊,薛崇简却朦胧睁开眼,太平心中一惊,忽然就想转身离去,却听薛崇简哑着嗓子低声呢喃道:“阿母,我疼,给我揉揉。”太平在他身旁停驻片刻,见薛崇简眼神涣散,便是如太医所说的梦魇,竟然忘记了他这一身伤痛,便是自己赐予。太平稍稍松了口气,坐到薛崇简身边,轻抚着他的头发,薛崇简忽又受惊一般哭起来,道:“阿母,阿母我知错了,你别不要我……”太平泪水涌上,轻拍着薛崇简背脊,安抚他道:“阿母在这里,阿母永远陪着你的。”薛崇简似乎也并未等她回答,哽咽着哭了一阵,又挂着泪水睡去了。
太平缓缓伸手擦去儿子眼角的泪水,这样也好,他醒来时,不会记得梦中自己来过,更不会记得自己的许诺。有些许诺不敢出口,因为未来她无法兑现,有些深情在离去时才能懂得。她主宰着万千人的性命,如崔湜所说能够扭转乾坤,却不敢对儿子许下诺言。过了一阵,太平要起身时,却见儿子手中握着自己的帛帔,她低头轻轻在儿子面颊上一吻,将那帛帔脱下,放在他枕边。
她出门来对内侍吩咐道:“去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