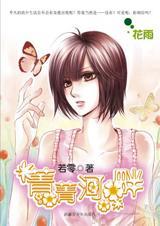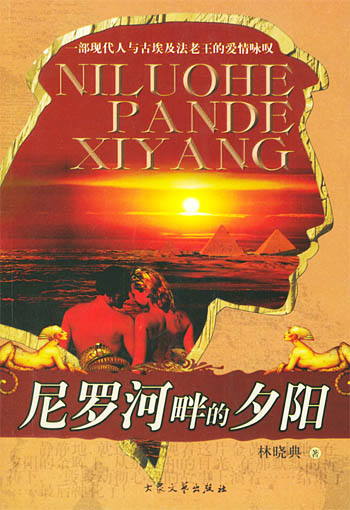鹤阳河畔-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符荣华又怀孕了。
怀孕后的荣华,胸脯高高地挺着,肚皮鼓胀得似就要从紧绷的短裙间挤露出来。脸颊上长着灰黑色的斑锈,但是精神还算可以。自从到山区跟丈夫生活在一起后,他们夫妻互相体贴,互慰互助,生活虽仍是艰难,但荣华脸上常常挂上笑影。放学回来,在灶台边,在洗衣盆前,荣华有意或无意地会哼着她在学生时代所唱过的一些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陶天赐看到了她脸上的笑影,听到了从她那欢悦的心田上流泻出来的歌声,他心里也很高兴。有时,他也凑了过去,跟她一齐唱着那“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个小生命在她体内蠕动,算下来小家伙很快就要出生了。大女孩在老家跟着奶奶生活,水肿病还没有治愈。天赐上中学的弟弟和家中老母的生活费用也需他们照顾。荣华的母亲和弟弟也需他们照管。他们两人每月仅有六、七十元的工资,不管怎样紧缩开支也都很难安排。肚子里的小生命一出世,用什么来养活他(她)呢?荣华的心情近来十分沉重。脸上的笑影渐渐消失了,歌也不哼了。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商量、议论和争吵,最后陶天赐屈服于符荣华,同意她到医院去请大夫给她作人工流产。经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检查,因荣华体质虚弱,胎儿月数又多,医生建议人工流产必须到地区级医院去进行。
天赐向学校出纳预支两个月的工资,又跟老师们借了一些钱,准备带荣华到地区医院去。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天赐要送荣华去地区医院的前一天,接到弟弟从老家寄来的信,说家乡饥荒严重,饿死的人不少。又说丽丽水肿病重,叫他马上设法带女儿离开老家。
看了弟弟来信,天赐马上给弟弟拍个电报,叫弟弟接电报后马上带丽丽到专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找他们。
第二天下午,天赐的弟弟带着丽丽到专区医院找到了他们,看到了女儿,天赐和荣华全愣了。女儿浑身通黄,连头发也变黄了。脸上浮肿的肌肉呈半透明状,皮肤下面饱含水份。手指肿得像熟透了的芭蕉,脚板肿得又肥又硬,穿不了鞋,只得光着脚。丽丽看到了爸妈,哗的一声哭了起来……
妇产医生对荣华全面的检查之后,对陶天赐夫妇说,胎儿已有六、七个月了,母体贫血,体质虚弱,人工流产恐怕流血过多,会有危险。建议暂不作流产,回去先调养好身体……
无奈,陶天赐将凸着肚子、脸色苍白的妻子和患有水肿病全身黄肿的女孩,带回自己谋生的苗寨学校来。
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孩子气还未脱掉,陶天赐就离乡背井到边远的海滨小学去饶口舌。为了找一条出路,他有幸考进大学就读。孰料在圣洁的孔门府堂,也有诬陷,致使他身陷囹圄,吃尽苦头。幸得上天开恩,友人相助,逃出虎口,来到山区苗寨中学当教书匠,天赐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道生活的浪涛却一次又一次地扑来,使他招架不了。不知道是历史的错位还是人为的原因,陶天赐一直在人生的苦海中漂泊,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爬行,在苦难生活的磨盘中流汗流泪。年青的陶天赐发根已渐渐地缀上了斑斑的银白。
戴帽中学的帽子终于摘掉了,中学从小学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间独立的初级中学。教育局派来一位姓卓的校长,来领导这间只有三个班级的初级中学。因荣华汉语拼音较好,中小学分开后,她从幼儿园到小学来任教。
新学年又开始了,荣华挺着大肚子到学校去。想不到那个被人们叫为“半截人”的任教导对她说:“这学期学校不安排你的功课。”
“为什么?”荣华诧异地问。
“你到公社去问问。”
回到家来,天赐、荣华夫妇都在为这件事而苦恼着。这一夜,夫妇几乎全没有睡。荣华叫天赐到公社去问问。天赐认为反正都是因出身问题,问与不问都是这样。荣华却认为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这样被开除。要开除也要说个原因。荣华说:“你不去我去。问个明白,死也瞑目。”天赐怕荣华瞎子不怕老虎,到公社去胡乱说话,犯了政策,伤了领导,闹出了大事来。退一步来说,也许事情并不像所想
象的那么严重,她鼓着肚子到公社去,下声下气的求爹求娘,要是懂事的领导,以礼相待,耐心解释还好,要是领导架子大,不予理睬,或是官腔十足,双方顶撞起来,鱼要鱼鲜,虾要虾红,这还了得?想到这里,天赐只得迁就了她,说明天下课后,他到公社去找管文教的木副书记问一下。
第十八章(2) '本章字数:1574 最新更新时间:2011…10…09 10:00:08。0'
陶天赐来到学校报到了。这是一间戴帽中学。所谓戴帽中学就是在一所完全小学里戴上中学的帽子,在这里先招一个初中班。以后班级逐年扩充,学校发展到初中一、二、三年级都有了,戴帽中学就由小学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一间中学,这时,“戴帽”二字才被除去。
戴帽这个词,对天赐来说十分敏感,他右派分子的帽子刚刚摘下,现在又来到一间戴帽中学来。他心有余悸,一听戴帽,心就惊惶。戴帽中学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日子里的产物。是浮夸风到处泛滥的岁月里的新创造。
在河岸边的高坡上,在几棵参天的大枫树下,在被人工整平的一片黄土地上,井字形的横竖卧着四、五幢茅草房,这就是戴帽中学。台风刚刚刮过,屋顶上的好些茅草片被台风刮走,剩下来的一些茅草片,很像被宰的鲤鱼身上逆竖起来的鳞片。陶天赐持着县教育局的介绍信,来到学校报到,看到这些茅草房,心里马上想起了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由自主地他口中溜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
接待陶天赐的是这间学校的余校长。此人背稍驼,脸色黑黄,两行牙齿排列得很不整齐,说话时语音不太清楚,为使对方能听懂他所说的话,说话时他的双手总是习惯地比划着。余校长毕竟还是个有修养的教育者。对人热情,态度温和,对新来的教师很亲切,给天赐留下好的印象。
一间戴帽中学,能有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来当教师,这实在是难得。余校长安排他住宿在一间较大的宿舍里。虽然也是茅草房,但还算是宽敞、凉爽。
这里是黎苗族同胞聚居的山区。这里的干部、家长和学生,对这位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教师十分器重,家长夜里猎到猎物,第二天早上学生就会给他送来用荷叶包着的一包猎肉。过“三月三”节时,每个苗族学生都给他送来“五色饭”,这种民族风情,陶天赐感到亲切又新奇。
晚上,天赐躺在茅草房里的竹床上,听着崖下河水的奔流声,树林里猿猴的悲啼声,竹床周围蚊虫的鸣唱声,他的心里翻滚着一种难以表述的波浪。
这里高山迭起,河溪交错,交通阻塞。解放前勤劳、淳朴、善良、勇敢的黎苗族同胞,世世代代就在这里过着原始人那样的生活。农忙时,他们刀耕火种,农闲时,就狩猎捕鱼。山外的情况,他们几乎全不知道。解放后,修了路,架上桥,山里的人到山外去,山外的人进山里来。后来,政府在这里设了区、乡。大跃进时,政府提出二十年赶超英国,县里有了农业大学,公社有了农中,也有了戴帽中学。就这样,这里的黎苗族孩子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学了。
河岸边,山坡上,石崖下,散落着一间间船篷似的茅草房,黎苗族同胞不知道自己住这样的茅草房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也不知是哪个祖先发明的。狂风暴雨将他们的茅草房吹倒了、打垮了,他们就用最简单的工具钩刀、镰刀,将茅房再盖起来。山里、树木林立,茅草丛生,钩刀一砍,一支支木条就扛回来,镰刀一刮,一捆捆茅草就挑回来,不多久,茅草房就盖起来了。
这间戴帽中学,也许是世界上最简陋的一间中学了。课桌是埋在地里的两支木桩钉上一块木板。木板是用钩刀削平的长木,削平的那一面,就是写字,放课本的桌面。课椅也是同样如此,二十来个黎苗族男女初中生,就在这样的课堂里聆听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陶天赐教初中语文,一个姓王的中师毕业生教数学。除这两位是新派来的任教初中课程以外,其他都是原来的小学老师,包括校长。
这里的家长学生都喊天赐陶老师,不像劳改场里人开口闭口都大声地对他指名道姓。这偏僻落后的山区,人们心中阶级斗争那支弦并不绷得那么紧。天赐想,这里的人们斗争的对象是禽、是兽、是山、是水,而不是人。可不是吗?山里猎人手中握着的火枪是对着空中的飞鸟,森林中的走兽;是对着山坡上的野兔,河溪中的游鱼……古代陶渊明描绘过一个与世隔绝,太平和睦的桃花源,是否我现今来到了桃花源式的境地?要是这样,那真的三生有幸了,我将要把我的老母亲、妻子、儿女也带到这桃花源式的地方来,让他们好好地过和平温馨的日子。
第十八章(3) '本章字数:1817 最新更新时间:2011…10…10 17:16:54。0'
山区的夜实在黑得吓人。陶天赐穿上衣服,跌跌扑扑地从茅草房里出来,直向公社卫生院奔去。由于心情太急,走路匆忙,引起了山村守夜的饿狗群起而攻之。这都是山村苗家农户养的猎狗,比一般家犬凶狠、狡猾。它们一边拼命嚎嚷,一边气势汹汹地向天赐扑过来,大有非将对方咬死不可之势。天赐,赶紧弯下腰来捡石块向它们打去。但是,凶狗毫无退让,它们兵分几路,继续向那陌生的来客袭击。天赐看见群狗来势凶猛,自己招架不了,只得拨腿遁逃。眼看快到卫生院的门口了,冷不提防,一只默不作声的蓬毛猎狗闪电般地一下向他袭去。嘶的一声,裤管被咬破了一尺多长。幸好腿没被咬伤。
到了卫生院,门全部紧闭着,只有太平间的大门张开着,黑黝黝的,似要吃人。在朦朦的夜幕下,实在使人心寒。不过,临事的时候,人都总会本能地产生出一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力量和勇气。陶天赐这时心急、胆壮、神旺,别的全然不顾,唯一想的是赶快找到助产士。他不知道助产士住在哪间宿舍,他像个狂人似的对每间宿舍的门扉敲一阵就叫一声。也许主人白天工作太累了,对敲门声、呼叫声全无反应。他更急了。突然记起卫生院的院长是姓程,于是,他每敲一个门就叫一声程院长,急促的敲门声将寂静的夜搅醒了。周围的狗狂吠不停。这时,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一丝微弱的灯光从窗洞中射出来。陶天赐像只漂流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突然见到了标灯那样的高兴。
“叫院长做什么啊?”一个女人的声音,有气无力地从窗洞里飘出来。
“我爱人快生小孩了,要请助产士。”
“助产士下村接生还没回来。”
那怎么办?陶天赐急得几乎要哭起来。
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里面响着:“天快亮了,你回去等一等,天一亮助产士就要回来。”这可能是程院长的声音。
“女人生小孩怎么叫她等一等呢?”
天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转头向学校走去。走了几步又折回去敲程院长的窗门,求他发慈悲给他想个办法。程院长想了一下说,唯一的办法是到学校对面那个荔枝子村去请那个接生婆。不过她年纪大了,不知道能否请得动她。天赐转身走了,后面院长又补充了一句:“接生婆家就在利国队长家的对面。”
在去荔枝子村的路上,天赐的耳边隐隐约约地好像听到婴儿哇哇的啼哭声,天赐歇斯底里地心里想着:是否荣华已在茅房里生下小孩子?她身边只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谁照管她?不会那么快的,不会的……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天赐走进了荔枝子村。四周的树影黑糊糊的。牛粪的臭味和水田里稻草腐烂的腥味阵阵扑来。这些他全不管,心中想的只是找到接生婆。他先来敲利国队长家的竹门,开门出来的是利国队长老婆,山村苗胞纯朴厚道,热情好客。她听这位老师说明了来意,又看这位书生满面窘态,马上披上外衣,带着天赐找接生婆去。
敲接生婆家的门,又惊动了守夜的猎狗。不过,这次有利国嫂的陪同,猎狗狂吠着冲过来,一听利国嫂的吆喝声,立即退了回去。
接生婆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苗族老太太。在天赐的好言好语的乞怜下,利国嫂也在一旁说好话,接生婆终于请回了家。
生男育女本是人生常事,可是,事情落到这对青年夫妇的头上,却又总是那么的不平常。幸好这孩子还未出世就很懂事,他等待着接生婆来到后才降生。要是接生婆未来之前就急于来到人间,那荣华会吃更多的苦!
是上天可怜荣华,不想给她再添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