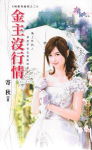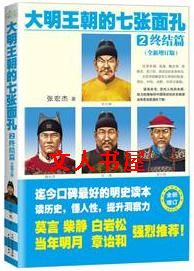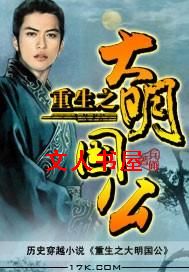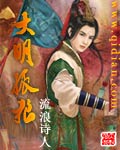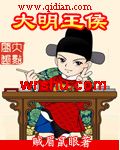大明金主-第10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大春面色稍霁,道:“则你所长者何?”
徐元佐想了想。还是把“诗词”吞了回去。他已经知道林大春要考他古文,再说诗词非但改变不了什么,反倒惹来一通教育。更何况,他的诗词强在背诵,真要三五七步写一首惊世绝艳的试帖诗出来,却是没那个功夫。
“回宗师。小子平日爱读古文。”徐元佐道。
林大春早就预设了这个答案,并不觉得意外,道:“喜读什么文章?”
“先秦诸子,两汉论赋,唐宋杂文。皆有所涉猎。”徐元佐道。
林大春难得地咧嘴笑了:“岂非博而不专?若去其一,则何如?”
张元忭微微皱眉,却是觉得林大春有些过于欺负小朋友了。依他看来,徐元佐天资纵横,但是亏在年纪上。你就算从娘胎里出来就开始看书,什么事都不做,看到十四五岁又能看多少?
而林大春的问题,却不是光看书能解决的,还必须要游学。
只有四处游学,与鸿儒交往,才能知道如今古文的源流,以及派系之争。一个不曾游学参访的少年,最多从父兄那里听得一鳞半爪,如盲人摸象,焉能得其全貌?
想到徐阶徐Ф疾荒芮桌矗约壕褪切煸舻暮笤旁砬辶饲搴砹鹕硇欣竦溃祷埃幢涣执蟠褐棺×恕�
“子盖稍安勿躁,且听他说。”林大春又对左右学官道:“若是他能答得好,我岂吝啬一个案首?若是答不好,且回去再读三年书罢。”
徐元佐脑中转了转,悠然道:“大宗师表面上问的古人,实则问的是今人啊。”
林大春略有吃惊:果然是个悟性极高的。
“前七子文必秦汉,首倡在前……”徐元佐突然脑中一个激灵:前七子是李梦阳、何景明那批正德文士,但是后七子的概念应该是在隆庆中才最终确立的。他临时改口:“唐、归呼应在侧,在小子看来,并非抵触。”
“前七子?岂有后七子耶?”林大春还是抓到了这个词。
“乃是李沧溟(攀龙)、王凤洲(世贞)等嘉靖七子,区别于李空同(梦阳)等正德诸君子,故称前后。”徐元佐解释道:“此复古者诸君,所求‘文则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一也,故可同论。”
张元忭听了微微颌首,的确是有底蕴人家出来的孩子。寻常人家的孩子,这般年纪能读完前三史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林大春道:“荆川(唐顺之)、震川(归有光)诸君与十四子相悖,你为何说呼应在侧。”
张元忭不得不给徐元佐递个小纸条,翻译道:“荆川、震川皆以唐宋为法本,而前后七子不以文字落入开元以下,何处呼应了?”
文学鉴赏是很主观的,有人喜欢四六骈文,有人就喜欢散文吟咏。这说到底是审美不同,未必能分高下。而一旦有了审美,就有了“恶恶”,也就有了对抗。
第186章 少年说
在十四子的复古派看来,唐人至开元之后就有了暮气,宋人只会拾人牙慧,十分可鄙。
至于元人,呵呵,粗俗之徒不足论耳!
甚至连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看来也只有“尚古文”——提倡古文运动,是他们的闪光点。
而唐顺之、归有光领导的唐宋派,则觉得行文应该直白些,秦汉时候那种堆砌各种生冷典故,文字佶屈聱牙的风格实在讨厌。应该学学唐宋,尤其是韩柳欧苏等八大家的文章,简明扼要,不重辞藻,而辞章之美跃然纸上。
文学审美的差异令这两派直接对骂,而且言语极重,偶尔还有人身攻击,放在后世许多论坛都有可能被版主关小黑屋呢。
“虽然各有所美,各有所恶,但是‘言之有物’却是诸君所共识。”徐元佐道:“小子以为,只要言之有物,能为载道之器,皆是一体。故小子读古人文章,只求其实物;读今人文章,只观其载道。至于文风如何,何足道哉?恐怕这也是十四子之本意,而唐宋大家之所求。”
林大春暗笑:果然是少年之人,不知道人心争执,岂会因为一同而存百异?
他道:“言之有理。你可带了往日习作?”
“来得匆忙,并未带来。”徐元佐暗道:往日不写作文,真不好意思。
林大春略有遗憾。
“请大宗师命题,小子这就写来。”徐元佐又道。
林大春心中一动,道:“便以‘少年’为题,写篇古文。”
“敬诺。”徐元佐躬身告退。
徐元佐不知道林大春是怎么想到“少年”这个主题的,但既然出了题目,断然没有讨价换件的道理。更何况“少年”一题。正中徐元佐怀抱。
张元忭听了此题,心中第一个反应是《孟子·万章上》。
“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意思是说:人在年少的时候,会依恋父母;知道美色,懂得找对象了,就倾慕年轻美貌的女子;有了妻子,就眷念妻子;做了官就一心放在君主身上;得不到君主的正反馈,心里就火辣辣地难受。具有最大孝心的人,才能终身眷念父母。到了五十岁上还眷念父母的,我只在伟大的舜的身上看到了。
从立意角度而言,少年一题正是与“立志”、“恒心”、“大孝之始”等等联系起来的。
张元忭不知道徐元佐打算采用哪种文体写。所以大概揣测了一番,觉得难度不大。如果正统来写,可以循着孟子的意思写,无非就是少年之人要立志,且支持以恒。如果要剑走偏锋,可以从《周易》入手,以少年为潜龙,推演十二消息之卦。也能让人惊艳。
张元忭是博学鸿儒,徐元佐却不是。
他是个文科学霸。
第一个反映在他脑中的并非孟子。而是梁启超。
当年梁启超曾有一篇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文章:《少年中国说》。
此文是个将死老朽,前途绝望而写出来寄语后辈的抒情诗,除了文辞上还有些排偶、比喻等可以拿来教中学生写作手法,就只有题目和立意有些价值。
整篇内容都是感情强烈,而逻辑欠缺,就比如脍炙人口的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简直可笑。
长辈老师都是愚昧的,怎么教出智慧少年?长辈老师都不智,智慧的少年只会被视作疯了的少年,还指望国家智慧……先篡权夺政吧。
至于少年富则富,少年如何富?休学去开软件公司?还是创立“非死不可”?
指望萌芽状态的水稻结出饱满的颗粒。真是有种反差萌呢。
徐元佐如果照抄过来,实在太砸自己“神童”的名声,即便后人也会吐槽他是“神经病儿童”。
不过公允地说,梁任公将少年与国运捆在一起,的确是推开了一扇窗。
只需要将“少年之国”改成“国之少年”,文章的利益和格局就上升到了指点天下的高度。
“世有三岁之翁,亦有百岁之童。”县学教官看了徐元佐落笔,连忙抄了下来,送到厅中,呈给林大春。
林大春正与张元忭说话,见这么快就有文字呈了上来,笑道:“小友文思却是敏捷。”他展纸读了出来,微微诧异:“先声夺人,有点意思。”
张元忭听了,微微一沉思,道:“三岁之翁,百岁之童,接下去便是要说赤子之心了。”
“恐怕不好把握。”林大春既有些期待,又有些担忧。
赤子之心讨论的是心。
《礼记》所谓“总包万虑谓之心”,这是最早赋予“心”哲学概念。其后为了满足古人的哲学需求,心正处于身体中间——上中下的中,如同天子处于天地人之间,国君处于君臣民之间,所以心的精神层面意义与实体器官相融合。
到了目今,古籍中将疯癫之症与大脑联系的非主流思想大有传播。
内丹学的发展告诉人们,真正主宰思考、思想的是大脑,或者说是大脑区域。李时珍就说“脑乃元神之府”。当然,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并不相信大脑本身有思维,而只是思维所寓居的物质基础。
反正这个口水仗打了很久很久,在徐元佐穿越的时候还没打出个胜负。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宣布终结了唯心唯物之争——精神病院倒是有不少这样的终结者。
这就意味着,徐元佐要讲“心”,讲“赤子之心”,从纵横两方面阐述,都是极大的题目。
谁知再次传上来的时候,却是“人既如此,国亦亦然。”
这个甩尾漂移叫厅上两位大才着实愣了愣,彼此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张元忭道:“元佐朋友正应了天马行空而步骤不见,确实引人期盼。”
徐元佐定了基调,旋即开始大段类比。
少年诚如国朝初兴,订立典章,革除旧弊,创立文化。与之相对的,老翁就如国运衰竭,社稷将灭,多有诡谲妖异之事。三岁之翁,便是二世而亡的秦、隋、国祚不长的小朝廷,以及蒙元;百岁之童,则是上古三代,圣王治世,时时自新。
林大春张元忭一段段读下来,也不免被徐元佐缜密思维所引导,挑不出半点纰漏。至于行文炼字,这本是徐元佐的弱项,但因为是古文,要求没有时文那么高,讲究“字字珠玑”,便成了瑕不掩瑜,大可忽略不计。
全文最终在回到“修齐治平”,而在“新民自新”点睛,更见格调之高。
第187章 道试案首
徐元佐誊真时并没有改动多少,所以呈卷之后林大春只是扫了一眼,便放下了卷子。
张元忭身份较低,自然先开口道:“此文格局大,立意高,行文流畅,笔法老道,不可以等闲少年笔墨目之。”
林大春见张元忭对此评价极高,自然也不能往下拉太多,只是道:“行文尚且不论,少年人有这般胸襟抱负实属难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学纲领。朱熹认为“亲民”既是“新民”,意为带领生民图新从善。
从文义而言,新民是属于治国范畴,是君子出仕之后的阶段。
寻常生员仍旧还在“明明德”的自我革新,学习修业上,这也是进士们觉得生员格局普遍太小,需要多读史书、诸子古文的缘故。
徐元佐能够跳出这个框,直接从治国入手,阐述国家当如少年一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而达到千秋万世,止于至善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一切古文皆不离今世,以此文观国朝史事,的确是日新如少年。”林大春作为提学官,一要立足学术,二要立足为国储才,所以政治必须正确。
明朝在这点上的确如徐元佐阐述的,是个一直在“革新”的朝代。朱元璋时候就经常改变国策。建文削藩,成祖奉天靖难,其后安南的建省与废弃,下西洋的坚持和终止,盐法由开中到以银代米继而又要回复开中……重要国策始终是在变化之中。
有人讥为朝令夕改,如今徐元佐却用“少年日新”来解释这种现象。正是站在了国家朝廷的正确立场上。而且这文章也符合如今的大势——如今大势正是张居正要恢复祖制,强调考成法,约束官吏。
林大春说罢,收了卷子,道:“以此文与《幼学》,谁也阻不得你入学。只是我却不忍看大明多个庸碌之官。少个鸿儒种子。我且问你,你可想参加明年的乡试?”
又是一个早已经泄题的问题。
徐元佐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斩钉截铁道:“小子有心在经世济民的学问上走得更深更远,生员足矣,弱冠之前并不想再钻研时文。待弱冠之后,学问有了根脚,上可佐君王,下可安黎庶,如此才愿下场考试。谋个身前身后名。”
林大春大喜,道:“我既担心你过于执着功名,枉费了天资,最终碌碌无为。又怕你天资过高,一心于学,以至于颠倒本末,落入隐逸之路。既然你已经想得如此周到,我便点你个道试案首。只盼你不要忘了今日对我所言。”
张元忭一旁笑道:“徐案首,我却是个证人呢。”
徐元佐当即拜谢道:“承蒙大宗师错爱。小子何以为报?唯有奋发读书,有益道德文章!”
一时皆大欢喜。
回到了张宅,张氏父子特意设宴为徐元佐庆祝,反倒是徐阶只是简单叮咛几句,要他好生读书云云。
徐元佐完成了自己人生中头一桩真正的大事,总算是放下心来。现在好歹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了。就算此生无缘举人,问题也不大了。
当然,如果日后机缘巧合,还能摸个举人当当,那就更完美了。
至于进士。徐元佐真心是觉得太过遥远。
就好像一个成绩在二流学校排名二流的学生,考虑清华北大如果抢着要他,该选择谁……实在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