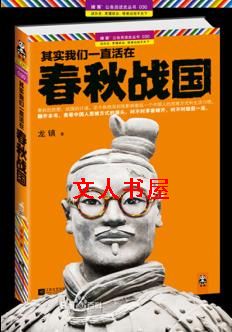我们-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识到,如何使幸福回归……不,您再听我往下说!那时候的上帝和我们呆在一起,坐一张桌子。真的!是我们帮助上帝,才彻底制服了魔鬼——就是他撺掇人去犯禁,去偷吃那害人的自由的禁果。他是那阴险毒辣的蛇。可是我们抬起脚用大靴子照它脑袋咔嚓一踩……好了,重新又有了天堂。于是我们又像亚当、夏娃一样,无忧无虑,纯洁无瑕。我们不必费脑筋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一切都很简单,像天堂一般美好,像儿童一样单纯。大恩主、机器、立方体高台、气钟罩、护卫局人员——这一切都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和纯洁。因为这一切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只有古代人才爱没完没了地论证,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什么是伦理,什么是反伦理……好了,就这样,总之,写一部这样的天堂史诗很不错吧,对吗?而且语气还应非常严肃……您明白吗?很不错吧,啊?”
怎么会不明白呢!我记得,当时我曾这样想过:“别看他长得歪瓜裂枣其貌不扬,脑袋倒真好使。”难怪他和我——真的我——很要好(我至今还是认为,过去的我是真我,目前的一切都是病态的)。显然,R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他搂着我的肩膀,哈哈笑了起来:“啊,您呀……亚当!对了,顺便提一下夏娃的事……”
他在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看了一下,说:“后天……不不,两天以后,O有一张来这儿的粉红票子。您怎么样?还和以前一样吗?您愿意让她……”
“那还用说,这很明白嘛。”
“我就这么对她说。要不然,您知道吗,她自己还不好意思……我告诉您,怎么回事,她对我只不过按粉红票子行事罢了,可是对您……但她又不明说,是哪第四位插进我们的三角。
风流汉子,您坦白吧,她是谁?”
我心里的帘子哗地掀了起来——我又听见了丝绸的悉簌声,看见了绿色的酒瓶,她的嘴唇……突然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要是忍住了不说该多好!):“告诉我,您尝过尼古丁和酒的滋味没有?”
R抿了抿嘴唇,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我听得一清二楚:“虽说你是我的朋友……可还是得……”他回答我说:“怎么说呢?我自己——没有尝过。可是我知道有个女人……”
“I,”我喊了出来。
“怎么……您,您也和她有来往?”他嘎嘎大笑,气都喘不过来——马上要喷唾沫星子了。
屋子里的镜子挂在桌子那边,我坐在软椅里,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额和眉毛。
这时我——真的我——从镜子里看见两道剑眉的直线歪扭着,拧着,颤个不停。那个真我还听到一阵野性的嚎叫:“‘也’是什么意思?你说,‘也’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要求你说!”
R两片厚嘴唇紧紧抿了起来,眼睛也瞪得圆圆的……
我——真的我——狠狠扭住另一个我的衣领,就是那个野性的、满身毛发的、气喘吁吁的我。真的我对R说:“看在大恩主的份上原谅我吧。我病得厉害,睡不着觉。我这是怎么啦,我都糊涂了。”
厚嘴唇上掠过一丝笑意:“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能理解!这些我都并不陌生……当然,是从理论上讲。再见吧!”
走到门口,R像个黑球似的又转身回过来,走到桌子跟前,朝桌上扔下本书说:“这是最近写的……专门带给您的,差点儿忘了。再见……”
说着又喷我一脸唾沫,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也许准确些应该说:我和另一个“我”单独在一起。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软椅里,好奇地看着我(我自己)在床上抽风。
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我和O整整三年能生活得如此和睦,而现在突然只要有一个字提到那个I……难道爱情、嫉妒这些疯狂的东西,不仅仅在古人愚蠢的书里才有?主要是我出了问题!方程式、公式、数字我都明白,可是对这些东西却一窍不通!
一无所知……明天就去找R,告诉他……
不,那不是真心话。明天也罢,后天也罢——我永远不会去。
我不能也不想见到他。完了!我们的三角垮台了。
我独自一人。傍晚。扯起了薄雾。金光灿灿的乳白色天幕遮住了天空。要是能知道那里高处是什么该多好!但愿我能知道,我是谁,我是什么人?
记事十二
提要:对无穷大的限制。天使。对诗歌的思考。
我总觉得,我身体会好的,能恢复健康。近来睡眠很不错。不再做那些梦,也没有别的什么病痛。明天可爱的O要来看我。一切都将是简单的,规矩的,有限的,就像一个圆圈那样。我不怕“限制”这两个字,因为人最高理性活动的目的,就在于要对无穷大不断的限制,在于要将无穷大化小为灵活方便的、易于接受的微分。我热爱的数学的无与伦比的美也正在于此。而她正好对这种美缺乏理解。不过,这仅仅是偶然的联想而已。
这些都是我坐在地下铁路车厢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想到的。伴着轰响的车轮声,我抑扬顿挫地低声吟诵R昨天送我的《诗集》中的篇章。这时,我感到,我背后有个人小心翼翼地探过身子,从肩膀上低头看着我打开的那页诗。我没有回头,只用眼睛的余光就膘见了那一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朵和双曲线身影……是他!我不想打扰他,装得无所察觉的样子。我不明,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我进车厢时,好像并没有他。
其实,这不过是件小事,对我却起了很好的影响;可以说,使我信心倍增。当你感到有双警惕的眼睛随时爱护地关注着你,不让你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让你半步也不偏离正道,这时你会感到多么愉快。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于多情,但是我脑子里总浮出这样类似的比喻,例如把护卫局人员比喻为古人曾幻想过的天使。古人许多美好的憧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我感到我背后站着一个天使般的护卫局人员时,我真感到了十四行诗《幸福》的魅力。我想,如果说,这首诗是兼有诗意美和思想深度的难得珍品,这样的评价是不会错的。下面是开头的四行:
二乘二是永恒相恋的数,不离不分融进四,炽热相恋的男和女,正是二乘二永不分的数……
下面的诗句,也都是关于明智的、永恒的、幸福的乘法口诀表。
任何真正的诗人无疑都应该是哥伦布。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这块大陆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但只有哥伦布才发现了它。在R…13以前,乘法表也早就有了,但只有R…13能在数字的原始丛林中发现新的黄金国①。确实,哪里还能找到比这美好的世界更智慧、更美满的幸福。钢铁会生锈。古代上帝创造了古代人,也就是说,创造了会犯错误的人——当然,这么一来上帝自己也犯了错误。乘法表比古代上帝更聪明,更准确可靠些。因为乘法表从来(请注意)从来不出错。按乘法表严整、永恒规律生活的数字是最幸福的。这里没有犹豫,也不会发生迷误。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道理也只有一条。真理就是二乘二,正确道理就是四。如果这两个幸福地、完美地互乘的两个二也考虑什么自由(换句话说,它们明显地想得不对头),难道这不荒唐吗?R…13抓住了最重要、最……对此我绝不须再加以论证。
这时,我后脑勺感到了护卫局的天使呼出的暖融融的柔和的鼻息,接着又转到了左耳。显然,他发现我膝头的书已经合上,而我自己早已遐思飞越。其实即使他要我打开脑子里的书页,我也乐于立即从命。这样做使人感到平静和愉快。我记得,当时我还回了一下头,眼睛定定地、询问地望了他一下。可是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也不想弄明白什么——他一句也没问我……我不相识的读者们,我只能向你们来倾吐这一切。现在你们对我来说,也像当时的他那样,无比珍贵,既近在咫尺却又高不可攀。
我由一个个人——R…13扩展开去,想到了宏伟的整体——我们的国家诗人和作家学院。我曾想过,古代人怎么没有发现他们文学和诗歌的极度荒诞可笑呢?文艺无比巨大的力量,竟被他们毫无价值地浪费掉了!作家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简直可笑!同样滑稽、荒唐的是,在古代世界,海洋竟毫无目的地昼夜不舍地拍激海岸,那潜藏于水力中的巨大能量只用来激发恋人的爱情。而我们却从海浪的絮絮情语中,索取了电力。我们把狂啸发威像野兽一般的海洋,变成驯顺的家畜。对狂野不羁的诗歌,我们也如法炮制,驯化和制服了它。现在的诗歌不再是夜莺无所顾忌的啼鸣。诗歌是国家的工具,诗歌应带来效益。
我们有几部著名的《数学诗歌》,没有它们,试想我们在学校里能如此真诚、如此深挚地爱上算术四则吗?《玫瑰花刺》这是经典性作品,其中护卫局人员就像玫瑰花刺一般保护着娇嫩的国家之花,以防人们粗野的触摸……当孩子们喃喃诵读诗句“顽童顽童采玫瑰,花刺尖尖扎得疼,顽童失声噢噢叫,吓得急忙往家逃”时,当你看到孩子诵读时天真、虔诚的神情,任你铁石心肠,也会感触万千呢。还有那本《大恩主日日颂》,谁读过后会不对这位最伟大的号码的忘我劳动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那部猩红得痉人的《法庭判决书集萃》、不朽的悲剧《上班迟到的人》,以及案头必备《性事卫生诗抄》!
我们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美都永恒地镂刻在金子般的诗歌语言中了。
我们的诗人已经不再生活在幻想的天国,他们降到了人间。
他们和我们一起踩着音乐机器进行曲那严肃、机械的节拍,步调一致地踏步前进。他们诗的灵感来自早晨电牙刷的簌簌声,来自大恩主的机器火星飞溅时可怕的喀嚓声、大一统王国国歌庄严肃穆的回响、晶亮的夜壶里不堪入耳的响声、窗帘垂下时使人耳热心跳的咔咔声,还有最新烹饪指南轻松快活的语言和街上膜片的极其微弱的震颤声——它们都是诗的灵感的泉源。
我们的众神就在这里,在人间,与我们同在;他们在护卫局、在厨房、在工厂作坊、在厕所。众神变得和我们一样了,apro②我们也变得和神一样了。不相识的星球读者们,我们就要去你们那里,要使你们的生活变得和我们那样无比理智和准确划一……
【①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想象中的神奇、富庶的国家——黄金国。】
【②拉丁语,意为:所以。】
记事十三
提要:雾。你。荒唐透顶的事。
天蒙蒙亮,我就醒了。一睁眼就看见一大块玫瑰色的坚实的霞天。一切都很好,圆圆满满。晚上O要来。我身体当然已经好了。我微微一笑,又睡着了。
起床铃声响了。我穿衣起床。再一看,天气大变:从天花板和四壁的玻璃望出去,左右前后到处都弥漫着云雾。雾气缭绕,一片混沌,狂乱的云层愈来愈厚,然后又变淡,愈来愈近。天地之间已茫无界线,一切都在飞快地运动,融化,坠落,什么也抓不住。房子看不见了,玻璃墙在迷雾中消失了,就像晶盐在水中化开一般。如果站在街上,你会看到屋里黑影憧憧的人影,就像浸在荒诞的奶液里的悬浮粒子,有的沉在低处,有的高些,有的再高些——在十层楼。一切都烟雾腾腾——也许那里是一片听不见声音的大火。
到正11点45分的时候,我有意看了看表,想抓住几个数字,让它们来救我一把。
按守时戒律表,14点45分应该是体力劳动时间。出去劳动之前,我急匆匆回屋一下:突然,电话铃响了。那说话的声音像一根根长长的针慢慢扎进我心里:“噢,您在家啊?我很高兴。请在街口等我。咱们一起出去一次……就这样,到那儿您就会知道去哪儿。”
“您明明知道,现在我要去劳动。”
“您明明知道,您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再见,两分钟以后……”
两分钟以后,我已站在街口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告诉她,我听命于大一统王国,而不是她。还说什么“按照我说的去做”……
听她声音还很自信。好吧,现在我要严肃地跟她谈谈……
一件件潮雾织成的灰制服急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一秒就过去了,然后马上就在雾中融化了。我眼睁睁地盯着表;我变成了那根尖尖的、颤动着的秒针。8分,10分……12点差3分,差2分……
不消说,去劳动,我已经迟了。我真恨透她了。可是我应该让她知道……
在街口的蒙蒙白雾中,露出两片血红的嘴唇,就像用尖刀拉开的口子。
“我好像耽误了您的事儿了。不过,也无所谓。现在您已经晚了。”
我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