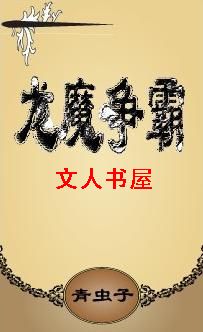狗日的战争-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多个弟兄原本也突出来了,因为咱俩被炸翻了,二子和陈玉茗带他们折回去救咱们,就没回来几个!”老旦越说声音越低,微带哽咽,他怎能忘了那一幕呦。
“弟兄们呐……”杨铁筠轻叹一声,像是怕泪掉下来,就闭住了眼。
“连长,老哥,不说这些了,弟兄们没个啥,打鬼子哪有不死人的?没有你们俩,咱们又怎么过得来?大伙怎么舍得你们被鬼子捉去?二子哥见你们被炸翻了,他一下就跳车了,他跳了我就跳了,不少弟兄就都跳下去了……我们都等着你俩好了,领咱们回武汉呢!”黑牛又要哭了。
“好了黑牛,不说了,连长还累……”陈玉茗语气镇静,他永远是个不掉泪的。
二子悄悄钻了进来,攥着只漂亮的山鸡。他头上结了疤,黑乎乎的像顶着条蜈蚣。二子也不言语,笑呵呵冲老旦和杨铁筠举起断了脖子的山鸡。老旦冲他笑了笑,杨铁筠只点了点头,又喝了口水问:“地图呢?”
“给丢在半道上了。不过乡亲们可以做向导,她们是从咱到的那个村子逃出来的,在这里躲鬼子,她们知道出去的路。”老旦见杨铁筠这么快就放下了自己的伤,立刻考虑任务了,对他更添几分敬佩了。
“日军有没有跟进来?”
“跟进来了一些,山很大,估计暂时钻不到这么深。”老旦说。
“这些女人……”
“就是俺说的乡亲们。”
“哦……”杨铁筠的脸色开始泛白,老旦立刻示意大家散开。
“要注意警戒,夜间不要起火……”杨铁筠说完这话,眼见着要晕过去。老旦对大家挥了挥手,大家就退出去了。他轻轻搀着杨铁筠躺下,听见他长长出了口气。
“我做了个很长的梦,梦见在家乡的田里割了十几亩水稻,一块块的,都是我自己割的……”杨铁筠闭着眼说。老旦木然点着头,不知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
山里林密草深,日清夜静,比起那恐怖的伤兵医院,简直是天国的日子。这里吸口气都像是营养,更别说到处都有的野果野菜。有伤的安心调养,没伤的吃个膘肥。这么惬意地待了半个多月,大伙精神振奋。几个老兵深谙打猎,野猪野鸡、山兔地鼠,连穿山甲都成了锅里的美味。女人们熬的草药和各种粥汤也百喝不厌,养得士兵们红光满面。二子开始调笑几个俊俏的女人,厚脸皮的伤兵故意赖在床上。老旦的皮就像锤不烂的土地,烂成那个样子,竟也悄悄平复,胃口还越来越好。他只讨厌这没完没了的雨,到处都湿漉漉的,裆里永远都不自在,一点不像板子村那般爽气。二子每天穿条裤衩走来走去,和他说着哪个女人好看,哪个女人脚小,哪个女人的奶子最为圆润;还说有女人给找来了山里的野烟叶,等太阳出来晒晒就能抽了,另一个女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像你家隔壁的山西女人看她那爬灰的瘸腿公公。
二狗和大薛去外面摸情况,一大早跑回来,说出了山口便看见鬼子的大部队在往西边开拔,有很多飞机飞向武汉方向,看来狗日的飞机场又能用了。山口有鬼子的炮楼子,上面有重机枪,想从原路出去是不能的。老旦听着心堵,想琢磨一阵再和杨铁筠说。这么个四边不靠的地方,往哪边去都是鬼子,这可如何是好?
梅雨季节,入夜天就变凉。一场雨下了一宿,就没个完了,每天细刷子一样扫拂着山林,雨丝随风飘来摆去,时密时疏,把这山泡了个透,山上时不时有蓄积的水流冲将下来,下来的水干净透亮,带着奇怪的丝丝香甜。老旦纳闷这山这林,这么冲下来的水,在板子村非黑即黄,只带着恶心的土腥和驴马的粪臭,哪里能喝呢?
女人们看似细弱,却多是干活的好手,尤其那几个岁数大些的,胸大嘴大嗓门大,本事也大,她们能手把手地教战士们砍树削桩搭草房,柴刀抡得忽忽带风,彪悍得战士们都怕,这可是地道的男人手艺。胳膊粗的竹子砍下来,战士们一捆捆背下来削尖了,在地上打成三排结实的桩子,桩子上再搭上网状的木架子,再一层层扎上去,就成了个蝈蝈笼样的悬空房子,编的草席子盖上去,再扎上一簇簇干草,就是房顶和四壁了。战士们对这些灵巧坚韧的女人们钦佩不已,没多久钦佩就变成稀罕,稀罕再变成垂涎,垂涎很快就变作不要脸的溜舔,纷纷找着各自的目标伺机歼灭,帮她们挑水煮饭抱娃,自任了一堆干爹干哥干弟弟。阿凤定也有不少人盯着,二子就不怀好心,时常和老旦聊起她。老旦不上这个当,没事就走出去溜达,到杨铁筠那儿说说事情。他见阿凤让战士们在山脚下挖了三个很深的坑,丢入很多长满小洞的石头,蓄积起山上下来的水,能喝能用的,战士们不用在半夜到湖边打水,鬼子巡逻艇神出鬼没的,被发现就糟了。
这天,老旦一早醒来,雨还在下,山里沙沙地响,像大片的蝗虫在啃地里的庄稼杆子。窗是暗的,却是绿的,雨虽然烦,却把那些绿浇得鲜嫩。这破屋里一切都蒙着潮气,衣服和床褥发着潮臭的霉味,一拧都恨不得出水。愈合的伤口十分娇气,在这潮湿天气里奇痒难耐,身上的痒勾起了心里的痒,心里的痒弄得无处不痒。老旦抓不到挠不着,床上床下地别扭,出门更是无趣,连二子都懒得过来,谁还想出门溜达呢?老旦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看看天,一会……还是看看天,烟斗早就没了烟,烟叶子不得晒,早早发了霉,嘴里心里乏味如寡淡的米汤,着实没有滋味。
老旦望着一溜竹木房子,隐约听见男女的嬉笑,笑也是抠着嗓子的,不敢大过雨声的。老旦宽慰地叹了口气,杨铁筠的房子静默无声,窗也没开。老旦昨天没去找他,他需要安静,等着腿伤长好,等着心情康复,等着一个合适的计划冒出来。而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想不了这么多,他们没人比杨铁筠伤重,他们无人比杨铁筠心焦。那些无家可归的女人们早已过了悲伤,看见这些天降的男人,更觉得是可贵的希望。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竟相依为命呢。而这命也是从阎罗殿门口捡回来的,亲友与战友不断死去,他们只能在沉默里或者坚强,或者死去,或者拉着手往前走。几个兄弟已经在和女人们眉来眼去,也有的动手动脚了,开始你情我愿了。杨铁筠看得分明,却没吱声。老旦看得仔细,也没干涉,劫后余生的男女,谁在乎那扎不住的篱笆?破了就破了,弄了就弄了。大家都等着沉默的杨铁筠说出成算,条件一允许,他一定会带大家离去。带她们一起走是妄想,就像盼着麦子地里长出水稻,一个都不可能。这深山里的苟且,并非这些军人既定的命运。
杨连长呢?会稀罕上一个么?这问题颇为有趣。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猜过,女人一个个量过,竟挑不出个合适的。乌龟吃了萤火虫,老旦心里亮堂得很。跟连长可不能比!人家出身就好,读过大书留过洋,委员长身边最忠诚的部队骨干,必是将军的料,元帅的材。杨连长好像有女人,却不是乡下人眼里的“女人”,那定是头发梳得干干净净、裙摆毫无皱褶、皮鞋晶亮、走路便能醉人的美妮子;美还不够,一定是读书识字,拿笔便可挥毫,细皮嫩肉里藏着大家气韵,是知书达礼的娇娃子;又美又娇也还不够,定还有三分飒爽,八成就和杨铁筠一样,抬手一枪就能敲个麻雀啥的。老旦越想越羡,站在窗前鼓着腮帮。一个女人光脚走来,披头散发咧着嘴,过去时挠了挠屁股,抠了抠屁眼儿。老旦一口气全喷了,转身时却又想起,这里有几个女人很看得过,比如阿凤,比如阿果,还比如那个半大不大的潘寡妇。这都是板子村必会抬举的姿色了,这几个也都算得上干净,阿凤尤其是手不沾泥的,衣服上有片叶子都要摘去的。那些他记不起名字的,大多是破衣烂衫的,虱子一胳肢窝的,喂孩子更不避人的,擦屁股还用草棍的。但即便如此,这些村姑仍比板子村不知强了多少,几个月洗一次澡的山西女人来了必定羞愧得跳了湖,翠儿来了也要在小竹房子里闭门思过的。杨铁筠当是不把这些女人看上眼,看几眼也是假的,那是城里人的礼貌,和看你家门口那只友好的狗是一个意思。弟兄们可是真的看,恨不得看到衣服里去肚子里去,老旦对阿凤的看更是真的看,每天都盯着看,梦里剥光了看,一天看不见心里还有些抓挠了。袁白先生说过,管天管地,任谁也管不了男人的蛋,女人的裆,男人女人爬上炕。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日就是五千年。这边是干柴,那边是烈火,凑在一起棺材里都能烧起来。这都是两厢情愿的事,这又有啥不好的哩?一个个朝不保夕的命,一天天擦来蹭去的人,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山沟子里的国仇家恨,压不住肚子里的烈火干柴。阿凤日日来照料自己,伤都好了她还是每天过来,而自己见了阿凤,也是个心里长草毛糟糟的,她一推门进来,就像鸡毛掸子捅进心里了。
让纪律喝尿去吧!今天她会来么?
阿凤帮他清理伤口的时候从不主动说话,不管把他弄疼了还是舒服了,她只是看着伤口,脸上就算红白黑绿地变来变去,也只看着伤口。她断不会问一句什么,大多是老旦说一句她答一句,老旦问半句她就答半句,老旦胡问一嘴,她也胡答一嘴,答完了该答的也就没什么了。老旦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总想多和她说说自己的……光荣。他身上那些伤疤,有枪眼儿有刀口,还有烧的呢。他一直等着她问出关于那个伤疤的故事。但她从不,那些伤疤就像蚊子包一样不值一提。而老旦却看见她的痕迹,她低头摆弄时,时常露出胸前奶间那条红色的蜿蜒下去的胎记。老旦常想象它的长度,将它想成红色的带子河,翻山越岭地流到一个隐秘之地。想到这结果时他血流加速,呼吸仓促,手心也出了汗,七八个兔子在心里乱蹦。他大腿内侧有个洞穿的枪眼儿,不知哪个鬼子打出这么玩笑的一枪,再抬一寸老旦就成了小旦或是扁旦。这地方好得快却痒得很,每次阿凤要收拾它都会深吸口气,小手抓耗子似的小心探下。每逢此刻,老旦埋伏在旁的东西就起身敬礼,隔着裤衩和她打个招呼。这感觉顶得上两针麻药,盖住了换药的疼,驱走了心里的痒。阿凤每次定看在眼里——躲也躲不过去啊,就像老旦躲不开阿凤那条胎记。虽不言语,阿凤的脸会浮起红晕,手脚反倒麻利起来,并不会如老旦的期望那样碰触什么。老旦不说话,她就不搭理,换完药就收拾篮子走人,出门的时候也就是笑笑,像对他笑,也像是对这房子笑。最近天气潮,洗过的绑带她便挂在屋里。关在屋里也干不了,她自己的衣服也是湿乎乎的呢。
老旦正想着,竹门吱呀就响了,阿凤拎着筐钻进来,穿着绿色的露肩对夹小麻布褡裢,下面是条灰色灯笼裤,她对他笑了下,在桌边放下了手里的筐。
“又来了……”老旦说。
“嗯,来了。”她笑了笑。
“差不离好利索了。”
“嗯,再看一眼,天儿不好,怕复发。”
“真劳烦你……”
“不说了,躺下吧,再换一次。”阿凤在盆里倒了水,洗手。
老旦坐在床上,脱去上衣,撩起肥大的裤腿。
“这儿还有点肿。”阿凤摸着他背后一处,抹了抹,按了按,用一块小布擦着。
“没啥事了,就是自个挠的,你莫再费心了,俺可以收拾自己。”老旦挺直了腰。她的手在几个疤上游走。他知道她会怎么摸,先是后背,从上到下,然后是腰,然后是腿,最难堪的那处总放到最后。
“天气不爽快,口子容易烂,你别老挠啊。”
老旦应了一声,说:“这次小意思,俺在武汉伤得重,肿得多了十几斤肉,绑得像个粽子,不也活过来了?俺命大着呢!”老旦故意扭着脖子,摆出神鬼不畏的劲儿。
“这儿什么药都没有,见那大黑蚊子了么?毒大着呢,在你伤口上叮几下,肉就会烂的!”阿凤第一次自己说这¨wén rén shū wū¨么多,老旦暗喜,忙不住地点头。
老旦上半身的伤口都结了痂,有的已露出白嫩的新肉。腰上那个弹片钻的小窟窿凹了进去,瘪进去指肚大一块儿。虽然有脓,毕竟合了口。唯独右大腿下侧方这个仍然肿胀,窟窿不大却难伺候,虽然摸得到,老旦却看不着,脑袋总不能伸到裆里去。裤子揪上来,那里撅乎乎的像个小嘴,仿佛和谁怄气。老旦知道做梦时常不老实,挠那玩意的时候顺道就摸过来,长好的又抓烂。这无关大碍的伤口并不影响那玩意儿,动不动就撅起来,更别说被阿凤在旁摸那么几下。
“阿凤,你们住在一起,听谁的?听哪个大姐的?”老旦见她要下手了,忙问句别的话,“都是女人,会不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