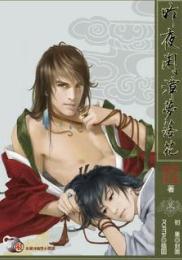落花谣-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性了。
这样就到了盛夏;十四也没让人带信,就到了杭州。
那日我才起来,懒懒散散地在吃了早饭,正为打发日子发愁,一转头竟见十四斜斜地靠在门边,容颜清俊,一双黑黝黝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嘴角是我最熟悉的慵懒笑意。
我才咧开嘴想笑,却忽然想到刚开春时自己的乞求他理也不理,心里便懊恼起来,冷着脸冲他微不可见地点了一下头。
十四的表情有些错愕,薄唇微微一撇,道,“哎,我的姑奶奶,这又是谁得罪你了?难为我这么大老远赶来看你,合着热脸就贴了这么一张冷屁股。”
我听了十四的话,心里不免冷笑,贵人果然多忘事;再把他的话往深里一想,方觉大为不妥,脸上瞬时便有些发臊,啐道,“什么话,也不怕下人们听着笑话。”
十四笑嘻嘻地凑到我跟前道,“还好我早就遣散了下人们,不然给他们看到堂堂十四爷竟是这幅猥琐样,可怎么是好?”十四言罢自己一笑,却不见我跟着笑,便抓起我的手握在掌中,问;“花楹妹妹又怎么了?算我错了,我赔不是还不行?”
我听到这句十四从小到大不知说过多少回的话,心里止不住地叹息,绷不住还是笑了出来。我和十四年岁相差不多,打小就爱闹,只是不管错在谁,每回他都是这样赔着不是……我抬头望着眼前的十四,高大英挺,已是成熟的男子,难道疼我的心竟反而少了?想到这里,我微微叹了口气,幽幽道,“我开春写信给你,说想回北京,你为什么不搭理我?”
十四听了便皱起眉,神色有些诧异,凝神想了一阵,才慢慢开口道;“信?我可没收到你的信,你写了信给我?”
没看到信?我也诧异地望向十四,那日我不是亲手交给望月的?“不可能,望月说她亲手交给杨顺昌的,他不是专门为你传递信件的差使吗?”
十四听了摇摇头,道,“前阵子我跟前的人说杨顺昌病死了,这边的信差老早就换了人了,难道你竟不知?”
病死了?我诧异地望着十四,脑子里好似在煮浆糊,又见他极为确定地点头,心里便替那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难过起来。真是世事无常,好端端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那你给他家里抚恤银子了吗?还有……我的信呢?”
十四耸耸肩,两手一摊道,“天地良心,我可从来没见过格格你那封信,许是小杨并未来得及把信送到?我回去找人查查,丢了福晋的信,这可不是小事。”十四说完顿了一下,又道,“小杨家里我已经吩咐下面好好安置了,忠心为主的我断不会亏待,你放心吧。”
我点了点头,有些六神无主地坐在凳子上,心里有些憋闷,却又为冤枉了十四而愧疚。正在胡思乱想间,十四忽然蹲在我的面前,极为专注而温柔地望着我,握住我的手道,“想回北京了?”
“花楹丫头,想回家了?”直到十四第二遍问我之时,我才猛然反应过来。他在问我,他在问我!我连忙看着他的眼睛,重重地点头,好像生怕力道轻了他看不到。
十四见我这幅忙不迭的样子,眼圈竟然微微的红了。他站起身来,一把把我揽进怀里,伸手摸摸我的头发,轻声道,“好,我们回家。”
我静静地坐着,任由十四抱着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我和十四的距离是如此接近,我似乎已经不再排斥他的拥抱和他温暖的气息。而可笑的是,在另一些时候,我们的距离却又渐行渐远了,不仅是两个人实际的距离,而是我们的心。
气氛在这一刻说不出的宁静和祥和,然而我终究还是推开了他的怀抱。可是十四却在笑着,微微的羞涩,微微的满足,温言道,“只是现下天气炎热,你身子又虚,怕是不宜上路。不如养好身子,到入秋再起程。”
我听了十四的话,呆了半晌,才开始拼命地点头,一时间几乎喜极而泣。
十四在杭州休息了几日,每日不过与我下棋饮茶。有时相伴在杭州城里溜达。几日后十四动身回京,我一直送他到城门口。
十四把手里的马鞭交给身边的小太监,伸手握住我的肩膀,眼睛盯着我道,“照顾好自己,养好身子才准回去。”我点头应允,管他什么条件,只要能让我回到北京城,再难的事情我也尽力做到。
十四点点头转身跨上马背,却仍旧看着我,那幅神情倒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我如今看惯了他意气风发的样子,哪里见过这样的神情,便笑道,“你先回去,我过几日就能回来。”
十四微微笑了一下,却没搭我的话茬,道,“多谢你能相送。”言罢便挥鞭而去,侍从们连忙尾随于后,驿道上扬起了轻轻的尘土。
我看着十四远去的身影,微微笑了一下,心里默道,“北京城,等我回来;胤禛……等我回来。”
卷三:曾经沧海难为水 卷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第一百一十四章 失望,希望,事情的真相
卷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第一百一十四章 失望,希望,事情的真相
日子一天天地过,天气慢慢转热又慢慢转凉,眼看着夏季将尽,金秋欲来。秋季是杭州极美的一个季节,白乐天有诗云,山寺月中寻桂子,说的便是这样的一种美。
因为与十四的约定,自他离开杭州那日起,我便开始注意保养身子,常常跟城里的名医会面。这几个月来悉心调理,加上自己心气又好,少了心事觉也比往常睡得好,身子竟是这些年来难得的好。眼看节气逼近入秋,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便嘱咐望月慢慢开始打理东西。
在我的心里,喜殊自然是不能回去的,她跟孙济常已经办酒成了夫妻,虽是仍旧每日过来伺候,虽是个离不开的得力助手,然而我要去的是千里之外,纵使再不舍,总不能还得人家夫妻分离,天各一方。
只是我的话刚刚起头,便被喜殊极为坚定地拒绝了。
“奴婢自然要跟着福晋回去的。”喜殊极为正式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福晋出来这么些年了,家里的丫头婆子们一定换了不少。奴婢也要看看那些下人们的手脚,差劲的还少不了要细细调教一番,总不是让主子再倒过去调教下人们。”
“有望月在,你还怕什么呢?”我。心中感动,微笑地望着喜殊,温言安慰着,可是心里却也不得不承认,喜殊的精明和能干,是远远在望月之上的。
哪知喜殊还是微微摇了摇头,“奴。婢也知道福晋是心疼奴婢,只是还请主子成全奴婢的这番孝心,不看到主子安然地生活,做奴才的怎么能离开呢?那是不忠不孝不义啊。”喜殊说完见我微微皱着眉头,便又忙道,“奴婢已经和济常商量过了,奴婢陪着福晋回去,精力都安顿好了,济常自会派人来接。”
听到这里,我终于还是不能再。拒绝喜殊的一番心意,摇着头应了。
立秋那日我在房里给十四写信,一面写以免在心。中暗暗地想,这个人大概圣眷正隆,忙得昏天黑地,早已忘了我的请求。不过他不请,我自己要求便是。
信方才写了一半,望月进来说老陈求见。这个老陈。谨小慎微,平日里难得跟我说几句话,今日竟主动求见,倒是稀奇。
我心里一面暗自纳闷,一面让望月带他进来。
老陈躬着身子走进来,低着头,有些畏畏缩缩地。道,“夫人,京城来的消息。”言罢顿了一顿,又道,“准噶尔入侵西藏,战事吃紧。皇上命十四爷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授正黄旗,称大将军王。十四爷已于今日动身。”
这个十四,这么。大的事情竟也不跟我知会一声!我听了心中先是一惊,不觉微微逸出惊叹声,又因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半晌方才道,“知道了。”
但老陈听了我的话,并没有出去的意思,接着又道,“十四爷因不放心夫人的身子,前日里捎信过来,请夫人仍在杭州休养,待爷班师回朝再来接夫人回去。”老陈的声音到后面低了许多,但我还是一字不漏地听进心里。这是十四的手段吗?最后一日方告知我不准回京,让我连个争执的机会都没有,原来我还是被拘禁在杭州。
想到这里我心里早已是怒火冲天,不觉怒道,“他去打仗,把我留在杭州做什么!我该回去时自然要回去,难道还要受制于你不成?”
老陈听了我的话,没有半点多余的反应,只是将身子躬得更低,极其谦卑地道,“小的不敢,只是十四爷有言在先,做奴才的不敢不从,还请夫人体谅奴才对爷和夫人的一片忠心。”
老陈这话面上说得好听,可是意思却很明白,就是没有十四爷的命令,便是决不准我离开杭州的地界半步。
我一时间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转眼一瞥又看到望月和喜殊这些日子打包好的东西,只觉得自己上了当,心中又是愤怒又是难堪,抓起桌上的镇纸砸在老陈脚下,怒道,“你给我滚出去!”
老陈还是躬着身,却是不为所动,向我打了个千便出去了。
自打那天开始,我便处于老陈的严密监视之中。无论到哪里,似乎都不能躲避身后躲躲闪闪的目光。我起初还是愤怒,后来便渐渐习惯了。老陈一家都是十四的人,十四说的话便是金科玉律,我说起来虽是主子,却不过是站在老虎身前的狐狸,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
安静下来之后,便不再生那些个没用的闷气,我悄悄地分别找来喜殊和秦旺,让他们各自去打听关于十四出任大将军王领军西北的事情,结果两边得出的信儿完全吻合。原来西北的战事年初方才开春之时便有,准噶尔进攻西藏,藏王杜伯特蒙古人拉藏汗请求康熙发兵救援。康熙当时只命侍卫色楞会合驻青海西安将军额伦特援助,岂料后来战事紧张,便预备派十四亲自挂帅。这个想法确定是暮春的事情,我听了只觉一颗心不知沉到了什么地方,暮春之事,那就是说十四来杭州时早已明了即将出征之事,那么接我回京也就不过是一句搪塞之语?
我暗暗冷笑,是了,他出征西北,怎会放心让我这个不守妇道的人回到北京呢?只是十四也过于辛苦,把我扔在杭州自身自灭便是,何必大老远地亲自跑来,给我希望复又让我失望,难道他憎恨我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是极大的,心情一直愤懑抑郁。
秦旺对于这件事情思忖了一阵,便直接道,“福晋,向王爷求助吧。十四爷在杭州城里一定安排了不少的人手,纵然奴才会功夫,可是带着女眷,硬闯总是不行的。”
求助于胤禛?我低着头想了一阵,却是不住地摇头。十四如今对胤禛是最为忌讳的,如果我硬要回到北京,那也罢了;可是如果是在胤禛的帮助之下回到杭州,我不确定十四在激怒攻心和嫉妒的交织中又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来。我不由地想到了十三,心中微微涩然,胤禛身边不如八阿哥他们人才济济,我不能给他苦心经营的大业再造成任何的破坏了!
秦旺在我身边的年数久了,对于我和胤禛的事情又是一直了然于胸,见我不住地摇头,便也猜到了我心中的想法。他微微叹了口气,仍旧劝解道,“福晋,王爷未必会用怎样的强制手段……”
“可是如果我求助于他,他便是没有手段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是吗?”我苦笑着反问。
秦旺默默地立了半晌,终究也是微微蹙着眉不语,的确,作为一颗胤禛精心培养的钉子来说,他对自己的主子是有所了解的。以胤禛的性子和城府,冷漠和狂热夹杂着,我们永远猜不出他在一个特定时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那日我又在窗前发呆,喜殊端了杯红枣茶进来。茶杯放在桌上,人却没有出去,立在我身后,半晌却没有言语。
我回头,一眼看到她低头思索的样子,便问,“你有话要说?”喜殊咬咬嘴唇,眼睛盯着我,欲言又止。
我知她一定有要紧的话,便道,“有什么话,只管说便是。”她于是又走近一步,低声开口道,“奴才想替格格引荐一个人。”
我听了心里奇怪,便问,“谁?”喜殊轻轻道,“四王爷派来的人。”
我听了半晌无语,整个人却是如坠冰窖,心中瞬间涌起种种复杂的情绪,是震惊、是喜悦还是恐惧,一时间只是百味杂陈,无可分辨。算起来喜殊在我身边已经有十几年了,除了听雪和望月以外,她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而且在到了杭州的这几年里,她为我出谋划策,为我尽心竭力,其实我对她依赖和信任的程度甚至已经隐隐在望月之上。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又是胤禛在我身边埋下的另一颗钉子?
我的心被惊得有几分木然,口中开始一阵阵地发苦,就连脸上也开始不自然地扯出几分苦笑来。
“原来你是他的人……”我有些木然地说,一面又有些恍然大悟,怪不得她一直积极地为我筹划收服江南三家织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