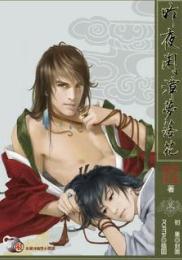落花谣-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氖虑椋鞘强滴踔概傻娜挝瘢渌氖虑樨范G几乎已经达到了不管不顾,不听不看的地步。虽然有些茫然,但是胤禛的用意,我还是渐渐猜出了一二分,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就是他所谓的放手一搏。可是这实在是一招险棋,因为打消康熙疑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深居简出、清心寡欲,但是也怕因此就淡出了康熙的视线,失去原本十分重要的注意。
局面似乎隐约陷入了一种怪异。地胶着当中,人们都暗暗地琢磨着康熙的心思,而我渐渐地把心定下来,不再像初到杭州时那样的彷徨,而是开始有些无耻地谋划着怎样把曹寅拉到我的船上。
秦旺也同样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在我布置山中楼之局的时候,秦旺就开始着手后面的一步棋。只是令我们都有些惊异的是,以秦旺的深谋远虑目光如炬,他在江浙一带进行了颇为详细地了解,却仍然没有在曹家发现一丝可疑之处。
“奴才没有找到什么疑点。曹寅在江南百姓中的声。誉极好,曹家故去的老太君多年来一直在乐善好施,直至今日还被江宁的百姓们奉为‘老祖宗’,遇到祭祀的时候百姓们更是会自发地前往祭拜……曹寅秉承着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是颇受爱戴。至于《全唐诗》,福晋您也知道,这在士子们心中是一件极大地政绩,只怕在朝廷心中也是如此。”秦旺轻声说着,脸上纵使波澜不兴,却也显示出了一丝暗暗地焦灼与挫败。
这么长时间的搜索探查,这么大的家族没有什么。疑点?我不怎么相信地眯起了眼,心中十分疑惑。秦旺见我紧紧盯着他,便苦笑道,“如果贪点钱也算问题的话……可是福晋,贪钱的事皇上心里肯定有数,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咱们匆匆忙忙抛出这张牌,只怕还会打草惊蛇。”
我有些默然了,知道秦旺所说不假,康熙南巡这。么多次,次次都是江南三家织造负责安排行程的,如果说三家织造用自己的俸禄接驾,恐怕会引起全天下的哗然。这样一个康熙知道,官员们知道,甚至天下百姓皆知的秘密,确实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参与到夺位的事情当中来呢?他们明明已经有了向八阿哥靠拢的倾向。”我苦思着,能够断定的事情却找不到证据,这让我十分头疼。
“确实不可能,所以更要找。”秦旺低着头轻轻嘀咕了一句,再抬起头来又恢复了满眼的自信,大有不把曹家拉下水誓不罢休之意。
秦旺说完这句话后颇为正式地跟我打千行了礼,接着便转身离开。
喜殊见我沉思不语,只是极为乖巧而温柔地帮我绞了一条微烫的面巾。我有些木然地接过面巾,轻轻地捂在脸上,任由面巾灼烫着我的脸颊,同时也给我带来几分清醒。
日子又过去了一些天,我心中有些焦躁,但还是耐着性子等待着,因为我相信秦旺的能力,用人不疑,我虽然跟政治的交情不深,但是这点起码的原则还是可以秉持的。
过了没几天,秦旺果然带着几分怪异的神色来到了我的面前,只是那表情确实很别扭,似乎高兴又似乎有些犯愁。秦旺本来是个城府颇深的年轻人,一直都有一种泰山压顶而不惊惧的淡然气质,似乎什么事情的发生都不大会令他感到震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极端情绪。但是少年毕竟还是少年,我看到了他难以掩饰的怪异神色,不由地露出了几分笑容。什么事情能让秦旺这样为难呢?我笑盈盈地看着他走到了我的面前,了然地眼神竟让少年的面颊微微泛起了浅浅的绯红色。
“奴才发现了一些事情。”或许是在我的目光下感到有些羞涩,少年秦旺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极为简单地说着,说完见我扬眉不语,便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压低声音接着道,“曹家和八爷的事情没有什么明显地头绪,只怕跟接触时间不长也有关系。只是……他们跟废太子的渊源却是极深。”
秦旺低低地点了一句,我却是整个人都微微一震,不由地睁大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黑脸少年。秦旺见了我的反应,便又微微羞涩地笑了起来,极轻地道,“奴才前几日跟一个官员去泡澡,那个官员在仕途上有些不得志,喝得多了些,便跟奴才不住地发起牢骚来,竟然……告诉奴才曹家曾经私下为那位打造过一方金玺。”
起初听到秦旺和人家去泡澡,我还是满脸的嘲弄,想着纯洁憨厚的少年原来也涉足了这样暧昧的场所,但是听到最后一句时却真的吓坏了。其实秦旺的话说得还算隐晦,但是我从小就生长在深宫里,对帝王的吃穿用度的东西都很熟悉,对那个“金玺”的含义更是十分了解。废太子竟然在康熙仍旧年富力强着的时候就私下打制了金玺,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早已超过了什么结党谋权之类的事情,如果给这件事定性的话,这简直就是谋逆的前奏!
“这事可信吗?”我有些木然地问。秦旺神色严峻地沉思了片刻,还是缓缓地点头,“那官员说得十分清楚,说他的一个老乡就是掺和到这件事里,被曹寅灭了口。死的人已经活不过来了,但是他却知道这件事情……”
“奴才也觉得兹事体大,所以怎么也不敢自己拿主意,只是好好地照顾着那名官员醒了酒,并且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秦旺有些为难地看着我,见我脸上的神色严峻,又温言地宽慰我,“福晋,那名官员其实是颇为谨慎的,只是跟奴才已经混得极熟……不过奴才已经命人严密保护他了,福晋千万不要忧心……”
我听着秦旺宽慰的话,却已经完全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嘴里微微地泛出一丝苦意。这少年秦旺还真是一把好手,让他调查,他竟然就调查出这样的一桩惊天大案来。我的心砰砰地跳着,极为剧烈,一阵惊悚之下竟是猛一挥手,硬是将桌上的茶碗打翻在地。茶碗摔在地上发出极清极脆的响声,望月神色紧张地推门而入,见我和秦旺的脸色都有些怪异,一张俏脸也是瞬间变得有些苍白。
屋子里的气氛有些诡异,我们主仆三个人大眼瞪小眼,脸上却都带着几分奇怪的惊惧。望月愣了愣,忙跑过来蹲下身子收拾残破的碎瓷片,我狂跳不已的心开始渐渐平静下来吗,脑子里却又闪过她脸上方才煞那间的惨白,不由地笑问,“我摔了个茶碗,倒吓到你了?”
望月仍是低着头收拾地上的碎片,语气却也恢复了平静,有些委屈地道,“奴婢,奴婢是担心福晋……”
担心我?她担心我被秦旺挟持?我有些愕然地品味着望月的这句话,眼神却是不由地瞟向了立在一旁的秦旺的脸。果然秦旺的一张黑脸又泛起了红色,颜色与猪肝有些相近,再看他的神情,夹杂着尴尬和不可置信的愤怒。
“福晋,奴才先下去了。”秦旺简短地说了一句,也不管我有没有点头,便风一般地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卷三:曾经沧海难为水 卷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第一百零二章 江宁织造府的老花匠
卷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第一百零二章 江宁织造府的老花匠
杭州的寒冬几乎毫无预兆地降临了。南方的冬季与北方完全不同,是一种极为凛冽的寒冷,不论在刮着刺骨的风的户外,还是在阴郁潮湿的屋子里,寒冷似乎像个幽灵一样地如影随形,让那些感到身子冷和心冷的人们都觉得人生更加的凄惨难耐。
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里终于落下了第一场雪,大片的雪花像鹅毛一样密密麻麻飘飘荡荡地从天空中降落下来,落在屋顶上,落在树枝上,落在道路上,被来往着的行人们踩得有些泥泞,不复原来那样高高在上的纯洁模样。
这场雪足足下了有两日才有些不甘心地停了下来,只是雪后的杭州城里似乎更冷,原本就非常珍贵的阳光被冰雪毫不犹豫地吞噬,冷得街上连人都忽然少了许多。
毓庆班金碧辉煌的戏厅里,厚重如棉被一般的门帘和窗帘挡住了所有的严寒。无双正轻柔而婉约地唱着,灯火极为辉煌地照耀着华美的房间,三个极大的火炉子正旺盛地而红火地燃烧着,使得整个屋子里异常温暖。
我x在柔软的的榻上,一面同边上的涵玉悠然地聊着天,一面抿嘴磕着一盘粒大饱满的瓜子。
涵玉微微地笑着,带着一种。极为恭谨和高兴的语气开口,“福晋真是个雅人,这毓庆班竟然一包就是一个月。”她言罢又拿起身边几上的一张清单,细细看了一遍,“这些真迹孤本纵然珍贵,可是涵玉却从没想过竟然值这么大的价钱。”
我今日在毓庆班请客听戏,请的。是孙文成极为知书达理又极为精明强干的大女儿涵玉。不过我今日却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是开出了一张清单,希望杭州织造府帮我在民间寻找并高价收买一些名画和古书的孤本。我出的价格高得有些吓人,所以连锦衣玉食的涵玉也颇为感慨,以为我就是那种为了这些个字画极肯下功夫的行家。只是孙家人并不知道,我清单上的这些东西大多数就藏着胤禛的府上,也有一部分就在我自己手里,我出这样打的价钱,其实也不过是有价无市罢了。
所以我看着涵玉咂舌,却只是。淡笑不语。其实不管是豪爽地包下毓庆班,还是出大价钱买名画,我都只是在演戏而已。道理很简单,我在杭州织造的入股迟早会被孙文成和另外两家知道,孙济常是商人,或许对于我要钱的原因并不关心。但是孙济常不关心,却有人关心,三家织造一定会揣测我索取这笔不小金额钱财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像我这样一个养在深闺中的女人却如此热衷于赚钱,这是一件蹊跷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件事情落入八阿哥和十四他们的耳朵里,难保他们不会深思到官场的运作中来,我不能让自己苦心经营的事情落入他们的怀疑中去。
而在我请涵玉听戏的这个夜里,少年秦旺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杭州,小心翼翼地潜入了江宁地界。秦旺基本上已经被江南的人们定义成了一个专门替我跑腿买东西的小太监,大到字画花卉,小到一根针、一串冰糖葫芦,这位话不多的小太监一直极为耐心地执行着我的每一个要求。以至于老陈的女婿曾私下同情过这位皮肤黝黑的小太监,直叹为女人当差难。当然秦旺自然是不理会这些的,他只是憨厚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表示丝毫没有任何不满,让想要拍马屁的老陈女婿在心里不禁对他翻了个白眼。
秦旺这一次的出门像往常一样寻常,但是他的速。度却是极快,在距离江宁并不太远的县城里搜刮了些小东西,便消失在了进入江宁城的人海中。秦旺这次的目的是曹寅家中一个不怎么起眼的老花匠,这个花匠虽然不起眼,却是向秦旺泄密的那名泡澡官员的一个线人,其实也不仅仅是线人,确切地说他是被曹寅灭口的那名官员失散多年的远房表弟!
在那名冤死的官员同江南三家织造府一起密。谋着制造金玺的时候,曹寅家里的花匠忽然得了失心疯,但是这件事情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地重视,因为这位花匠本来就是个毫不起眼的角色,如今忽然得了失心疯,也只是变得喜欢出入江宁城里最低级的窑子,顺便有天没日地唱上几句戏。其实按照常理,这样疯疯癫癫的花匠本来并不应该继续留在堂堂江宁织造府里,但是曹寅是个善人,起码在外人眼里是个善人,他念着花匠三代都是曹家的家奴,于是也没有狠心地将他逐出院子,还让管家多放了他一丁点的月钱,让他能够逛得起那些低级窑子。
但是事实上这。位花匠并没有疯,相反他一直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老花匠失散多年的表哥在了江宁织造府,可是认出他时却只是极为隐晦地扫视了他一眼,而这样的眼神是在儿时游戏中培养出来的一种默契,这样的眼神代表了一种秘密,一种决不能宣诸于口的秘密!于是老花匠千方百计地寻了机会出门,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表哥,并从表哥的口中知晓了那件有些惊天的秘密。
于是这件本来应该是皇家秘密的事情就落入了一个寻常老花匠的耳中。原来鼎鼎大名的太子终于按捺不住他的急躁了,并且他也发现了父皇对自己的不满,而他自保的手段便是寻找机会从他那无比英明的皇阿玛手中夺过那片他垂涎了四十年之久的大好江山!篡位!这就是锻造金玺事件的原因,花匠的官员表哥慑于江南三家织造的强势而不得不参与到锻造过程中来。但是这名官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而他试图劝说曹寅等人罢手的行为也遭到了失败,所以他事先将这件惊天大案告诉了刚刚重逢的远房表弟和那位极其信任的老乡,并极为准确地语言了自己即将死于非命的命运。
老花匠在震惊与伤心之余,只好装疯卖傻地在江宁织造府里生活起来,不过一切似乎都没有偏离他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