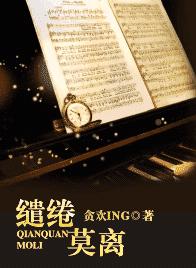春怀缱绻-第1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药侍把话传回来的时候,阿容正等着药用,一听码头把药扣下了,连问缘由的功夫都没有,骑着马就往码头去了:“再怎么样也不能耽误用药,你趁这会儿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那揭起事来的药侍这时有点着急了,再怎么也不能让这位去呀:“容药令,这事儿不必您去,随便派哪个药师去就行了,就钟三这身份,哪用得着您亲自去。”
“要是平时我管他,可是病患等着药用,我等得病患也等不得。”阿容这人就这样,一遇上药啊病患的脾气就硬起来了,管你是谁压。
而且她最近被大公主灌输了不少“咱是容大姑.京里只管横走的主儿”之类的念头,脾气一上来,这身份带来的底气就显出来了。
到了码头,阿容就指派了人把要补的几样药材先拉回去,守着码头的人不干,阿容站旁边只说了一句:“病患等着用,人死了伤了残了你们负责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们负得起责吗?”
守着码头的人本就是小民,经阿容这么一吓谁还敢上前来,就任由药馆的人把几样药先拉走了,好在也不是拉全部,人也就当是睁只眼闭只眼了。
最后一样儿药上了车,钟三却风闻而来,只见当头一姑娘穿着白甲子站在那儿,迎风而立瞪着眼那叫一个威风劲儿。
钟三惯是个耍耍威风的,眼见有人在自己地盘上这么耍,当然过不得眼去:“站住,谁让你们拉的,谁许你们拉的?”
“如果我没记错,这码头是姓容的,没错……水上归钟家管,可货一旦落了地那就归我容家管。我在自己的地头上,要拉自己的东西,难道还得跟你先知会了,断没这道理。”这会儿阿容得感谢天天在她耳朵边上,来回提容家事的那几位容家长辈。
这钟三一下就被压了气焰,略带迟疑地问道:“你是容雨声?”见钟三这态度,阿容身后的药侍说道:“容药令的名字也是等闲人叫得的。”
姑娘家的闺名外人是叫不得的,这钟三虽然混,可长年在京城,大家里的规矩懂,这时连忙改了口说:“容大姑,不知道您要来,要不然改列队相迎才是。”
既然人的态度软了下来,阿容也就跟着温和了一些,这也是跟周毅山学的。他惯常做的就是人横他更横,人和气他更和气,在有底气的时候这是管用的:“这倒是不必了,只是这些药材药馆还等着用,还望钟三爷放行了才是。”
“这”…”钟三这时候才想起来,这位和谢长青五月的大婚,以后就是一家人。
这下放与不放就为难了,不放吧形势比人强,放吧,这口气摆了出来.这样草草收尾的可不像话。
好在阿容已经问请了缘由,这时想了想决定给人递个台阶下,“我和淑妃娘娘也算是旧交,还请看在淑妃娘娘的面儿上,放药材出码头。回头进了宫,一定代您向淑妃娘娘问候一声。”
一听提起了钟碧微,钟三就知道这是人在给台阶,而且给得特明白,要不然阿容不会说得这样干巴:“哟,早说呀,既然容大姑和娘娘有旧,那……还看着于什么,赶紧帮着搬药材。”
但是当搬到还剩下大约半成的时候,码头就不肯放药材了,据说这是水运的抽成,这是惯例。
对于这惯例阿容问了身边的药侍:“怎么还有这规矩。”
“容药令不知道吗,这半成容家和钟家各抽一半。”药侍的意思多明显,这里头有一半是容家的,咱自家人就不计较这么多了。
而阿容这时候想的是,容家和钟家这些年抽的药到哪里去了,这么多药……要知道药也是军备之一,他们总不会用于民间:“他们抽了药做什么,用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卖给异邦夷国吧,反正哪儿价早卖到哪去。其实这些也都是心知肚明的事,只是大家都不说破,朝廷对这些事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药侍回得极其理所当然。
然而这么一说,阿容却有些惊讶了,如果药材、米粮、油布等都扣半成。那么五年以来,钟家和容家职下的那些都以哪里去了,反正她在容家是没听人提起过。
“行了,把药拉回去再说,以后钟家应该不会再再为难了。
”钟家倒是不为难了,阿容现在又乱了。
她现在想的竟然是周毅山知不知道这些事,国家动乱百姓受苦,她可不想当这消防队员。虽然她是这职责,可万一因战争而起的人祸,那死伤就不是她救得过来的。
想完这事儿,阿容又禁不住抽自己一巴掌,既然人都说是心知肚明的她还瞎操什么心。
这时刚过了正月,正是二月春寒的时候,街上冒了些小嫩芽儿,阿容看了一路顿觉得舒服,也就没再催着马再快行。
正在她想着事儿的时候,半路上遇着了谢长青,谢长青见她安好着松了一口气说:“你怎么自已就去了,码头上的事你让药馆的管事去就行了,这些事向来是他们处理。”
“管事出去了,药馆里又急着用药,我不去谁去。再说我不是好好的,就像大公主说的,在京里没谁会欺负我。”阿容下了马,把缰绳递给了随行的药侍,然后和谢长青一块并肩走着。
春光里两人缓缓而行,一人着白,一人着青,两人的身上都心是披着柔光一般。
“母亲是要告诉你,你身份金贵……”谢长青说着叹了口气。
“长青,码上的药材要抽半成,这事儿你知道吗?”说来说去,阿容还是放不下这件事,要是别的可能就这么过去了,可是在药材来说阿容放不下。
只见谢长青点头说:“知道,因为钟家每年要交银钱给朝廷,进行抽成也是自然的,船运费是定好了价儿不能改的,要是不抽成钟家就只能往里头倒贴银钱了。”
看来这事儿还真是谁都知道,而且谁都觉得理所当然,阿容想了想说:“那那些东西卖到哪里去了,总没见他们在卫朝卖过。”
“卫朝价低,这些东西转手卖到关外去才能身价儿倍增……声声,你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事了?”谢长青疑惑地问产延。
“五年了,这是不少东西吧,长青,你就没想到别的地方去?”阿容有点儿怀疑是不是自己从前军事八卦看多了,所以产生了不好的联想。于是谢长青一琢磨,摇头说:“不至于,你想多了。要是不放心.你回头去容家查查造册就行。”
别说,阿容还真去查了,只是回去一查造册的底,这才知道容家从来没收过东西,收到的只是折价儿的银钱,比市面上高一些,但远不是谢长青说的翻着倍地往上涨。
她起先还怀疑是容景福动了手脚之类,但查了进出往来,再问明了各自发现没动半分手脚。
等查完了再回药馆去时,阿容先就去找了谢长青,开门第一句就是:“容家没有收到东西,是直接折了价儿。”
“声声,你先等等,我派人去把运转司的造册拿来,看看这五年水上往来的各项出入。”
这些东西,要真是卖给了关外诸夷国,还真不算什么,但是要是某王囤起来,意图做点儿什么,那就是件大事儿了。
更兼着要是卖给了独一位夷国的国主,那事儿也小不了……阿容是这么想的,说到夷国国主阿容就想起那啥国的大王子来了,那位应该当国主了吧,原谅她一直不记得是啥国!
(对手指,我写过阿容从前的全名么,我竟然记不起来了,查来查去查不到,我写了没,还是没写……比我聪明能干滴娃们,某弈求解……我个渣,自我拍飞了!)公子的责任与阿容的誓约立春水运招标,谢长青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将水运继续标给了钟家,这其中有多少缘由,那就真是不足不外人所道了。
对于这个阿容当然有些疑惑,当然她更得承认自己有那么些儿酸,不由得要把事儿往钟碧微身上去联想。
水运招标的次日,阿容在药馆后头的山上掐白叶兰芽,卫朝有“春吃芽.夏吃茬”的说法,白叶兰芽就是春芽的其中一种,有升元养气的功效。
她不会做,但不妨碍她喜欢吃“够了吧,满满一筐子了,回头肯定能煎不少白叶兰芽饼。”
随行的药女鼓了半天儿劲才问道:“容药令,您何必自个儿来掐兰芽子,要是想吃吩咐一声也就是了。”
看了眼这药女,阿容默默地不说话了,她能说自个儿是心里烦闷,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来祸害这些小嫩芽的么:“吃的乐趣不如采的乐趣足.你就当我闲得发慌也成。”
那药女或还想说什么,但这时正看见谢长青举步从小山坡上过来:“容药令,爷来了。”
“嗯,你把兰芽子拿到灶房里去,今儿中午咱尝个新鲜。”阿容说完也不站起来,继续蹲在那儿跟两株小药苗奋斗着。
那是一株野露草和一株晓星兰,这两样药草都是还不明性状味的,阿容忍不住戳了戳自个儿,又想起了这事儿来。或许是近来遇的事多了,她竟老也把这明性状味的事儿给扔了脑袋后头。
一路缓行而来的谢长青看着阿容,见她在那儿拨弄着野露草和晓星兰,那不依不挠的劲儿真让人替这两株小苗不忍:“手燥热,你再拨弄下去,它们就长不好了。”
“谢长青,你为什么要把水运标给钟家。”阿容问完就想抽自己.真是个小心眼没治的。
只见谢长青闻言一笑,遂说道:“我昨儿就等你问,不见你来,这会儿想着来跟你说说,没想到你倒是问出来了。声声,你这性子真是不好,憋在心里头只是伤了自个儿而已。”
于是阿容恼了,瘪着嘴恼羞成怒地说道:“为什么要等我问,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见她生恼,谢长青嘴角的笑就益发地明显了:“要是我说就想看你这嗔怒的模样,你该更恼了吧。”
果不其然,阿容确实更恼火了,瞪着他说:“是皇上的意思是吧,他这是要把鲁王往深了坑。”
“怎么联想到鲁王的?”谢长青却不意外,既然能发现事儿,他就相信阿容能看明白事。不过看来这姑娘是开始学会用容家的力量了,这样倒也好,渐渐地掌起容家,对以后也多有益处。
“因为他不能容忍有人和他一样名正言顺,虽然他更正一些,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皇上就是这样的人。”对皇帝她当然不了解,可论起周毅山来,她却了解得够了。
对于阿容说的话,谢长青思索了会儿,而后就决定结束这个话题:“声声,东西大比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这段时间我们一块回连云山,把你知道的那些药的性状味一一写明白怎么样。”
“不是说明性状味要实证实方吗,我可没有这些。”阿容见谢长青提到了自己刚想到的事儿,又不由得觉得自己跟他还真是有默契,想事儿都想到一块去了。
她说完这话后,只见谢长青也蹲了下来,然后揉了揉阿容头顶有些乱的头发说:“那就托上古药书的名,这事儿你可不是第一回干了吧。就算托了名,以后也是要实证实方才能行的,只是可以一边呈报审核,一边在把实证实方的任务发下去,让山里药令及以下都来进行,这不就是今明两年的事么。”
听完谢长青的话后,阿容想到了一个词儿——人多力量大:“这些惯例你比我熟,你要是觉得可以那咱们就办……”
说到这儿阿容忽然又奇怪,最近谢长青把各项事务都交待得明白,而且很多事都在办,他到底想干什么?
见她疑惑地望过来,谢长青问道:“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你最近怎么闹得跟交待后事似的,件件事儿都紧着在办,虽然这话不吉利,可你现在就给人这感觉。”阿容扶着谢长青的手站了起来,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感觉看着谢长青。
而谢长青也就这么蹲着抬头看着她,丝毫不见仰视之感,却只显得纵容而已:“开春就讲这些事儿,也就你嘴里才说得出来。”
迎着山风,谢长青站了起来,俯看着山放下的连云山药馆,他眼里显出几分眷恋来:“声声,我从小就长在这里,天天睁开眼看到的就是药材、药师、病患。后来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成为我肩上的责任。”
“但是不论先帝还是皇上,他们对八大家早有削权归公的意思,所以你着布置,希望交出去的是一个完整的,可以自行运作的连云山。”阿容通过容家,早已经对这些了解明白,就算谢长青不希望她知道这些,但是她最终还是知道了。
身在其位,就算不谋其事也要知其事,这是容家长辈们的意思。“自行运作,这四个宇倒是贴切。你从前说我有圣人癖,我最大的圣人癖就是希望连云山得以泽被苍生,而不必沦为人祸的牺牲品。”就这个或许并不能称为愿望,阿容坚定地认为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
谢长青从小就被灌输这些,长大了之后有这样的念头其实很正常。想了想阿容不由得笑出声来说:“或许你不必交待这些,我们会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