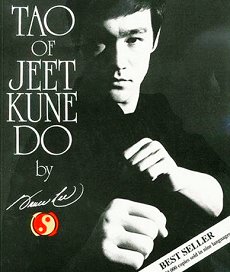大学之道-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天晚上我们宿舍实现了大学生活第一次的通宵达旦,挑灯夜读。挑灯夜读的不仅有田鸡,胖宝,还有我和冯林。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这是第二次学着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勤勉夜读,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的惨痛经历发生在小学三年级,因为我抄了同桌的作文,本来抄作文是常有的事,只不过那天的作文题目取得不好,叫《我的爸爸》。下午放学的时候,老师提着我到他学校的宿舍里问我到底有几个爸爸,我回答得很干脆,只有一个,他叫马壮壮。然后老师又问我,胡葛田是谁。我告诉他是同桌胡静的爸爸。就这样,他最后把我给了扣下来,要我重新写篇作文,直熬到晚上九点才放我回家。
熬夜对于我和冯林来说是常有的事,但就熬夜这种异常行为的内容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兴趣使然,比如牌九麻将斗地主;而另一种则是自杀性的素质提升,比如现在的背书。
每当夜读的时候,我和冯林都会不约而同的将后脑勺对着烛火,两眼张望着窗外朦胧的夜景。我说,瞧外面那景色,多美呀。冯林说,谁说不是呀,星光闪烁,晚风徐徐,又是一个迷人的思春之夜。
其实那几天连绵阴雨,晚上天空乌漆抹黑的紧,别说什么星夜璀璨,就连窗户口灌进来的风都阴森森的,吹得灯火摇曳,人影倒映在墙上成了几道鬼影。
我知道冯林思春谁,还不是彭雪。这段时间他们打得火热,就差搬出去住进“堕落街”。对于冯林的爱情归宿,我心中说不出的滋味,就像被别人分享走了你一半的记忆,孤寥寥的时候总觉得有几分落寞。
我和冯林就这样坐了半宿,书刚翻开了封皮,眼皮子就困得直往下坠。最后我们决定放弃这种幼稚偏执不切实际的抵抗,屁股一抬,噌噌的爬上梯子上床睡觉。
上帝是不公的,特别是在分配时间用于睡觉和学习上时显得更为失衡。他使出便秘的劲儿将睡眠的时间压了又压,就那么眼一睁一闭就是一宿;而上课时无论你打了多少个盹,眼睛开开合合了多少回,只要你还能醒来,你就会发现,台上的老头仍在不厌其烦的讲解矩阵排列。因此,我觉得上帝就是一最为原始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比如大肠杆菌,神经系统简单到不需要睡眠。
所以,我也一直认为,上帝就在身后,寄居在肛门里。
一早醒来,我就在拉肚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在里面作祟,就因为我昨晚骂了他。我也来不及深究,只能随便吃了些药,背上书包去学校的复临舍考试。
考试的座次是按学号编排的,而学号又是按姓氏的首字母编排的。李茹坐在我身旁,而冯林坐在离我较远的侧后位,但这也完全阻止不了我跟冯林的协同作业。
试卷一发下来,我就趴在桌上小睡了一会。根据历年来的作弊经验,从一开始发卷抄到收卷的绝对是雏儿,而真正的强手是等到麦子成熟了才去收割。有时我觉得自己经验足够丰富到可以出书立著了,只不过这种书还没有出版商敢应接,就只好口口相传。
等我睡足起来的时候,台上的监考老头已经趴下了。我估摸着昨晚他也跟我们一样,后脑勺对着烛光欣赏了一夜窗外的月朗星疏。对这样的老园丁一头伏在讲台忘我的“工作”,我们往往是感恩戴德的,恨不得给他跪下叫声亲爹。
当周围的试卷答得七七八八的时候,也是我和冯林眼神开始活络的时候。我们都有着超敏锐的视力和超强的记忆力,一双眼珠子宛如高分辨率的扫描仪,所过之处,无一字幸免。只不过扫到李茹座位时,我的脖子就像卡了跟钢条,眼睛再也挪不开半丝半毫。她正不时的掀开短裙的下摆,将大腿上的字抄回试卷,而那白皙细滑的大腿就像一盆上好香滑的猪肘子肉,看的我涎水直流,忍不住对着她的*猛咽了几口口水。那是怎样的一双修长的大腿呵,光滑的如一汪西湖的春水,微风拂过竟掠不起一丝波澜;细嫩的如一根纤滑的蛛丝,细雨沾染便化作道道青烟;皎洁的如昆仑山顶的圣雪,尘埃掠过也不忍玷污她的圣洁。
我觉得我对她有一种最为简单而原始的冲动。
“看看。”我悄声的对着她说着话。她瞥了我眼,又扫了眼讲台打盹的老师,最终还是决定把胳膊垂落,将试卷斜斜的朝我的方向移了过去。
“不对,我是说下面。”我又指了指她的大腿。其实我当时是想说抄你大腿上的答案。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只怪当时没见过女人的大腿,一冲动,满脑子充满辩证思维的逻辑性语言经过*一过滤就变了味儿。
她瞪了我好久,我以为她在踌躇思虑。女人都是小气的,我能理解,所以我也一直耐心的盯着她的眼睛等待她的回复。
那一会儿,我觉得她的眼睛漂亮极了,明亮而深邃。
最后她没有给我秀大腿,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难,朝我猛抽了一耳光。当时我立马被抽得蹦了起来。
按理说,大大小小的耳刮子我从小吃到大,不论花掌,断掌,还是蒲扇掌,钉锤掌,不管他抽的如何的势疾如风,凌厉如雨,我打出娘胎就从没痛得吱过声。而这小妞好像专门研究过防狼术,一巴掌掴过去,抽在我耳廓子上,抽的我好一阵耳鸣,伴着星光璀璨,泪水横流。
我当时痛的就想骂丫的怎么就这么狠毒。可我还没开口,又被连着甩了一耳光抽在另一边脸上,一左一右,十分的对称协调。
我终于忍不住满腔怒火,一口气骂了出来:妈拉个巴子,抽上了瘾了啊还抽。
等我擦干呛下来的泪,扭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监考的老头已经冲到我的面前,一只手还提的老高,气的瑟瑟发抖,原来最后一巴掌是他抽的。
“你这学生,不害臊。操(抄)人家女同学,还敢骂人。”这老头满口的湖南腔调,而且更为要命的是他把“抄”字发音成“操”字,自己半点也不觉得别扭,满口子乎者也的教训我。
老师一通数落下来,我倒没半点觉醒,却把李茹气得哭了。
而这老头早年也是个怜香惜玉的主,一见女生气的哭了,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收了我的卷把我踹了出去。
而这里面最冤的莫过于我,明明是他自己犯了贱嘴的毛病,却把我轰了出去,还抽了我一巴掌。
最后这里面顺带着倒霉的还有冯林。因为从高中时开始,我们之间为了公平抄袭,就实行实名对换制,也就是我的试卷写他的名字,他的试卷写我的名字,互相给对方抄答案,这样就能做到公平竞争,毫无私利。冯林见我试卷被没收了,知道我是没戏了,于是又把名字改回自己的名字交了上去。这样,批卷的时候就发现两张同名的试卷,更让人透心凉的是,答案竟然出奇的一致。
那一场考试过后,我们俩又成了垫底双绝。最终还被拉去补考了一次。
十二
大学除了学习只有两件事是最值得干的,一个是泡妞,另一个是进社团,而进社团是为了更好的泡妞。所以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是可以干的,那就是泡妞。
而对于泡妞这件事,我和冯林有着的极大的分歧。他崇尚的是拉手谈情,挽手谈性,分手谈钱,讲究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上炕头。而我所追求的是那种欲拒还迎的闷骚型女人,就像那些难以追到手,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激情似火的三贞九烈的女子,她们往往都有着明确的人生观,传统的情爱观,奔放的*观。她们的整个人生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人前贤妻,床上*。这样的女人追求起来虽然非常棘手,但总会给男人们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恨不得将她们像剥笋子似的扒个精光研究得通透清明。这样的爱情结局也许会很平淡,但过程绝对是荡气回肠。
所以,一开学冯林就过得活色生香,而我却只能痛苦的在梦境里寻找慰藉。
我突然想起学长语重心长教导我们的那几句话: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更何况我们这些牛B般帅气的陈世美,面对院里屈指可数的几个柴火妞,谁又忍的心下手?最后我不仅耳根子软了,连手也软了,被学长洗完脑后就牛逼哄哄的奔向社团这条不归路。还信誓旦旦的妄言要为生产社会主义新一代接班人而奋斗一生战斗不止。后来才发现这他妈的都纯属扯淡,那些学长们个个毕了业还光棍打得倍儿响。
在整个大学生涯里我一共加入了两个社团,第一个是自行车社团,而且还是被半欺骗性质的诱拐进去。那天在食堂门口我被一个穿着运动短裤特阳光型特唆蜜的嫩*生给缠住了,她往我怀里塞了一团纸,我起初还以为是情书,后来仔细一看是张自行车社团招人广告。那个发传单的女生看着我笑得无比灿烂,就像一道阳光一下子就射进我的心窝子里,暖暖的,亮堂堂。我这人向来对女人的微笑没半分免疫力,更何况还是看似那么单纯无暇的清澈少女。我想,她一定是处女。
我问她社团里的女孩子是不是个个都像你这般清纯漂亮,她听了咯咯的笑着回答说“是的”。最后我就稀里糊涂的进了社团。
但在第二天早上的一次社团*,我顿时感觉被那小妮子卖进了鸭店,黑压压的人头放眼过去都清一色带把的。甚至好几个雏鸭儿见我年纪稍长,都跑过来问我,我们社团那天发传单的那个女生在哪,弄得我哭笑不得。往后社团也没有举办过任何自行车运动,还把每人500元准备买山地车的集资挪用出去撮了三天大锅饭,就彻彻底底的解散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发传单的小妞是社长的女朋友,而吃饭的饭店老板是社长的舅舅。
打那个饭团被解散以后,我见了社团宣传就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骨。但是很快,我这愤世嫉俗的焰火魔术般的被一个女人的柔情所浇灭,于是又一头栽进社团的怪圈。
那是在一个晚霞卷天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到公寓门口,蓦地发觉一道从未见过的靓丽的风景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位异常娇艳的女生立在一张小方桌后面低首危坐,一双白皙的细手在纸上刷刷的抄录着。这是怎样一个华丽的女子啊,一副玲珑剔透的身材在黑色紧身衣的包裹下尽显突兀,那坚挺的乳房,高翘的臀部与她来说,简直就是绝世版的薯条,可乐配麻辣猪堡宝。那玻璃珠子般清澈的双眼如此恰如其分的镶嵌在那一张无可挑剔的俏脸上,让你不由得赞叹其父母造人工艺的精湛。
那一刻,我的整个神经中枢系统为她彻底崩溃,*的倒瘫在地。恍惚间,我只觉得前半生都TMD白活了,只怨恨自己的老爹没在二十一年前和丈母娘替我们定下娃娃亲。当时整个给我的感觉就像隔世的梁山伯邂逅了祝英台,续演一部来生缘,立马激动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抹着步子向桌前拖过去。
“同学,你要报名吗?”她笑起来简直就是迷死人不偿命,那双媚眼曲成一道弯弯的月儿登时钩住了我的三魂六魄,外加七窍生烟。
“报,当然报。”我看到她朝我笑,简直就像是见到了死去的亲娘,就差往她的*怀里蹦跶。
但紧要关头我还是踩住了刹车,我问她,你是社长的女朋友吗。她听了朝我抿嘴浅笑,我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似要沸腾起来,无论她的哪个侧面,哪样的举止都是那样的让人欲仙欲死。
她说,我就是话剧团的社长。我一听长长的舒了口气,心想,骗子都还得有国家公休日呢,况且这女娃娃怎么看都长着一副准媳妇的俊俏模样,怎么可能是骗子。于是又问她要不要交钱。她摇摇头回答说,社里不用交钱,我是学戏曲出生的,可以免费教大家。
我听了差点鼻血当场喷出,我真不敢想像日后她在我面前扭动腰肢的媚态。
“不过,我们得优先招收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为我们经常参加学校以及电视台的有偿表演,可以赚些补贴。”
“我,我,我家里就很困难……”说着说着我就声泪俱下,将祖宗十八代的烂事,平生二十一载的糗事,以及旧社会的压迫,黑社会的胁迫,全球金融危机的逼迫,抖了个尽数。我恨不得当时就带个拖油瓶,穿着个大破棉袄,打扮的特杨白劳再出来见她。
有时,我觉得自己TMD太有表演天赋了,竟说的那妞哭肿了眼。后来我顺利签进了话剧团,问她要了姓名,联系电话,班级,籍贯户口,除了三围该有的都有了。她名字叫方雅琪,97级英语系学生,江苏常州市人,三围88…60…87。其实三围是现场目测的,我向来对数据不感兴趣,通常喜欢直接用手箍。
![[清]康雍之道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8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