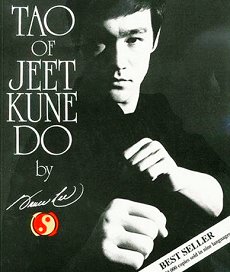大学之道-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一听这猪脸男满嘴喷粪就恼了,站起身一巴掌抽得他转了几个圈,骂道:“滚你ma的蛋,爷在这,啥时候轮到你撒野。”我这人一向性子暴烈,特别是听到别人调戏自己喜欢的女人,我就会立马对谁龇牙。况且,在冯林面前我不想让他认为自己是个软蛋,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猪脸男圈还没兜完,我又猛地听到李茹在身后尖叫,我急转过身想看看出什么状况,却不想被人一板凳拍在后脑勺上,一阵闷响倒在地上。冯林见我被拍晕了过去,急跳起来一脚踹飞旁边的黄毛,提起酒瓶朝那个拿板凳的小子脑门上一通猛砸,爆开了花,稀里哗啦冒着血,痛的他滚在地上一阵哀嚎。猪脸男捂着被抽红的脸算清醒了过来,也端着一个酒瓶子要来砸冯林,不过那肥猪满身赘肉,挥酒瓶时幅度大动作慢,还没等他手在头顶完全举直了,冯林已握起半截破酒瓶朝他肚脐眼扎去,呼啦一声,软绵绵的像插在豆腐堆里,抽出来时,血顺着衣角流了一地,也不知道那些花花肠子有没有给抽出来。
冯林一见给人开了膛,心里一个哆嗦手也软了下来,破瓶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冯林虽然自小打架打到大,见血的场景仅限于被人揍歪了鼻梁,鼻血鼻涕污了满脸满脖颈,再顶多使些黑招,猴子偷桃,通人会阴,哪见过这种大手术,当即吓得倒退了几步。而几个小喽啰看老大被人放倒了,都哇呀呀的提起板凳准备一哄而上,吓得冯林撒腿就跑,他们也跟着追了出去。
三十二
大学四年里,我唯一值得引以为豪的是,除了妇产医院,几乎住遍了长沙所有的医院。有时我想,我若不是投错了胎,进错了行,否则,干起医生这行当绝对比当工程师更有奔头。按人们“久病成医”的逻辑推理,我应该比医神华佗更要医神。李茹却说我是天生烂命,不及草芥,要放在几十年前顶实的一个炮灰,就算运气好,落个伤痛,最终还是得不治而亡。我就骂她是个扫把星毒舌妇,才离婚没几天,就咒前夫死。
那天晚上冯林夺门而逃他们没追上,等他们回来时,安德楠已经叫李茹偷偷把我送去医院。他自己则陪着那几个小喽啰把猪脸男送到另外一家医院,还垫付了所有药资。后来,我们再次在师大的一条林荫道遇到他时,他怀里正揣着两本书埋头赶路,又像回到了三年前,满身书呆子气。他说他已经关掉店子,和任青筱两人正全身心的准备考研。他说上次猪脸男那件事他也有责任,任青筱原是黄毛的女朋友,后来见他整天不务正业混社会把他给蹬了,黄毛就怂恿猪脸男带着一伙人来他们的酒吧闹事,目的就是为了诈取所谓的“分手费”,却不想那天晚上被黄毛认出了我,才捣出这么场乱子来。事后双方都没敢报警,安德楠怕遭他们报复,他们则怕敲诈勒索的事曝光。
当我们问起猪脸男的伤势重不重,安德楠却是咧嘴笑,说:“你们是没见呐,那天晚上,那家伙一路上从酒吧到医院,杀猪似的捂着肚子哀嚎,可一进了医院检查,医生跟他说根本没伤到筋骨,他就立马止住了惨叫。他爸是交通局的副局长,两父子养尊处优惯了,吃得跟胀鼓鼓的猪大肠似的,肚板油厚实的很,只是伤到了些皮肉。”冯林听完后拳掌一合,嘴里骂道:“ma的,看来上次还是手软了。”
我想,他们也只是出来求财,这事过了也算过了,犯不着跟我们扣眼珠子掐脖子,又不是抢山头,再说了,我们和安德楠不同,不是软柿子,搞不好还能沾他们一身骚。所以渐渐的也把那件事给淡忘了,依旧昏天黑地的过日子。
我和冯林打小臭味相投,性格相仿,只不过我心思缜密,他有些傻头傻脑,有时我们连喜好的东西也出奇的一致,也因此经常为玩具糖果大打出手。上小学那会,我们都喜欢胡静,经常为胡静的哪只小手白些争吵。后来老师把冯林和胡静的座位编在一起,我就特不服气,隔天就去班主任那打小报告,说他们俩上课经常说悄悄话,递纸条,我还把从冯林抽屉里偷出来的小纸条给班主任看。其实那会我写给胡静的纸条比谁都多。那时候我觉得大人都特好骗,老师就信了我,给他们棒打鸳鸯两头散,将我和冯林调了位,我也趁虚而入尝到了甜头。
胡静的母亲跟父亲很早就离异,后来改嫁给一个庄稼汉,没两年庄稼汉又死了,她母亲便寡居在家守着巴掌大的屋子,家境并不好。有一次她们家来了些娘家的穷亲戚,她母亲嫌地小,住不下这么多人,就把胡静送到冯林家借宿,还和冯林同床睡一张床。我第二天知道了特别气愤,那时候七八岁大,对男女能在床上干出些什么花样狗屁不懂,只知道只要同谁睡在了一块就是谁的媳妇。我一气之下把冯林的作业本一把火给烧了个灰烬,还拉着胡静的手说,“下次你家来人了,就住我家。”胡静摇晃着脑袋,两根马尾辫在脑后面晃荡,问我:“为什么?”我就跟她说:“我们是同桌,要住就得住同桌家。”胡静眨巴着眼睛点头说好。可惜后来她家穷亲戚还没来,她母亲就得了重病死了,她也被一个陌生男人接走了。最终我那同床的奢望一直没得到满足过。
胡静一走,我和冯林又如胶似糖的黏糊在一块,整天的街头打架,街尾骂娘,到了初中还欺负外地的学生,摸女老师的屁股。那时候我们的学习成绩还不至于一塌糊涂,我脑子灵光,初中的东西看一遍就能掌握得*不离十,只不过后来欠的债越来越多,渐渐的对代数,化学莫名其妙起来。初中时我们偶尔还上些课,老师说的话还算能听得进去。有一次物理课讲到杠杆原理,老师说了一句阿基米德的名言来开导我们,那句名言是这么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冯林坐在座位上对我说,这个姓阿的真牛比,他比大力水手波波艾还猛。我说,“猛个屁,给我一个女人,我就能将娃娃铺满整个地球。”冯林听了拍着桌子乐的哈哈大笑,他压根忘了这是在上课,女老师站在讲台上都能看到他喉咙里的扁桃体不停的上下翻动。老师一把把他给揪了出来,问他为什么上课大笑。他立马把我供了出来,还把我的话复述了一遍。老师一听完,哇的一声哭了,扭着屁股跑到教务处去告状。
后来我和枫林被赶到厕所门口罚站。下午毒辣辣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眼睛半眯着睁不开,嗡嗡的苍蝇夹着厕所的臭味一直在我们头顶打转转。我们站的腿软,便就聊起物理老师。我对冯林说:“我喜欢物理老师,你别跟我抢。”冯林说:“我不跟你抢,胡静我也不跟你抢。”我扭过头,顶着刺眼的阳光抬起眼皮子望着他,说:“真的?”他说:“真的!”我一脚踹在他腿肚子夸他是好兄弟。冯林站的累了,没防着我会踢他,跟一根面条似的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他赶紧爬了起来骂了我一句,又说:“以前胡静没走的时候,是不是你把我家的玻璃用弹弓打碎的?”我嘿嘿的笑着说:“是的,谁叫你和她睡一块。”他掐着我脖子骂我没义气,我就说:“你不是也把我的物理老师气给哭了吗,咱抵了。”他说:“我没气她。我只是讲你讲过的笑话,谁知道她这么不禁逗。”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些成年人才该想的问题,女人为什么这么小家子气,不禁逗,明明很好玩的玩笑话,进了她们耳朵里就像会要她们贞操似的,哇哇的会哭。
冯林说不会跟我抢女人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但是他现在好像完全忘了有这档子事,跟李茹越走越近。这事我不能怪他,要换做我,也会是光说不练。我要怪就只能怪他为什么还不移情别恋,还装的那么忠贞,简直就一武大郎。所以,总的来说,这事还得怨他!
过不了多久就是学校八十周年庆典,全校全院的师生都在为校庆文艺汇演作准备。土木院是墙旮旯里的屎壳郎,除了滚粪球就是吃粉球,木讷木讷土鳖土鳖的,上得了炮台上不了舞台,堵得了枪眼却不敢表演,近百年来演艺人才极其凋零,只要涉及到庆典活动都直接将整个院PASS掉。最后还是李茹借着话剧团的名义抢了个名额。
经过一晚上的合计,我们就定好了话剧的剧本,是一出三国人物回到现代社会的穿越话剧,当时就流行这个,漫天铺地的穿越小说,就像臭婆娘的裹脚,虽然没什么营养,但臭中带香,有男人喜欢,虽然恶中带俗,但观众本身比话剧更恶更俗。
剧本的整个人物都是李茹敲定的,她扮演小乔,冯林扮演周瑜,而我却扮演个莫名其妙的路人甲,悍匪乙,整个过程就是跑龙套,露两次脸,前一次只露左半边脸,扮演路霸躲在草丛伏击,后一次只露右半边脸,另一半被“周瑜”踩在脚下,总出场时间不超过10秒。
三十三
李茹是在刻意疏远我,这一点我看的出来。整个话剧她给我的戏份超少,根本没有同她她瞪眼对嘴的机会,就连田鸡这种质量不靠谱,嘴里含鸡蛋的角色都有三分钟的舞台戏。自从那次晚上她带走结婚证后整个人就变了,对我不冷不淡,整天和冯林泡在一块。我不知道我该庆幸自己发现得早同她离婚,还是后悔和她解除那层关系把她拱手让人。每次排戏时我内心总是痛苦的纠结,整个人拧成一团乱麻,瘫坐在角落里怔怔的望着。冯林拉着李茹的手演练的很卖力,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身影映在我眼眸里,就像一道火红的烙铁,嗤啦的烫出怒火来。
田鸡是所有人里面智商最低的,撇去我,他戏份也是最少的,但排演所花的时间却是最多的,因此他也是里面所有人中最勤奋的。李茹这时候总会爱心泛滥,帮他矫正形体和发声,就像当初方雅琪帮我一样。几天下来在李茹的帮助下他进步不少,但是结巴的毛病却是劣性积久,不是李茹所能改变的。这天他和枫林对戏时结巴的毛病又犯了,拉着冯林的衣袖支吾了半天,说:“公……公瑾……言……言……”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胳膊将他甩了下来,他身子轻飘飘的,就像一只在南极冰层贴着肚皮滑行的企鹅,沿着地面飞了出去。我说:“什么宫颈炎,白带异常的,这不是给咱丢人吗?我那个角色没台词,咱俩换了。”于是我就拉着冯林衣袖要求对戏。我知道田鸡当时想说“公瑾言之有理”,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抢他的角色,因为最后落幕时,他会拉着李茹的手高山远眺,而这也是我觊觎他的原因。
李茹见我如此蛮横霸道,朝我眼一瞪鼻子一哼,生气的走了。冯林夹在中间又无可奈何。我明白,在众人眼里我是一颗老鼠屎,但无论如何我还得舔着脸演下去。
随着排练的进行,李茹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大,在她眼里我还不如田鸡,而我却对她和冯林的亲密劲也越来越嫉妒。排演休息的时候,冯林帮李茹擦汗,我气的往墙角一坐生闷气。冯林擦完汗后又拿瓶矿泉水递给我,在我身边坐下来。我没好气的说:“坐这干嘛。”他先是一愣,然后挤着脸笑,说:“难不成坐你腿上?”我又对他说:“你知道鲜花插牛粪上,鲜花是什么感觉吗?”他愣头愣脑,不知道我说什么,半开玩笑的回答:“*的感觉呗。”他的话本是无心,但听在我耳里却是那么的恶毒,我登时脑子*,两眼猩红,抬起右拳对准他的鼻子就是一记重击,他的鼻子立时鲜血直涌。骇李茹得容颜失色,对我嘶声骂道:“马冬,你个神经病。”随即赶紧拉起冯林去洗手间处理。
我从没想过自己竟会对冯林下黑手,而李茹也会这般怒不可遏的臭骂我。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所有的朋友,众叛亲离。我就是一个变态的人,一条疯狗,心理扭曲,性情暴躁,对着镜子我经常认不出自己来。我扭过头去吼了句:“老子就是个神经病。”然后拾起衣服吧嗒吧嗒大步的走了,头也不回,馆场里只剩下吵骂声跟脚步声嗡嗡回荡。田鸡和胖宝在一旁嘴张得跟浑天仪下的蟾蜍一般大小,丝丝冒着热气,不知道是该劝我回来,还是给冯林包扎,两双眼睛互相对望着手足无措。
下午,天气不温不热,我一个人坐在公寓里的球场上看一群人打球。绰绰的人影在我眼前忽来忽去,没有留下一丝记忆。
在我走神的那一小会,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头,我扭头一看,冯林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身后,鼻梁上贴了一大块纱布,就像一个戴偏了的口罩。他没有说话,和我一样静静的蹲在围栏边看球。我先是憋了很久,终是忍不住,说:“你要打就打,我绝不还手。”他一巴掌拍在我腰上哈哈大笑,脸上的肌肉一绷紧,又把鼻
![[清]康雍之道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8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