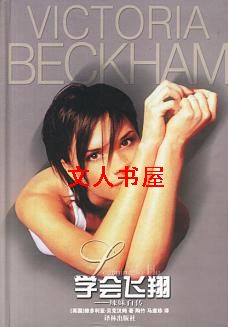搞笑自传笑看人生-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于这两位老人,尚在青春期焚烧的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彼此谈话的时候不多,我只是听别人谈起过天聋。天聋,这老头有点儿玩老不尊。
走在街上,看到路边摆摊的,天聋经常一伸手,或者一把瓜子,或者一个苹果。对面的卖家,十有五六不会和一个老爷子斤斤计较,暗骂他几句了之;也许有几个会沉下脸,提醒一下老头:“大爷,付钱的!”而天聋,都会恰倒好处的利用了自己的天赋,一句“啊?你说啥?”一举击退敌人;偶尔还有一个不死心的卖家,继续大声解释:“我说,让你付钱!”天聋马上就会甩出一张一毛的票子,“来一毛钱的!”
对于范大爷,他是湖南的,一个六旬的老人,还要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打工,背后肯定是有一个让人辛酸的家。相比于天聋,范大爷就显得要好的多,虽然身体上的障碍,使他不能很好的和周围的人沟通,但忙起来的时候帮我们上上菜,或者是下班之后帮我们扫扫地的做法,还是让我们很尊敬这位老人的。记得有一次中午饭,我做卫生晚了点,去打饭的时候,却发现米饭没了。范大爷看着眼前空空的盘子,觉得很对不起我,于是把厨师长老周做给顾客吃的银丝卷端了过来,让我吃了个大饱。一会儿,老周找这些卷子的时候,范大爷“啊……啊”的向老周解释了半个钟头,最后老周挠着个脑袋回去重新做了一份。
看着这两位老人家,我心里觉得王总真有经济头脑淘了两个便宜货的同时,从他们走路的速度和办事的效率来看,王总看重他们的那就是俩字“稳重”。
厨房内部,就是我们这些饭店的精英。这些人,按工作性质,又分成三等。地位最高的是掌勺的师傅,又称“灶上的”;第二等是办料理的,就是为每一样菜备料,又称“堆上的”;第三等就是我们这些小卒子,又称“打盒的”。哥们,就算你取得了厨师界的博士学位,你刚入厨房的时候,也不会让你炒菜,你得先来打盒,然后是办料理,最后才是师傅。
在这个厨房里,有五个灶,也就意味着有五个师傅,后面隔着一张桌子站着我们五个打盒的,侧边的是三个办料理的兄弟。
前面的两位师傅都姓王,咱按年纪称呼为老王和小王。这爷俩儿并且都是标准的厨师身材,脑袋大,脖子粗,并且粗的部位不光是脖子。第一次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就看见这爷俩儿在那吃东西呢,一探脑袋,前面两个碗,哥们,你这是吃葱花呢?还是吃香菜呢?
老周执政的时候,开始可能是对我个性的长相有点儿不能适应,而让我去做这做那,习惯了几天之后,老周就不再管我了,我经常去隔壁的房间抽烟歇脚。这样自在了不到一个礼拜,老周就byebye了,而老王上任了。
自从老王当政了之后,年也已经过去了,来吃饭的人都开始上班忙着赚钱准备明年再来搓一顿了,我们这些人就轻闲了许多,经常去隔壁的房间扯蛋。老王看到这种场面,不大高兴,于是他响应王总“给你钱是让你来干活”的号召,打着“绿化厨房”的口号,烧起了那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所以,我们在老王的领导之下,天天高举抹布,一遍又一遍的擦拭着饭店自开业以来就残留下的油渍污迹。
当厨房里终于焕然一新了,我觉得自己终于应该轻松下来的时候,3月27日晚,老王塞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出勤二十五天整”,他让我去找林总结帐,于是我就离开了。
对于小王,他的事,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喜欢买彩票。虽然暴富的概率很小,但如果不买的话,暴富的概率是零。我估计他频频买彩票的原因就是这么想的。
老李,不过我经常称呼他为“老胡”。理由嘛,很简单,老李虽然身在厨房,但依然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每天干净的衣服,发光的皮鞋,再加上那独特狗舔式的发型,让我一度的想起汉三大哥的身影。
老李,身材上无疑很是对不起师门,倍儿瘦,虽然他在厨房里一直都在偷吃,而且饭量也不小。我觉得他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直肠过长,而导致了营养物质未曾消化吸收便被排出体外。
老李很是担心瘦弱的人出门在外会受人欺负,所以当他看到一个生人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他曾经拿刀砍过人。于是,我在第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便听他讲述了昔日的神勇。
有的时候,我挺嫉妒老李,嫉妒的并不是那淤泥不染的崇高,也不是那举起菜刀的勇气,而是嫉妒他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每次当他扭捏着和自己的孩子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在想,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孩子叫我一声爸爸?
老刘,三十多岁了,隐约记得听人说过他和老婆离婚了,留下的只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管。面对这么一个痛苦的家庭,老刘无疑很是乐观。在老刘炒菜的时候,经常给我一种化悲痛为力量的感觉。你看,老刘炒菜了,双手一捋袖子,摇胳膊晃肘子,敲桌子砸锅的,咦,刘师傅干嘛呢?拿着个锅对着个灯!“妈的,锅漏了!”
我感觉老刘炒菜的技术很高。在厨房嘛,偷吃是免不了的事情,但备料的是根据菜单配料,一份菜就给你一份的料,就这炒出来的菜一小盘子,你一口我一口的一人一嘴那菜也不用上去了。而老刘炒菜的时候,要么多放些辣椒,要么多放些葱花,每次炒完一个菜后,都会多出那么一小盘,让我们品尝一下他的手艺。记得有一次,堆上的就送来三份的料,老刘楞是给他炒出了四份。
虽然老刘年纪也不算小了,但还是倍儿爱胡闹。有着共同爱好的我,和他走的比较近乎。老刘告诉我,他有两个大忌,一个是别摸他脑袋;第二个就是别扔他饭盆。
这两个大忌我都有幸犯过。对于他的脑袋,刚来的时候我摸过一次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他脑袋上有一个大疙瘩;对于他的饭盆嘛!我们吃饭一般都用盘子,老刘担心盘子刷不干净,特别找了个小缸子当饭盆,不过饭后经常不刷。就那满是残羹的小缸子往桌子角上一放,我的职责就是保持桌面的整洁,不扔它的话那不是不尽职吗?
老刘挺喜欢下象棋,水平很是一般化,不过相当有个性。怎么跟你说呢?一般人下象棋,都是车马炮齐头并进,互为辅佐;而老刘,显然更热衷于单枪匹马,让每一个棋子都有施展自己拳脚的机会。
经常看到老刘后方线上原封不动,一个马在前线胡窜乱蹦,呀,憋死了!换个子,继续上。其中,老刘最为喜欢的棋子那就是卒子,他说他想试试小卒子能不能撵的车呜呜的。所以和老刘下棋的时候,经常是到最后把他过河的杀光,而不是将死。有的时候,我也挺害怕和老刘下棋的,万一一个不小心,让他一个卒子单刀过来给憋死了,我以后还有脸下棋吗?
第二章 跑堂(6)
黄师傅,他是我的师傅,这二十五天里,我天天伺候着他。他也挺照顾我的,这段时间里,屁大的事他都会让我代劳。
让我去做什么我无所谓,我尽力去做,但老黄又不大喜欢说话,需要什么的时候经常向我比划手势。小圈是小盘,大圈是大盘,双手做个酒盅,那是小蛊子,(蛊子就是盆,我也是来到饭店才知道的)双手往外一张,那是大蛊子。
跟着黄师傅混的日子里,我经常觉得自己的领悟能力实在太低,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似乎多少学会了一点儿哑语。有的时候我看不懂他的手势,我就把门口的地哑招呼过来,让他帮忙。
记得一次,黄师傅手画了一个圈子,我一看这大小,介于大小盘之间,赶紧一个大盘一个小盘放桌子上,大哥,随你挑。黄师傅一摆手,再画一个圈,紧跟着指了指自己的。看那手指的指向,应该是脸部,圆圆的脸,这应该是啥?奥,我明白了!这个比喻真是贴切啊,我赶紧把一个鸡屁股端了过来。黄师傅大吃一惊,一反往常的吐出了俩字:“蛋黄!”
黄师傅炒菜的时候和老刘大相径庭,如果说老刘炒菜是浑身充满着激情,而黄师傅炒菜则显得循规蹈矩,给我一种孔夫子教书的感觉,并且他在菜的分量上拿捏的比老刘更为精确。一份料送过来,经过黄师傅的翻炒之后,就会变成一盘再加上一小勺,然后他亲自负责把这勺菜解决。
黄师傅脾气不好,经常犯急,朝我发脾气,尤其是在倍儿忙的时候。作为他徒弟的我,真有点儿有苦说不出来。你说吧,你需要啥东西,你告诉我一声,你又偏偏不开口,一个劲的在那敲桌子。初来乍到的我,我知道你用啥啊?真的很难适应,我知道你急,你以为我不急呢?
我虽然爱说笑,但我知道自己脾气也不好。我知道自己混到现在这种田地是以往不务正业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一直在忍!我为了避免俩人之间起冲突,所以当厨房里来了一个新打盒的之后,我让她去伺候黄师傅。但黄师傅,又好像很舍不得我,仍然指示去我做这做那,我尽量满足你。
终于有一天,黄师傅敲着桌子朝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忍无可忍了,我没有说我不知道你要我去做什么,我只是说出了三个字:“我不去!”
对于这种明显的反抗,黄师傅有点儿下不去台阶了,他走了过来,硬撑着面子,扯住了我衣领。
当时的我,低声告诉他:“我最讨厌别人扯我领子!”
黄师傅还是没有放手。
当我准备抬起脚的时候,老何把我拉开了。
老王给了我那张纸条。
我知道并不是由于这一件事,我才被解雇的,这张纸条是老王在这事发生以前就已经写好了的。当我去找林总结帐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让我走,他告诉我,饭店现在不忙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担心我的学业。靠!
当黄师傅不朝我敲桌子发脾气的时候,我还是认为他,人挺好的。一句“晚饭想吃啥口味”,经常把我说的暖烘烘的;再加上他打电话的时候对家中父母的牵挂,更是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
记得有一天,忙碌了很长时间的我,感觉倍儿烦气,于是把怨气发泄在该收拾的料盆上,扔在垃圾箱里的时候,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黄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情,告诉我:“看啥不顺眼,就扔!”
“我如果说看你不顺眼呢?”
“扔!”
王姐,四十岁左右年纪,在这里干了一年多了,工资还是800,虽然她属于打盒的领班,每一个新来的都会听她指挥。同样,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听从她的调度。
记得我来的时候,我告诉大堂经理我是一个大学生,开始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后悔说这话。显然,在厨房里打盒的大学生和大众不属于同类,王姐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仇视知识分子虐待文化人的倾向。
我只知道,只要王姐能看的着我,我就甭想闲着。所以,我很讨厌她,心里也不知道骂了她多少句。不过在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对王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事情很简单,那就是菜里突然冒出的一个鸡爪子让王姐捞了上来,她却把它夹在了我的碗里。虽然我真的很讨厌吃鸡爪子,但对于她的好意,我还是觉得心里一阵暖意。
王姐是负责给小王打盒的,她比我还累,因为每天把五位师傅的料盆备满,也属于她的工作范畴。
宋姐,年纪不大,算是有点儿姿色吧!不过,她嘴唇角上好像有一丝天生的缺陷,开始我以为是葱花沾在了上面,但时间长了,我逐渐的否定了这个想法。我眼睛不咋地好使,又不看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虽然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仔细端详一番查明真相,但我始终在害怕引起她的误会而不敢直视,所以到了今天,我还是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么一个我感觉暗无天日的厨房里,宋姐的出现无疑让我仿佛感受到了阳光。记得一次我切香菜的时候,不小心切了一根手指,所幸无啥大碍。宋姐一直都在嘲笑我,说我是高手,切香菜都能切得了手。世事真的很难预料。第二天,宋姐切香菜的时候也成了一位高手,比我伤的重,在家里休息了两天。
宋姐是负责给老王打盒的,自从老王升官了之后,作为厨师长的首徒,她走起路来也背起了小手,“一人升官,鸡犬升天”是不是就这副德行?
小辉,东北的,才十八岁,在意识到“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后便跟随着表姐,来到这里打工。在这里,年纪小了,很有优势,大哥姐姐叫个不停,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孩子。
开始的日子,我对打盒真的很不适应,真的很想逃跑,但当看到小辉的时候,我一直都在鼓励自己:像人家十八岁的小孩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后来,小辉走了,过年的时候饭店忙,不让他回家,十五之后,他回家看看去了,到底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