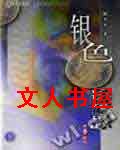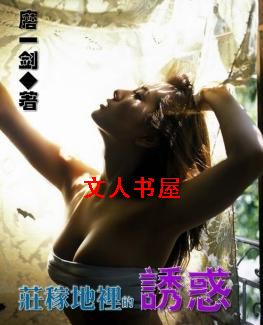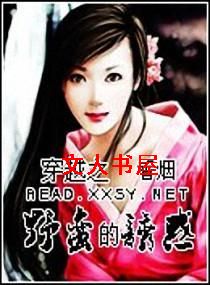诱惑-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争取增加办公经费,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再上一个新台阶。”告别黄校长,我的调查报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经费的内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国家教育经费流失,杜绝滋生腐败的温床。失学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为我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第二部分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和乡办秘书小白正往王家坡小学赶,走在深山老林中,忽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枪响后,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二十米外的地方蹿了出来。少年手提一杆猎枪,像只豹子,动作异常敏捷,连蹦带跳地向前冲去,在树林中时隐时现。我和小白跟着少年跑,大约跑了百十来米,少年站住了,举枪就要射。在少年的枪口下,是一只东张西望的小麋鹿。“不要打!”我大吼一声。我知道野生动物是不能随便捕杀的,面对偷猎行为,本能地表示出强烈愤慨。少年扭过头来,看到两个陌生人,脸上一片茫然。他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长得虎头虎脑,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透着寒酸。“不能滥杀野生动物,你知道吗?”我走过去,大声训斥少年。“俺不知道。”少年放下枪,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四五十米外的小麋鹿。小麋鹿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你是哪儿的人?”我问,口气缓和了一些。“王家坡的。”“带我们去吧,我们正要去王家坡小学。”小白说。“俺爹会生气的。”少年说。“为啥生气?”小白问,“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你爹他不会生气的。”“俺没打着东西,俺爹不让俺回家。”“我们陪你回去,你爹不会说你的。”我拍了拍少年的肩头。路上,我和少年边走边聊。少年很纯朴,毫无顾忌地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少年名叫朱同,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那一年,他爹把腰摔断了,从此卧床不起。他妈妈在一天清晨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残废的爹以外,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三四年来,他一直在山里打猎,一家人就靠他的猎枪生活。少年说他不知道打猎违法,也不知道不让打猎之后一家人怎样生活下去。“想上学读书吗?”我问。我认为少年需要用智慧武装头脑,我就是靠头脑里的知识从井下跨进北大校园的。“想,俺当年的学习成绩可好了,可俺进不了学校。”朱同回答道,“家里没有钱供俺读书,俺需要挣钱养活一家人。俺家到了。”朱同的家是三间低矮的石头房,小院是用树枝和玉米秸圈起来的,一群土鸡在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寻食,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迎了上来。“奶奶,他们是客人。”朱同对老太太说。“快屋里坐。”老太太张罗着。屋里的炕上躺着一个中年汉子,头发和胡须很长,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进屋后,我环顾了一遍房间,得到了满目凄凉的感觉。中年汉子用胳膊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请我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用机警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后,问儿子:“同儿,是来要货的?”“不是,他们是乡里干部。”朱同回答道,“他们要去学校,顺便到咱家里来看看。”“有啥好看的?以后不要啥人都往家里领。”中年汉子的脸阴沉下来。“知道了。”朱同回答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我是乡里的秘书,这位同志是市里来的讲师团队长,到你家来是抬举你。”小白发火了。“俺不需要抬举,想买山货俺欢迎,不买山货来干啥?”“买山货,买啥山货?你知道不,随便猎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的。”小白不依不饶。“杀野生动物违法?不搞点山货卖俺们吃啥?让俺们一家老小饿死就不违法了?”中年汉子并不畏惧权势,他要争自己的生存权。“小白,我们先走吧。”我拉起小白往外走,和一个端着一碗水的小姑娘差点撞在一起。“叔叔,你们要走吗?”小姑娘问。她的眼睛大大的,明亮得像两颗宝石。“是啊,叔叔还有事。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朱桃,”小姑娘答道,“喝了水再走吧,奶奶刚从井里打出来的,可凉了。”我接过碗喝了一口,凉得冰牙,又连喝了几口,把身上的燥热去掉了不少。“像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救济吗?”出了朱同家,我问小白。“估计得不到。”小白说。“为什么呢?总得给他们找条活路吧?”
第一部分 诱惑 5(5)
“像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乡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养活他们。”“有多少呢,统计过吗?”我想知道这些需要关爱的人和那些吃空额的人到底哪边人多。“没有统计过,因为乡里没有钱救济他们。”“小白,有些事我觉得很奇怪,需要救济的却没有钱,不需要救济的却按月从国库里拿钱,你说这事怪不怪?”“您是想说要能调过来就好了?”“是啊,需要救济的每月可以得到救济,不需要的就别再伸手了。”“宋队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您的想法不可能实现,连我都不会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两个亲戚也在吃空额。别的干部能让亲属吃空额,我为什么不行?反正是国家的钱,你能白拿,我也能白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谁不拿?”“照你这么说,当上干部就会有很多既得利益?”“那当然了,你以为光是为人民服务,谁没有个小九九?不为自己盘算好了,别说亲戚们骂你了,就连你的同事都会骂你,而且你肯定会干不长。这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你是说,如果调过来就会触动干部们的既得利益?”“那当然了。为什么行不通?就是有干部的既得利益在里面。这里是谁的天下?是干部的天下。”“别人我管不了,朱同一家能不能作为特例给解决一下?”“有什么意义呢?解决一个朱同,还有九十九个等着呢,这个口子谁敢开?”“那就让他们通过违法的方式来维持生存吗?”“这是领导考虑的事,咱没担任那个职务,不操那份闲心。”小白讲的是为官之道,我明白这里面的奥秘,该你操心的你操心,不是你管的事你最好想都不要想,越级越位是官场大忌,等于自己踏进了雷区。但是,作为一个讲师团成员,和这里的官场没有直接的瓜葛,把我所看所想写进调查报告,应该没有犯忌。在曹子营中学,我遇见了两个充满理想又备受理想折磨的年轻人。这是一对和我同时走出大学校门的夫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学艺术,一个学化学;男的叫施才,女的叫文烁。我是在小白的建议下来的。小白说曹子营中学值得一看,但马上又叮嘱道,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去曹子营中学,和他可没关系,就当他什么也没说。“曹子营中学有鬼吗?”我问小白,我不喜欢没来由的神秘。“不是有鬼,是有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大学生能到这里来支教,应该是好事,有什么不敢让人知道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他们搞的那一套,从上到下都有反对意见。”“有反对意见很正常,关键是看他们搞得对不对。”“说不准,您看看就知道了。”我到学校的时候,施才和文烁都在上课。一个自我介绍是教导主任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们。教导主任简单寒暄之后,就带我们参观起校园。曹子营中学的校园和别处不同的是,学校有养鸡场、羊圈、鱼池、蘑菇大棚,给我的感觉这里不像学校更像农场。“你们这里的副业搞得不错。”小白说。“这些都是孩子上课的课堂。”教导主任纠正道。“那学什么呢?”我问。“实用农业技术。”教导主任说,“施校长说了,农家的孩子一定要学农业技术,将来好有生存的技能,光学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行的。”“看来施校长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想起了以搞职业教育而名垂教育史册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当初就是主张半工半读的,用行动来获得知识。“是啊,不过有的做法这里的人并不完全接受。”教导主任说。“什么做法人们不接受呢?”“我带您去看。”教导主任前面领路,来到一排房子前。“您看,这是当年的知青宿舍,施校长硬是让初三的学生全体住校,说是有利于孩子们的学习。”“住校是有利于学习,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对施校长的做法投了赞成票。“这是在农村,很偏僻的地方,不是在城里。上初三的孩子们都十五六岁了,下学要帮家里干活的,留在学校,家里的活谁干?再说了,男女生住在一个院子里,要是出点男女方面的事,谁担待得起?”教导主任不无忧虑地说。“施校长怎么说?”“他说,这些想法都是小农意识,教育孩子们,就是要让他们脱离小农意识。”“孩子们接受吗?”“孩子们当然接受了,不用干活了,晚上还有电视看。可家长反对,有好几个家长要给孩子退学,孩子们不干,有个叫张红的女生被家长拽回去之后就喝农药了。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闹出人命来。”“宋队长,这个施校长不是在办学,他是在搞一场革命,这是他和乡长说的。”小白插嘴道。正说着,下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纷纷从教室里跑出来,在院子里追逐打闹。我注意到,这里的学生从着装上和别的学校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但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没有农村孩子们常见的木然表情,他们拥有和年龄相符的快乐,像一群在乐土上自由嬉戏的鸟儿。
第一部分 诱惑 5(6)
施才从孩子们中间穿过来,小白做了介绍。施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等个儿,鼻梁子上架着副无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此刻漾满笑意。他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市里终于来人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你们这里搞得很有特色。”我说。“来听听我们的名著名片欣赏课吧。”施才发出了邀请。我随着施才来到录像室,里面已经坐满了学生。一台二十九寸的电视摆在讲台上,施才安排我们坐下后,对学生们讲道:“今天的名著名片欣赏课,我们来观看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改编的电影。要求是:第一,写下故事情节;第二,写出观后感。明天上午交作业,下午开讨论会,每个同学都要发言。”《老人与海》?我的感觉很奇怪。施才让海明威与大山里的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教室里很静,只有影片里的声音。海明威和他的大海离这里并不遥远。孩子们被影片吸引住了,好像一片翠绿的小苗正在沐浴春雨。他们并不是看不懂,人类某些共性的东西完全可以跨越地域、种族、年龄、知识结构等篱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施才为了欢迎我的到来,晚上在学校操场上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住校的八十多个学生参加了晚会。晚会的台子就是操场的主席台,在主席台下燃起了两堆篝火,篝火上烤着两只山羊。当香气四处弥漫时,晚会开始了。这是我参加过的一个最具震撼力的晚会,我完全没料到山里的孩子竟然表演了那么多令我吃惊不已的节目。女生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由六个女孩子上来表演。动作有些笨拙,但她们的表情却是那么开朗;男生小合唱《游击队员之歌》,四个小伙子落落大方地站在台上,配合默契地唱出了他们的风采;女生小合唱《雪绒花》,二十个女生竟然用英语演唱,发音准确,声情并茂;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山里娃居然潇洒地拉完了全曲;话剧《雷雨》片段,八个孩子演得有板有眼……我的眼睛湿润了,如果这些节目是城里的孩子演的,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在满处是文化的大环境中熏也能熏出个一二三来。这是在与城市文明相差不知多少年的大山里,孩子们能表演节目,先不说表演水平,就说走上舞台,已经是太不容易了,他们要冲破多少禁锢才能把青春的光彩展示出来。“一年多以前,他们还什么都不会。”施才用刀子拉下一块肉,递给我说。“你们为什么想到来这里办教育?”我问。“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曾来过这里,被这里的风景迷住了。”文烁回忆道。她是个娇小美丽的女人,青春的光彩还在她的额头上闪动。“当时我想,要是能在这里生活该多好。”“所以你们毕业后就跑到这里来了?”我问。“没那么简单。”施才说,“毕业时,我们认真讨论过将来的工作问题。服从分配,肯定是留在市里的机关或学校;自己找出路,文烁的姑姑在英国,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考研究生,我是没多大问题,文烁就没机会了,因为艺术系不招研究生。我们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也算是磨练自己吧,就想到了这里。和学校谈,和市教育局谈,和县教育局谈,所有的人都劝我们认真考虑,这不是儿戏。他们越这么说,我们越坚定,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