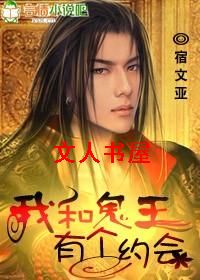我和母亲的情人-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是,成|人总是在纷乱的家庭战争中以孩子的名义去维护所谓的和平。
当我从电话里听到你疲惫的声音,我的心很痛。我们有着多年的友情,我能够想象出你的痛苦,你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祝你快乐幸福!好人好梦!
你的朋友 新
看完信,我犹疑了。
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爱情,信的作者更像一个理智的教育专家。特别是这句“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使我更加难以判断这个“新”到底是不是钟新呢?我终于又寻觅到蛛丝马迹——夜已经很深了。北方的空气中还潜伏着寒流,而楚江,此时应该已经是春天了。——是的,一定是钟新,北京的钟新。
目光久久停留在这封信上,我差点被这个男人打动了。没料到,他竟然以如此柔软的笔触去谈我,从信中,我读到了宽容和呵护。我想起了那个夜晚,我因为与母亲斗嘴而任性跑出家门的夜晚,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也彻夜未眠,为我。他和母亲谈到有关我的教育问题,这是出乎意料的。然而,这封信并不能成为我对这个男人产生好感的理由。
不能再犹豫了,我决定带上文稿,去寻找母亲的秘密。
一周后,我辞去广告公司的职务,带上仅有的500元钱,在医院和母亲父亲告别。
当我走进熟悉的病房时,父亲正在扫地,大概实在闲得无聊,见我进来,特别是见我的旅行箱,异常吃惊,听我说辞了广告公司的工作想去北京,他说:“宝宝,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没有看父亲,眼神空空荡荡:“爸,我想,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您知道,母亲的病也需要钱……”
眼角的余光感觉到父亲只是模糊一团,他叹了口气:“你能改变什么?唉,你大了,知道你的性格,拦不住你……”
我看着父亲,不过大半年,他憔悴了许多。很快,我又把目光投向母亲,母亲安详地躺着,液体一滴滴流进她的体内。我走过去,拉她的手,揉搓着。
我清楚我的生活即将变成一团糟:已经到来的冬天和伴随而来的寒冷、仅有的500元钱、孤独、母亲的秘密、一个我仇恨的男人。
就像现在。独自住在这个小平房里。
()免费TXT小说下载
未知生活已拉开了序幕。
眼角无声滑过两行泪。
我呆呆拿着手机,那陈旧淡黄的机身在我眼里模糊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又好似一块坚硬冰冷的石头,而手掌心,已被石头的尖角刺透。
11
北京的冬天太漫长了,可惜,它不是青春期。
漫无目的地走在天桥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天桥,反正看到台阶,一脚就踏了上去。带绒帽的超薄羽绒棉袄,宽大边沿帽空空落落地罩在我的头上。
走在蝴蝶结形状的天桥上,整个人随着桥身在微微抖动。瞥一眼四周,目光顺着脚下的铁板平移,又滑过栅栏,继续向下,我看见公交车宽敞性感的脊背:鹅黄的、淡蓝的、深绿的,如各式各样的鱼儿钻入桥底。本来,它们是向着我而来的,可是,在渐近时,明显达不到我所要求的高度,或许因为本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只是在此之前没有感觉到而已,于是,就逃掉了。
也有从另一边钻过来的:鹅黄的、淡蓝的、深绿的,性感的脊背,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这些是没有心理准备去迎接的。在这来来往往中,我的脚步轻了起来,身子轻了起来,虽然人仍然木木地朝前走,但心里却把自己当作了一朵彩云。我想:要是跃过栅栏,如一片叶飘落下去,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1章(11)
自从来到北京,带着母亲的秘密离开孤独的父亲,我脑子里经常出现种种奇怪的念头:拥挤的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海洋,它分娩了数不清的波浪,而且永远不停地生产着。它没有爱情,但是欲望却能使之怀孕。这样的城市偶尔落下一两片叶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不就是这样一片叶吗?它不是果实,却熟透了,便挣脱捆绑自己的柔韧绳索,逃了,留下了满身的伤痕。至于它的脉络纹理、它的爱恨情仇、它的血液是沸腾抑或是冷酷,只有它自己知道。
在冬天的北京城,我走着。我怀疑自己真的病了。觉出了冷。只要生病,不管冬夏,我就会觉得冷。此时,我又觉出冷来。这种冷不是身体对外界冷空气袭来时的反应,而是来自自身。我的腿裹挟着一股冷风,它们钻入骨髓,怎么都摆不掉,身体的表面仿佛涂了一层冷凝剂,所有的冷空气一来到四周就紧紧搂住了我。
我想找个没有风的地方坐下来,渴望喝点热热的液体来驱散彻骨的寒冷,我甚至渴望就在此时邂逅生命中的白马王子,他是个男人或者男孩,有一间小小的暖和的房子,眼睛里能发散出太阳般温暖的光辉,我要他将屋子里所有的灯全打开,我需要他的肩膀和温度,我想在这个男人或男孩怀里昏睡三天三夜。
没有王子,白马倒是经常看到,在动物园里。
终于,胡同里飘来的香味钻进了鼻孔,我下意识在鼻尖处深吸一口气,贪婪的。走近一看,果然,是一家孝感汤圆米酒店,一个漂亮的湖北女人在炉子边搓着汤圆,小小的、白白的、圆圆的,它们从女人的手掌心滑落进沸腾的水里,就那么看一眼,我身上就有了一丝暖意。
在角落坐下来,要了一碗汤圆米酒。一片水雾弥漫开来,它笼罩打湿了我这只流浪的小猫。食物,是最挚爱的亲人,在我们饥渴无力丧魂落魄时,它没有空洞的语言只有忠实的行动,它给我们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和温暖,它进入我们又不霸占我们,它只会牺牲自己,成为我们的血液。
若干年后,当我回忆起这碗饱含家乡气息的汤圆米酒时,我久久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恩,眼波里荡漾出只有回忆起亲密爱人时才会有的柔情。
12
终于有了进攻的力量。
我掏出那个奶黄|色手机,以母亲的名义给这个叫钟新的男人发出了第一条短信:“新,你好!在干什么?”
新,这是一句令我恶心的称呼。
那些滑下肚的汤圆,如元宵节夜晚的灯笼,点燃了,苍白顿时变得火红,然而,顽童提在的手上,颠簸着欢笑着四遭游走,有一种即将被毁灭的悲壮。整个夜空,宛如一只巨大的胃,忍受着被刺痛被划破的阵阵痉挛。
手机屏幕上掠过淡蓝的光,瞬间照亮了我纯洁狡黠的笑。当一个女孩把她所拥有的全部智谋及精力全身心去做她生命中所认为的最重要事情的时候,这种顽固的意志是非常可怕的,人们仿佛看到貌似坚固的城墙在口腔里被咀嚼,瞬间绽放成花朵。而春天,在几秒钟里凋谢,严冬幻化为一匹白色骏马飞驰而来。风中,一切根基在摇摇欲坠,惊雷把江南黑瓦劈成一节节痛苦蠕动的蚯蚓,血液已经凝为屋檐下的冰凌,只剩下屠宰自己的勇气。城墙脚下已绣满蚁|穴,千年混凝土被蝼蚁们丝线般的牙齿勒碎,变成美丽轻盈的沙粒。
只需一掌风,就能摧垮一座城池。
我想象着这个名叫钟新的男人——他是男的,他在北京,这些勿庸置疑。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他是何职业?多大年纪?与母亲是如何相识?……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来一一解开,就像中学时所做的证明题,用尽可能少的已知条件来求得最有说服力最准确的证明。
胡同里传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等报纸的叫卖声,声音是报亭的老板预先录好的,并非现场直播,一场公开的叫嚣的预谋。
手机许久没有动静。
我有些失望。自从发现母亲的秘密,钟新就再也没有发来只言片语。8个月,整整8个月,不问生死。气若游丝并不等于销声匿迹,毕竟,线还在。这手机,却如同被装了定时炸弹,又如被置了窃听器。我猜不出钟新不回短信的原因,难道真的如他所说的相忘于江湖么?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1章(12)
我思考着下一步。
假如他真的不回短信怎么办?那自己不是白费苦心吗?在手机完全坏掉之前,我决定必须坚持不懈的把短信发下去,只到他回复为止。
想到这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湖北女店主接过钱,笑眯眯地说:走好。我点点头,下了台阶。
胡同里站了几个卖菜的农民,他们把菜蔬摆成整齐划一的几何图形,在寒风中观望着。丁字形胡同的尽头,偶尔闪过几辆自行车,东来西往,在视线里交织着,也如那些菜蔬一样,成为一种游戏。
我决定换一钟语气发第二条短信。在走出胡同口的时候,第二条短信已经到了钟新那里。
“钟新,我是莹。我想你。”这样的文字对于母亲来说也许是种亵渎,但是,在这场神秘的爱情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心动魄呢?漠然、无知,也许才是最可怕的。
胡同的拐角处在卖《法制晚报》,一个铁喇叭喋喋不休的对路人说:“法制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法制晚报……”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成为真理。仰头,刚才还明亮的天在法制“晚”报的劝说下果然暗了下来。
异乡的茫然就如这眼前渐近的天色,昏暗无边。我甚至想到了退缩。想起母亲,想起父亲,拨通电话,那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宝宝,吃饭了吗?北京冷不冷?还好吗?快点回来吧!”
我说:“爸,您放心吧。我今天赶了两场招聘会,北京机会很多,您就放心吧,我已经长大了。我要挣钱给妈妈看病。”
“傻孩子,在外面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父亲的声音透着怜爱。
“爸,你也是,别太累着。妈妈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老样子。”
电话那端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它,落到耳里,成为我的乡愁。
13
又度过了茫然、毫无意义的一天。
钟新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两条短信大概还不足以打动他那坚硬的心。我怀疑他的手机关机或者换了号。于是,我决定冒险试一试,准备直接拨通他的电话,一声不吭,然后很快挂掉电话。和他通话,是万万不行的,倘若露了马脚,我将前功尽弃。
一进平房院子,我就听到了何大爷的声音,大概又出什么事了。现在好像一直是何大爷在主事,肥胖的何奶奶已经好久没到院子里来。在各家小窗映出灯光的照射下,何大爷青铜色的瘦削面孔如一个话剧演员,激动,他的唾沫浇灌着因长久发言而略显干涸的语言:“又堵了,掏了一下午,我今天就守在这儿跟你们一个个地说,以后不要再把什么菜叶儿呀茶叶末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水池里倒,我都说了一百遍了,下水管堵了,不方便的是你们,这还是大冬天,赶明儿到了夏天,你们弄堵了,那个臭味儿你们自己尝去!”
我就站在何大爷旁边听,平房的铁门“吱呀”一响,严大姐推着自行车进门,从超市回来了。
“ 何大爷,怎么啦?”严大姐人没站稳,急切地问,好像她专门为何大爷的事赶回来的。
何大爷转过身,清了清嗓子说:“又堵了,掏了一下午,我今天就守在这儿跟你们一个个地说,以后不要再把什么菜叶儿呀茶叶末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水池里倒,我都说了一百遍了,下水管堵了,不方便的是你们,这还是大冬天,赶明儿到了夏天,你们弄堵了,那个臭味儿你们自己尝去!”
严大姐接过何大爷的话说:“是啊,住在这里都要自觉,有的人,素质就是低,明明知道下水管会堵,还往水池里丢东西!”边说边去收她早上晾在院子里的被单。被单从绳子上取下后,还僵硬着身子,如一张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千张皮。
“对了,小严,你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已经过了一天了!”何大爷说。
“哦,知道了知道了。这几天忙着忙着就忘记了,明天下班回来交可以吗?”严大姐边说边掀她家的厚布门帘。何大爷怕她进去没有下文,赶紧说:“今儿有钱的话就交了,我也难得碰你们,既然租房,我觉着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好,一是一、二是二,实在。”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1章(13)
在他们说话的当口,我开了自己的房门。本来准备此时拨钟新手机的,但如此热闹的声音背景很容易引起钟新的怀疑,我决定等安静下来再拨比较合适。
头晕。
脑子里何大爷的那些话又旋转起来。
()
我不明白何大爷为什么能一字不差的把那些话背下来。在密集的时间里把何大爷的话听两遍这也是我头晕的原因之一。我不喜欢被灌输。何大爷的话就是一种灌输,而且是等着院子里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