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缘千里-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好的小日子,说个完就完。刘芳那小女人,心里主意大看呢;说回城就回城了, 我他妈一点也看不出点兆头来,光他妈想跟她过日子 妈X 的,盖新房的二百块钱都凑齐 这女人,多他妈没良心!拍拍屁股就走 要不是念她几个月的情分儿,我非打她个乌眼儿育,给她留个纪念不可。后来的事儿证明她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高级妓女罢 上了大学, 又当了记者当了演员播音员,名儿挺好听,主持人,又怎么 还不是靠男人活着? 三十大见了,卖她妈骚。傍大导演,我看你徐娘半老了傍到哪一天!我的款不够她傍的,没钱给她拍电视剧,拍MTV ,就装不认识我 狗x操的东西!连跟我跳个舞都有气无力的。我真纳闷儿,李大明能给她什么,这两天她对李大明党那么贱,那么骚!
我算让这娘们儿给涮 她一走,心就凉 原先想着在乡下盖几间瓦房跟刘芳过日子的好梦落了空,这才觉着没劲,想起巴结支书队长,弄个指标回北河。我操,回北河扫大街也成!下来的时候还想蹦达一下子,或许能闹腾成个张铁生邢燕子什么的,当个先进知青典型。都他妈方新害的,让我们早下来早占地方,才能早奋斗成名人。信了他的话,下来了,傻X 似的,让村里给秦到村边上的破知青点儿,跟流放差不多,想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都没机会,人家像防狼一样防我们。都他妈前几批知青闹的,进了村就跟拆白党似的偷鸡摸狗什么都干,女的为了回城就踉村干部睡,弄得人家家里老婆孩子见女知青就骂“破鞋”。唉,反正我们没赶上受欢迎的时候。也不知道报上说的那种贫下中农把知青当亲儿子亲闺女的事是真是假是啥时候的事儿。
走后门从烟厂弄了几条带把儿的《春美香》送过去,王八蛋操的支书瞅着大黄牙说给我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去参加“根治海河”冬季大会战,管饭,有大米白面,吃个够,村里还给算工分儿,这可是人人巴望的肥差。每年分几个外出干民工的活儿,这几个村干部就能小发一把。
说是去“根治海河”,其实压根儿没见着海河的面儿,是去修理一条什么干牙河,离海河远着呢。浩浩荡荡带着行李推着独轮小车像电影上的支前民兵似地去了,走了十来天,走到了一条大河边上,带队的说就是这儿,让你们怎么措怎么填就怎么着干,这任务光荣着哩,上游治好了发了大水不往海河里乱灌,海河就不会发大水,天津就保住了,保住了天津就等于保住了首都北京。这两个大地方不出事,中国就太平无事。妈的,敢情我他妈上工地来是保卫天津来的。怪不得那些天津知青那么牛X 哄哄的,原来毛主席都下命令要保住天津哩。小时候,六三年吧,北河发大水,淹了个透,听说就是为了保天津,炸了白洋淀的大坝,把水往低处放。唉,人还得生在大地方,老天爷想毁你都不容易。
就那么住进了四面透风的大棚于,喝白菜汤啃窝窝头,一天到晚挖河推车,果个贼死。身上开始长虱子,到晚上大伙儿就脱个精光拿虱子,我的妈,一疙瘩一片的老老少少虱子。奇。сom书光着屁股跳,虱子就哗啦啦往下掉,像是长在肉里头一样。棉袄棉裤成了虱子窝,一抖落,嘿,雨点儿似地往火里掉,一个个儿肥实实的虱子成群结队掉进火里,烧得僻叭乱响,一会儿就烧出香味儿来,跟烤肉似的,馋得大家直顺嘴角流哈喇子。肚子里没油水儿,恨不得凑一锅虱子炒炒吃折腾完虱子舞,钻进凉乎乎的被窝儿,浑身乏得要命,可就是睡不着。刘芳回去些日子了,心里空落落的不算,浑身不自在。一个人光打溜儿地贴着油乎乎发凉的被子,那东西就长,一身的力气没处儿使,真想拿把刀桶下去咕嘟嘟放放血。没办法,上手,撸几下子,越橹越起劲,就止不住,直到开闸拉倒。连着几天下来,推车挖泥就没了力气,脚底下发飘,手握着车把,把上像抹了油老往外出溜,连人带车从晃悠悠的桥板上折了下去。
河床子上头的土都挖喧腾了,算是救了我一命,没摔死,摔了个头破血流……
已想得利用一下这一脑袋绷带。不出三天,就带伤上了工地,照样尖尖地推小车儿,号称:“轻伤不下火线”。就这苦肉计引来了工地通讯员,写了篇通讯上了指挥部的《海河战报》,小小地出了一把名。
成了小名人儿,受了几次表扬,就不能半夜里干那个了,让一大棚的乡下人发现了汇报上去成什么 可是那黑咕隆咚的日子又实在难熬。 我是在学校出惯风头的红人,也算个文化人儿,老混在这群卖傻力气的乡下人里头胡吃闷睡也不是个滋味儿。人家家里有炕头上的老婆熬几个月回去亲热去了,口袋里揣一把钱,生生儿把老婆孩子欢喜死。没老婆的,仗着这把钱,也能买点时兴的东西给村里的对象。我他妈算怎么回事?为谁忙乎一通儿?唉,大半夜子牙河上的北风狼一样嚎,摇着木头棚子嘎吱嘎吱响,小贼风儿滋溜滋溜地往被窝儿里钻,让人睡不踏实,连梦都做不安生。那些个上老冒们照样呼哈打得山响,嘴里叨叨着什么,还有磨牙的,放屈的,莫名其妙大喊大叫的,咧着嘴大笑的,梦里头不定在干什么呢。一到后半夜,起夜的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弄得我更睡不着。就想起小时候着的小,好像里面的解放军英雄烈士啥的都是半夜钻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习毛主席著作,连长什么的查夜发现了,不仅不批评,还表扬。这黑灯瞎火的大棚子里,大睁着两眼睡不着,瞎想胡想也得出毛病,倒不如也学着人家那样儿学学毛选。
说干就干,第二天就打了手电念起来。一连好几天也没碰上工地领导来查铺。
民工可比不得军队里头,谁拿你当人?还查铺呢,整个儿一个猪圈,狼来了叼走一个都没人知道。
我这边傻愣愣地念《毛选》,工棚里却慢慢热闹起来,半夜三更的大周村来的傻三儿、六子和黑子在蠢蠢欲动着,像在打着什么暗号,一个接一个地轮班儿起夜。
一出去就好一阵子,回来钻被窝儿,叫另一个人“去吧,真他妈舒坦。”那人便赤溜溜地捂上大衣出去。我开始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儿,以为这些乡下人在搞什么破坏活动。 他们能干什么 炸大坝?炸河床子?偷东西?穷得叮当的乡下人,连根绳子都是好的。可眼见他们又被看大衣回来,仍然赤条条一个,什么也没带回来,钻进被子蒙头大睡。这就纳闷儿
那天我终于跟着黑子出了工棚。伸手不见五指,迷迷瞪瞪跟着那小子,一溜小跑儿,却原来是往做饭的大棚子那边跑一头扎进柴草棚子里去。就听见里面那胖大婶儿懒洋洋地哼哼着:“稳猴儿哟,都第三个了,上大兰子那边儿去,老娘不伺候”
随后就传来那爷们儿的声音:“她傻X ,我不X 她,我的钱是给你的,你甭偷懒儿,白拿钱呀!”“什么傻不傻的,一样,是个母的不就行了!我他妈哪儿能一下子接三个,非戳巴死我不行。”接着是一阵子拉拉扯扯,那老女人长叹一声顺了他。妈的,他们敢清是轮班儿干这个,连他妈个四十大几的精娘们儿都不放过,真他妈孙子!我不想再听那小子的吭吭啼啼声,都第三回了,有什么意思,再这么下去非惹一身脏病不行。胖婶儿这一夜够受的,非让这群畜牲折腾残了不可。老公还以为她在工地上老老实实揣馒头熬白菜呢,敢情人家人到四十猛如虎,好么,业余挣的比正业还多,无形中还起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虽然我知道那种地沟有多么脏,可还是让他们搅得心里乱得慌。睡不着,就又翻身起来打着手电筒学毛选,苦念一阵子还是念不明白,死念,我就不信这些最高指示我念不清楚。想当年李大明他才上初二就学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装模作样儿拿这东西吓唬我,让我当众现眼。
两年多过去了,我又长了两岁,还能看不懂?我也木会比李大明差那么远吧。好容易念进去几句,那黑子完了事儿钻进来了,吸溜着凉气鼻子里发出猪吃饱了以后的哼哼声。见我打着手电念书,就靠过来烂笑着说风凉话:“哟,大秀才念毛主席的书呢。毛主席的书念了明天就帮我多推几车河泥吧,这叫精神变物质。”那狗日的干活偷懒, 干女人倒有精神。 我就损他:“这一块五可够值的,放了三炮吧?”
“我操,你小子盯梢儿呀?”“懒得盯你,那种脏货,也往里德,倒贴我都不要。
同样花一块五,你排第三回,冤不冤?该让他减价儿,先去的一块五,到你这儿变五毛差不多!”“你拿我打镲,是不是?觉着自个儿读毛主席的书特了不起是不是?
少来这里个儿楞!我花一块五排第六,我乐意,老子是撒财童子,哎,关你妈屁事,招你说这风凉话 你小X 患子真他妈嘴欠,要不是看你是个孩子,我非抽你不可!”
这傻X 也敢冲我装大爷!我连想都没想,就觉着脑门子上血一涌,人就一跃而起,掐住他脖子往死里掐。不知不觉中扭成一团,打得头破血流。
这下子可好,招来了工地的领导,看见踩得稀烂的《毛选》,我理所当然地告状说我半夜带着问题学《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小子讽刺挖苦我,出口伤人,才打起来的。说着去捡我的书,一页一页抚平。那孙子理亏,连个屁也不敢放,怕那事儿给揭出来。见我不检举他们,也就认了错。
我也从此被发现,成了红人儿。先是获“轻伤不下火线标兵”称号,又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从此脱离了苦力,给抽调到临时会战指挥部当宣传员,给领导打下手,抄抄写写,出黑板报。那会儿正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最热闹的时候,我这城里的学生就成了秀才,专管成段成段抄报纸。那一冬,河泥没推见车,倒是要起笔杆儿来,成了知识分子。跟着领导走走看看,吃的也好,接长不短的有肉包子和白馒头就粉条炖肉, 一冬天下来人倒变白胖 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闹着了撞上大运。
过年回去前,指挥部写了表扬信让我带上,还说通知了县里,将来争取上县去当宣传报导员。心里这叫高兴这叫狂!打了一架,反倒有了出头的机会!说不定一回去就能抽调上县呢。我傻X 似地满心欢喜回了趟北河,跟家里人大吹特吹,让他们等好消息。
一回村,拎着徐水老白于去支书家,一进门就挨了一个耳贴子,表扬信都没掏出来,他骂我不要脸,上工地上去惹是生非,竟欺负到他表侄子头上了,还踩着别人往上爬,假充学毛选。从此让别人顶了我的名额去根治海河,我接着耪大地。我真想一酒瓶子开了他个王八蛋操的,可我忍住了,大丈夫能曲能掉,十年报价不晚。
在人家屋檐下, 能不低头 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回不去北河矿,就得打着在那个只产山药蛋子的穷地方扎根下去。
一班人不差什么的,全成双成对了,连三儿这号赖叽叽的小子也搭上了一个同样赖叽叽的女生,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他们搭帮过日子,一块儿吃一块儿通达,一块儿回北河去过节又一块儿回来,像是订了终身似的。集体户算是名存实亡我和鸣鸣,倒成了孤孤单单的两个人。我反正是栽了,也不可怜自己,只是可怜许鸣鸣,一个弱女子,独个地撑着干重活儿,又清高,不肯求人。我去帮她推车,她轰我,一个人伸着脖子拉粪车。帮她挑水,她不让,宁肯一个人回回挑半笆,一趟一趟地执。我真他妈替她难受!那个李大明说走就走,敢情那边有他伯伯照顾着,一点苦不用受。他按说应该从那边的知青生活中受到提醒,能猜出鸣鸣的日子。可他后来连信也不来 这个没良心的!
那天又在井台儿上碰上鸣鸣,她正艰难地往上摇轭转把儿,一看就知道她正病着,一摇三晃的。我盯着她那弱不经风的身子像棵小树秧子在风中晃晃悠悠,不知怎的就心里疼得慌。我知道我这是自作多情,是犯贱呢。人家虽然是让大明甩了,可照样看不起咱呢。‘鸣鸣,我来吧。“我管不住自个儿,还是说出了口。
她瞟我一眼,说:“用不着,我行。”我就受不了她这种口气和这个神态,一步冲上去抢过鞭轶把,冲她大叫:“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就那么不入你的眼?我巴给你,我图你吃了图你喝 甩什么脸子!你!”她扭身就走。我真忍不下这口气,眼冒金星儿大叫:“许鸣鸣!你站住!”她站住了,回过身来愣愣地看我。一看那眼神儿我就心软了,嘴也硬不起来了,只顾低头往上摇水,到满了两水育,挑起来就往女生那屋走。进了屋舀起水筲把水倒干净,低头就走。过她身边时,我怎么也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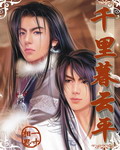
![[重生]修仙道之--躲不掉的孽缘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7/1727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