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缘千里-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红笔写上了“最高指示”,如“念念不忘”
之类,但仍依稀辨出南国风情的花鸟风景水墨画迹。这青瓦白壁的南方大院,让人们住得挤挤插插乱七八糟,碎砖房挤得院场中只剩下羊肠小路,可仍透着历史的风韵。你记不清呜呜家任第几进院子了,只记得她家是那院子中最整洁的,门前雨廊上没堆杂物,更没垒鸡窝煤棚之类,清清爽爽,高台五级上,是一尘不染的方砖慢地,轩檐斗拱,均是精细的透雕。方方正正的几扇大玻璃窗上罩着朴素的方格布窗帘,素雅而简朴。你愣头愣脑地在那迷宫样的院子里钻了好一阵子,终于发现了鸣鸣家那卓尔不群的外景。
你发现那些乱糟糟人家的窗上露出警惕的面孔来盯着你,但你不怕他们,大大方方地叫着许鸣鸣的名字,还说“老师让通知下午到校开团干部会”,大声大气地说着就进了屋,自以为像地下党一样机智勇敢。进屋后你迫不及待地把山里的情况讲给她听,讲得面红耳赤。你太需要她分享你的快乐和兴奋了,似乎一想起在农村“战天斗地”,眼前就浮现出你和许鸣鸣开梯田,油灯下读马列,为农民办夜校,上门为他们治病。你会写出一部部小说和诗歌,你们那个山村会出名,或许它就叫西山坞或北山坞之类,你会一夜出名,腰上扎根红腰带头缠陕北人白头巾,扛着锄头腋下夹着你的小说诗集之类让记者拍照,那种意气风发的新农民作家诗人形象会跃然全国的报纸上,你会比时下最红的浩然还要红。浩然那些农村作品实在太老掉牙了,他只会写合作社土改而已,他不可能懂上山下乡,不会懂反修防修,不会懂这一代人的情怀。
你如醉如痴,把想法一股脑儿倒出来给许呜呜听。她给你彻了一杯浓浓的白糖水,喝了一头的汗,仍感到口干舌燥,就到外间屋去从水缸里舀了半瓢带冰碴儿的凉水喝下去。
鸣鸣在里屋说你别再说了,快走吧,我爸该下班回来了,你呆工夫太长了,院子里邻居要讲闲话。
“我不怕,鸣鸣!只要你也不怕就行。”你在外屋里说。鸣鸣关了里屋的门,央求你快走,别让她爸撞上。说着从门缝里塞出一块小手帕,“擦擦汗,快走吧,还有几分钟我爸就回来。”
你掖好手帕,拉开风门出来,想起《红楼梦》中黛玉在手帕上写诗给宝玉的一段。你明白了鸣鸣的心思。她会听你的,一同跟你下乡去的。你不再怕那个李鸿章大院中的人们了!
那一年你们班成立了一个“学农”班。一到农村就激动,有几个月不下农村就难以自持,又要催着老师组织大家去农村度暑假,号称“革命化的假期”。你们组织了一个农机学习小组和一个“红医”小组,兴致勃勃地学什么汽缸,学电路,学中草药配方,学针灸,只恨学得太少。那时你想的是一下去就成为一个生产队的栋梁,有的当电工,有的当拖拉机手,有的当赤脚医生。
每次去学农,干完一天的活儿,同学们都在打扑克,你却爱一个人悄悄走出村,躺在麦地里,看天上越来越红的夕阳,看夕阳染红染黄的田野,一直躺到一弯清月上来,一边是落日,一边是新月。朦朦胧胧中你会想中国人奋斗了五千年才到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那时的人该是什么 你很为班上那些毫无理想的市民子弟痛心,他们仍然像一群小学生顽皮胡闹,组织他们下乡来,他们就欢呼:
总算不上课 到了田里他们不好好干, 全在磨洋工,收玉米时一刻不停地嚼玉米秆子当甘蔗吃,甚至偷了玉米棒往家带被农民发现后吊在房梁上打,打断了腿,他们有时会在地里边干活边斗嘴,说着说着就会打起来。你像个小老师一样批评他们,讲道理,他们会起哄,说听不懂,说你鼻子里插大葱——充象。在这些人面前,你从柳刚那里学来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昨天你又遇上了他们。果然像三儿这样当年就混混饨饨的人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迷迷糊糊。这一代人中荒废了多少?他们现在都娶嫁生子了,又一茬儿人正长起来。 早婚的同学中,孩子都十岁 谁又能保证这一代人不会像父辈一样无聊地成长为废物?
你曾一直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但现在你认为,用什么教育是个比教育更重要的问题,否则就等于没有教育。当年那种虚假的理想教育悲惨地失败了,它成了野心家们政治斗争的工具,戕害的是柳刚和你这样纯正的青年。而三儿这类占多数的混子依然混饨如初。多少虔诚的青年把。D 挖了出来做了理想的祭品?!
倒是三儿他们没有付出也没有牺牲。
而历史对柳刚们太不公平 这样执著纯正的人似乎无法从一个过去的时代中抽身出来。现在他的同学全拿他当笑料。亚梅跟他离了,带着儿子嫁了大款。他自信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自称一面与厂领导里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一面与世俗的拜金主义抗衡,超然于世,卓尔不群地清亮着。哪一方面也不需要他,他拒绝与任何一方同流合污。他永远只能停在团委书记的位子上,发发电影票,组织舞会、郊游,像俱乐部主任一样。那些资本官僚主义者永远混得好,永远是喝工人血汗中饱私囊的硕鼠。
他们会用什么效益工资和纪律惩罚这类市场经济的东西来整治工人,而他们自己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倒买或倒卖国有资产从中渔利先富了起来。工人们时而发不出工资,住宿条件几十年不变一贯下来,仍然住在那片破平房区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柳刚一边为工人的福利同厂里吵,一边却痛心地发现厂里不少工人在合作份材料倒卖。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那个工厂里没人需要他。最终他只能辞职,一头扎进日本人开的酒店里,默默地挣自己的吃喝,把自己混做俗众。晚上回家就着一盏清灯,读他那些读了多少年的马列原著,写着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做着写十篇发表一篇的文章,号称“在两个世界中执著于马列主义”。
他拿着自己这些文章去大学里谋教职,天真地等着人家的回音,材料全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理由十分充足,人满为患。
这次回来,你与他有了一次真正平等的对话,因为他在你眼中不再是令你五体投地的英雄。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
“三哥,你研究了这些年,最终弄懂了你研究的东西了吗,是不是更该面对现实?”
“我懂你的意思。你们都在可怜我,我也后悔自己没学一门技术,这是时代的错误。”
“我们都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都有十分丰富的的自然科学知识。”
“但我相信,只会一门科学知识的人并不能算知识分子,充其量是韦伯所说的那种没有心灵的专家而已。一个社会是木能指望这种专家的,他们其实与工匠似无大区别,只是一级工与八级工之差而已。”
“你不以为你这样以先知自居其实很徒劳 也很悲惨。一切似应顺其自然才好。
有时用一种超越实际时代的理论指导行动反会阻碍时代的进步。比如批判私有制。”
“我知道以我的身份做时代的先知是可笑的。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我有这种信仰。
上山下乡那五年,狂热,理想,走过了头,真理也成了谬误。可是人是不能没有理想和信念的呀。反倒是那几年农村艰苦的生活坚定了我的信仰,让我懂得钱不是万能的。
所以考大学时我没有去念时髦的理工专业,念了政治系。我绝不是想政治救国,我只是更关注人的心灵。我插队的那个山村,农民们靠着砍林子、卖猪、进城打工,是富了点儿,可他们心里仍然跟二十年前一样空空荡荡,有了点钱反倒修庙烧香跳大神, 算命,胡吃胡喝,城里人又比他们强多少?人没点精神,行 我这样理想主义是不是成了神经病, 你肯定也打心里笑话我。可我只能这样生活 这样也不错,白天挣自己的吃喝业余当当马列主义者。这并不妨害谁。“对仍像二十年前一样真诚的柳刚,你竟哑口无言。是啊,西方人还有牧师呢,人们还虔诚地信教,还在层出不穷地出着大思想家,我们却把柳刚当成了怪物。表哥这样的人其实含金量很高,但是并非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有用。他的作用只是当一个大堂经理。
历史把他摆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坐标上, 他又能怎 与他的同时代人比,他这样独领过风骚现在又独醒独行的人倒显得很珍贵。历史注定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既得利益者,成为虚伪的、丧失独立人格的人。有些人就是能够以变应变,一个时代一个腔调,永远领风骚,永远走红。尤其像表哥他们这种学政治出身的人。
你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柳刚那种英雄主义的影响,当时你就像一个狂热的小教徒尾随着一个大师兄亦步亦趋,一招一式都在刻意模仿,那一切都蒙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可是你却永远无法忘却,摆脱不掉那沉重的记忆,因为那一段生活给你的身心打下了太深刻的烙印。你成熟得太早,那就成了你性格和理想的定型期,那以后的许多事木过是破碎的印象无法渗透你心的基石,而定型期的记忆却是完整无损的。这就是强大的童年张力。
似乎成年后的一切不过是在重复童年,仅仅是变奏而已,主旋律仍是一致的。
那个恶梦样时代中国一个小城里的经验,让你过早地受到了创伤。与德国或澳大利亚的同龄人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像是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毫无沧桑感。你无法与他们交流。
比你小几岁的那些青年,连他们的痛苦在你看来都是幸福的。
于是你只能与童年交流,只有它才最实在。你的前妻,一个从小泡在燕园小洋房中长大的脑神经专家,她似乎永远不明白童年何以对你有那样大的魔力。你和她一起吃着吃着饭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说起童年的北方这个小城里的经历,自以为有头有尾地讲着什么,实则只有你一个人明白,她开始怀疑你的脑组织受过什么创伤,要替你进行全面检查,还对你使用催眠术,想让你摆脱那个看不见的阴影。你怕她了,怕这个弗洛伊德的信徒。她总在用医生的目光看着你。有时她的催眠术行至半途,你会怒火中烧,狠狠摔碎暖瓶以示你的清醒。你与她的童年大相径庭,两段经历永远无法融合。本以为同她的结合是个契机,是一场为了忘却的仪典,从此便可以像两个没有记忆的男女开始新的生活。可挥之不去的童年张力却死死地攥住你的灵魂不肯放手。你同她最初是那种小女孩与兄长的关系,她活泼可爱,崇拜你的深沉,用“沉默是金”的成语来套你,把你当成~颗金子,执著地追求着你。你迷恋她的青春美丽纯洁,常常被她的热情俗化,冰冷的心在恋爱的季节里曾解冻。她写诗,称你是一棵布满年轮的老树,她是一只报春的小鸟,停在你的肩上,仅仅因为她嗅到了老树心中的青春气息。你们在她的同学眼中成了最佳搭配,是那种成熟的智慧与亮丽青春的结合。可这并不能让你十分投入,因为她总让你想起许鸣鸣,她太像十六岁时的鸣鸣
对鸣鸣的负疚会让你一辈子不得安宁。那是全然不同于与前妻、洛洛季娜和青水季子关系的一种爱。那是一种“保尔与维吉妮”加革命理想的青梅竹马之情,不掺杂一丝的情欲。即使那个时候你有了一点性的成熟,它也早让理想的执著追求给冲淡
你们那个时候的座右铭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冯志永那类人由于性的早熟而变得无比邪恶,他们一口的下流话,放学后和一些女‘秋子“在一起”拍婆子“,在你眼里那与流氓似别无二致。
你追求的是一种“革命的爱情”,自以为是无比崇高的情调。因此与鸣鸣的爱就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清教色彩。那种朝思暮想的激情是神圣的,纯精神的,但在那个年代里是最温馨甜蜜的情感体验
那个恶梦般的小村子,根本不需要你们,队长书记抱怨多了二十张嘴,还不如养二十四猪更值得。你们狂热地去改造农村,结果是被扔在村边的一溜集体户房子中自生自灭。你不再像学农时那样躺在麦秸垛上憧憬共产主义了,你的现实是想法早点离开那里。那里的书记队长如同上皇帝一般,跺个脚全村都会抖三抖,全村的人都在巴结他们。什么电工、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教师、拖拉机手这些需要文化的角色全让那些没文化但会巴结的村民占 一、 二年一个的工农兵学员名额是不会摊到你们头上的。前几批的老知青中有两个女知青被招工,上了大学,可人人知道她们付出的代价。老乡们说“伺候了好几年换个回城,好惨。”她们现在是人到中年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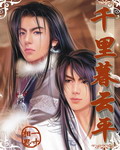
![[重生]修仙道之--躲不掉的孽缘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7/17279.jpg)

